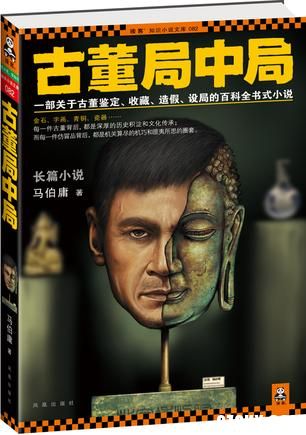古董杂货店 →蒋胜男、匪我思存、飞樱-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一字一顿:“如是,千秋骂名我来背负。”缓缓道:“史阁部一意孤行,全城苦守,结果如何?是屠城十日,血流成河。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我声音凄厉:“任你如斯诡言,亦不过替腼颜出降狡辩,叛国贰臣,你背负得起,我背负不起。”
大株芭蕉
他从来没有用那种眼神瞧着我,良久,突然道:“莫若说,你恨我不如陈子龙。”一语中的,我全身的气力突然一松,却原来家国只是一个籍口,我这铮铮的一身傲骨,只是一个籍口,我软软晕倒。
这一病缠绵数月,病榻之上只闻夜雨凄清,隔着窗儿点滴到天明。窗外是大株的芭蕉,漱漱有声。松江我那小红楼前,亦是植有大株芭蕉,每逢夜雨,卧子总伴我静听那淅淅雨声。我发着高热,那个名字噎在胸口,每次呼之欲出的最后一刹那,总有理智能及时拦阻。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如是,如是……
一碗碗的苦药喝下去,高热却总是不退。我昏昏沉沉睡着,仿佛灵魂已死。
颊上突然传来一阵清凉,我用仅存的力气睁开双眼,却是那只臂搁静静放在枕上。谦益却远远立在床前:“如是……”
我终于落下泪来,争不过,争不过,这许多年来还是争不过一个他,那陈子龙是我命中的魔障,避无可避,无路可逃。我慢慢伸手握住臂搁,像是想握住梦中的过去,谦益只是望着我,一刹那像是老了十年。
我的身子渐渐起复康健,山河早已变色。谦益奉了满清的诏书,北上为官。
我盛妆相送,却身着一身朱红。谦益变了脸色,那些来送他的新朋故友也变了脸色。朱红,不忘朱明,如清脆的一耳光括在他脸上。我痛意而绝决地看着他,他的目光反倒安静下来,仍是那种了然的淡定通透。
我从心里憎恨这目光,说不清道不明的憎恨,我错了,他错了,我们两个都错了。既不能为国,亦不能为家,这俗世令人厌倦得透了。
我开始放浪形骸,甚至公然当着他儿子的面与人调情。钱公子气得要鸣官究惩,我只幸灾乐祸着瞧着归家未久的堂堂钱尚书。
谦益淡淡告诫其子:“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
轰然便是一败涂地尽失城池——我终究不是他的对手,割袍断义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亦不是他想的那样。
家还是徒有虚名的家,国却是早就亡了。我倾尽妆奁之资献与南明朝廷,只盼能唤回东风。谦益不言,我亦不语。这是为国,还是为着陈子龙,他早已经不再问,我更不会再提。那个国寄托了我全部的信念,因为那曾是陈子龙的信念。那个国是我全部的过去,见证过我今生的唯一。
山河寂廖,残梦终醒,南明朝廷苟延残喘,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麻木地瞧着谦益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终于撒手人寰。
钱公子在灵前嚎啕痛哭,所有的人都是素白的衣衫,屋内皆是白汪汪的帷幕,四处挂着丧幡,我披在头上的孝布生硬摩挲在脸畔,粗糙如砾,我竟然没有哭。
钱家上下皆道我没有良心,谦益,你视我为至爱,我只能待你为知己。我终究是有负于你,这灵堂之上,连泪已干涸,半生就这样遥迢无望地去了。
那些旧日的诗句,还言犹在耳,你荫蔽了我半生,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现世安稳,你却撒手去了,抛下我继续留在这尘世受苦。
尸骨未寒,族人却已经寻上门来,挽了太叔公出来说话,言道钱家家产,不能再掌控于我手中。
家产?
我漠然望着披麻带孝的族人,他们如一群狼,眼里幽幽发着噬人的光芒。七嘴八舌搬出了祖宗家法,嘿,祖宗家法,甚至说我多年来并无生子,要撵我出门。太叔公坐在堂中上首的大圈椅上,只嘟噜噜抽着水烟,我突然微微有些眩晕。极小的时候院子里的妈妈也是抽这样的水烟,我在堂前咿呀学着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一个词转吐不过来,妈妈顺手用烟杆打过来,火辣辣得痛,却忍住不能吱一声,从头再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终究是都付与断井颓垣……
我终于缓缓道:“太叔公,此事等过了头七,我请阖族公议就是了。”
太叔公慢条斯理地磕磕烟袋,说:“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只要今天大家说个齐全,也是个了结。”
我瞧着他泛着烟黄的牙,只是一阵恶心。
这样的腌臜气如何受得?
谦益,方知你素日里曾替我抵挡了多少风吹雨洗。我到底是负了你,如今难道竟保不住你身后这点产业?
我淡然道:“好极,就请太叔公宽坐,我命人去请阖族长辈,还有近支子侄们来公议。”回首便吩咐婢女,叫厨房预备素宴。
他们松了口气,大约没想到我如此知趣。
我走回房中,暗暗写了封书信,命人送与知县,再出来亲自执壶斟酒。
阖族人都放下心来,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孀妇,最后还不是任他们宰割?酒过三巡,我陪笑道:“众位侄子陪太叔公坐坐,我上去开箱子取地契账簿。”
房里金碧箱笼,高柜抽斗,这一切,楼下那群人垂涎欲滴罢。我缓缓打开抽斗,一条长长的素色寒绢,轻盈若雪。轻轻抛过房顶的大梁。
谦益,我负你良多,今日便全还了你。
卧子,你答应过我,会来接我。
我派人寄与知县的信——夫君新丧,族人群哄,争分家产,迫死主母。
楼下酒宴正酣,那些人浑不知,一个也逃不了牢狱之灾。
锦盒
唇边终于浮起一个浅淡笑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如是……如是……
白月长长的睫毛如蝶翼忽闪,柔声问:“你为什么不去投胎转世?”
那声音却静默片刻,方道:“俗世纷扰,那一世我有如花之貌,林下之才,事国节烈之名,到头却只是枉然,何必再生受一番煎熬?为人其苦,不若为鬼。”
红云咭得一笑:“如今几百年过去了,情形可不一样了。”正说话间,忽见有人推门进来,白月小心将臂搁放回锦盒中,起身迎客。
却是一男一女,男的年可五十许,大热天里全身的名牌西服,粗肥的脖子上若不是系着领带,真叫人怀疑他是否还有脖子。女的却是韶龄妙女,身材妙曼,姿色过人。将嘴一撇娇嗔道:“答应人家买钻石,却带人来这种死气沉沉的地方。”
那男子道:“听人说这种地方才有好东西呢。”四面环顾,只见店堂洁净如茶舍,几把明代的鸡翅木椅,线条简洁明快。他伸手摸了摸那椅子,说:“好是好,就是样子太简单了点,要是雕上富贵牡丹,龙凤图案,这椅子就好看了。”
那女子在他臂上轻轻一拧:“这种地方的东西,全是些破破烂烂的老古董,只好配你们家那个黄脸婆吧,正好一样又旧又破。”一转脸却看到锦盒中的臂搁,咦了一声:“这个倒是真漂亮。”
“漂亮就买。”肥油的一张脸上绽出笑颜,趾高气昂问:“老板,多少钱?”
白月淡淡一笑,缓缓道:“前阵子拍的清乾隆粉彩御题诗文竹节臂搁,以71万元成交。这只是明代子岗所出的和阗白玉臂搁,曾为名妓柳如是所有,我们目前叫价210万人民币。”
红云好笑着瞧着对方瞠目结舌,从她手中接过了臂搁,轻轻放回锦盒中。笑得一脸灿烂如同窗外的阳光:“店小本薄,概不赊账,请付现款或刷卡。”捉狭地挤一挤眼睛:“先生,要不要包起来?”
就是白月,也忍俊不禁,微笑瞧着那两人急急仓惶离去。
红云扮个鬼脸:“他们两个怎么一幅活见鬼的样子?难不成他们和我们一样,异禀过人,可以瞧见这臂搁上的柳如是?”
臂搁上隐约传来一声轻笑,而后低低一声喟叹。声音几乎轻不可闻:“原来几百年过去,却原来情形亦不过如是罢。”
附录:
臂搁考证:
我国以前的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就产生了枕臂之具…臂搁,其竹片肚稍虚起,不惹字墨,最为适用。有了它,作书挥毫时枕在臂下,就既防墨迹沾臂,又防夏天臂上汗水渗纸。另外臂搁还有一个用途,纸轻易被风掀,压在上面,可代文镇。
臂搁又是书案重要饰物,富书卷气。一般用去节之竹筒分劈成三刻制。因是枕臂之用,宜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有镌座右铭以为警策,有刻所喜之诗画以作欣赏,有刊挚友亲人之赠言以为留念。它确实还有一些秘记档册的作用,故极受士人的偏爱。
臂搁是常置案头的玩物,日夕摩挲,愈摸愈润,久之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又因竹子性凉,古人即用“竹夫人”(唐时称竹夹膝,宋又称竹妃、竹姬、青奴等)祛暑,故每当心情烦躁,或精神倦怠之际,能独坐清斋,手抚臂搁,闭目养神,则可令人蠲虑忘世,得一时之清静,盖手掌有劳宫穴,触竹有凉侵肺腑之感。犹似佛门僧人坐禅以竹“性板”(又称禅板,形式似臂搁,但长达42厘米,由半爿筒竹制成,光素不刻文饰)置膝上抚手静心。这一妙用大概也是古人所谓的修心养性。
另有觅择异形竹或珍稀竹类,如人面竹(一称龟背竹)刻制为臂搁的,那就更物以稀为贵,奇趣耐玩了。
白月用毛巾仔细地替红云擦拭一头湿发。红云的头发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蓬得满头都是,所以她不能剪短发,只能紧紧地用头绳系住。这样“张狂”的头发洗起来自然更加麻烦。红云没有耐心,每次都弄不好,等干了一梳免不了又要哇哇大叫。
“姐。今天来的那个人……你确定那把古梳可以卖给他们吗?”红云有些不确定,先前她在店里找东西,一失手险些把那漂亮的梳子掉到地上,差点把白月吓死。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白月就把它卖掉了。之后还狠狠瞪她一眼说:“眼不见心不烦。与其让你总有一天弄碎它不如卖了换钱花。”
“你现在倒担心起那把‘倒霉’的梳子来啦?你已经是第几次差点把它掉在地上了?我还以为你看它很不顺眼呢?”白月故做不解地调侃她,嘴角隐隐地笑意出卖了她,可惜背对着她的红云看不见,可怜地想着怎么跟她解释。
终究还是不忍心看她那么烦恼“放心吧。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职责’的。”红云闻言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姐,其实我不完全是担心那把梳子……”
白月感动地笑了,其实她一直都知道妹妹是更担心她忘记职责而受到惩罚。
“看你下次还敢这么毛手毛脚的了。”
“我一定努力控制。”说话间她已经不小心的把一个红木雕刻掉在地上,换来白月一声惊呼。
红云暗想,还好这个摔不碎。
商品八:玉梳
魂牵梦萦
江心无月
广袤无边的枫树林,饱经风霜的红叶鲜红得仿佛要滴出鲜血,繁茂的枝叶遮天避日,形成凝重的红云,低低地压在人们的心上。
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耳边一遍又一遍地低喃:卿卿吾妻,当血枫尽染,珠联壁合,就是你我相聚之时……
谜一样的男人
是谁,是谁在说话?我猛地睁开眼,惊恐地弹坐起来,急速地喘息,瞳孔因为心脏的剧烈收缩而微微放大,双手紧紧攥着项链上的吊坠,想借此摆脱那个诡异的梦境,但收效甚微。为什么,还会梦到?不敢再睡,只能披衣起身,坐在书桌前,开始翻阅桌上的案卷。
本人凌霄,25岁,正值挑选男人和被男人挑选的临界点上,就职于本市第一医院心理科,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状况并寻找为其排减痛苦的方法,也曾获得类似“优秀”、“模范”之类的称号。但如同顶尖的理发师难以打理自己的头发,我不知道该用何种理论来解释自己的问题。
小孩子5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而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每当睡觉总是做同一个梦,给人一种让人心碎的熟悉,好怕好怕,往往睡不到一小时就哭着醒来,但醒来后只记得无边无际的红枫林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久而久之就不肯睡觉。人消瘦得很厉害,父母很焦急,带着我四处求医,但无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吃了很多安神助眠的药物,却毫无效果,每天强撑着眼睛想睡又不敢睡,人瘦得只剩一张皮了,只待一阵风将我刮回轮回殿去。每个人都知道我活不过这个秋天,人们只能拍拍父亲的肩膀,道声节哀。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