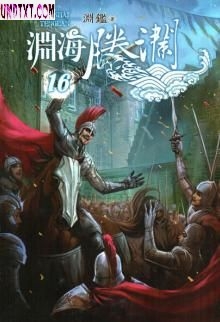越沧海-第5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日住在宫里也没甚意思,今时不比往日了,年后我就要去苏州赴任。将来总归要从宫里搬出来,而且还要安顿母妃,所以这两日先去勘踏了一番地界,准备圈地起个园子。地方如今已经选好了,不过如今也有法度,不好多动用宫内监的匠役,就想着来你这儿打打秋风了。”
吴越没有称帝,制度也不设六部。所以不像南唐有“工部”可以监管那些朝廷出钱的藩王府邸营建。不过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吴越没有这个部门不代表没人管这类事儿,“宫内监”和“都工司”就分别掌管着宗室需求和政府工程两方面的施工组织管理。
钱惟昱是大王的近亲,理论上他起园子也是可以从宫内监要求拨给工匠的,只不过数量上比较受限。如果园子起得大了、工期要求紧的话,自然不如自己再在找民间商人增补一些人手物料来得自在。
“嗨~这有什么!这点小事儿,哪要小王爷亲自来跑一趟,卑职今天就让族中子侄调集匠人物料,一准误不了小王爷的事儿。
这三年多亏了当初小王爷开导的新式造船之法、还有从大食人那里初窥而来的些许领航皮毛,卑职的生意家业三年里几乎翻了两番,比之前跑海十年都攒的多别家的船,一年去日本、高丽加起来也就三趟,最多四趟;卑职的船队不用等信风,一年可以至少跑**趟,去年还跑了十趟。这些修园子的地价、工匠、材料就算卑职孝敬小王爷的了。”
蒋衮一边说着,几句话见已经把钱惟昱引进正堂,一旁早有侍候的侍女端上刚刚煎好的团茶摆布停当。
“那小王就不和你客气了,不过这次来当然不光是为了这事儿。正有别的生意上的事情要和你商议。”
蒋衮刚刚坐定,一听钱惟昱这句话,半个屁股又虚虚地往前挪了一挪,一副不敢坐稳的虚心求教模样。这几年钱惟昱虽然人不在杭州,但是蒋衮也是有商队趁着唐、越交好的机会去金陵做生意的。钱惟昱时常让顾长风的人漏消息给蒋衮,蒋衮只要照办了总能弄出点能赚钱的玩意儿,所以他对于钱惟昱的点子已经是百分百的信了。
“首先就是那个‘活字印刷’的工艺你也知道,这东西小王鼓捣出来也有一两年了。原本就是打算等回国了之后大展拳脚多印一些经史子集的东西,好赚取一些文治教化的名声,倒也不纯粹为了赚钱。不过这次机缘巧合遇到了冯相,才把这东西献出去了一副样品。”
“唉,小王爷,这件事情,卑职总觉得咱布局了这么久,有些亏了。白瓷活字到了冯道手里,能够弄完《五经》、《九经》固然是让小王爷也涨了好文的名头,但是只怕从此在中原流传开来之后,往后印书的利润就下来了。”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忘了我这活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么?他们就算拿到了样品,也不过是用用罢了,还有很多后手不明了的话,也是无用。”
“这倒是……说实话,卑职虽然一直给小王爷提供了材料和工匠,但是至今,对那活字的制法,还是有些细微之处不甚明了。当初小王爷命卑职使人刻的錾钢铁碑,应该就是用来挤陶土模子的吧?”
“那是自然,如今我们只是给了白瓷活字的实样,他们一来不知道制这活字的白瓷土配方比例如何、怎样才能做到烧制前柔软、烧制后尽量坚硬,所要想仿制自然不易。而且他们也不知道錾钢模具的存在,就算有了配方,在雕刻的时候也要大费周章。”
原来,钱惟昱虽然把白瓷活字给了冯道,但是却留了很关键的两手。烧瓷用的陶土配方固然是其中之一,而更重要的则是刻法。
当初,钱惟昱让蒋衮使费重金,找高手匠人在几块厚熟铁板上雕凿了七八千个汉字,把常用字和两三千个冷僻字都涵盖在内。
既然雕刻的是铁碑,所以要想凿成阳文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雕刻文字的时候,雕凿阴文只要把笔画部分刻掉就行了,而雕凿阳文需要把所有留白部分刻掉。以铁板的坚硬程度,要想把大片留白部分都刻掉,除非有现代工业的铣床才行。
做好了阴文的铁碑之后,钱惟昱又教蒋衮用铁匠们改良的淬火渗碳工艺,还掺入了日本匠人铸造武士刀时的白蜡烧入之法,对铁碑进行表面硬化处理;
熟铁相对柔软、高碳钢则表面更为坚硬耐磨。在铁碑相对软的时候雕刻,然后刻好了进一步硬化,那就基本上很难磨损了。同时这样的“烧入”处理也能让铁质的耐锈耐腐蚀程度提高这就好比古代的名刀剑如果保养的好,都不易生锈。
表面硬化之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钱惟昱的白瓷活字在陶土状态的时候,其实不是依靠雕刻来形成字迹的。而是用带了字迹的铁碑作为模具,把陶土坯压在上面用力挤压,随后就印出了字迹。
然后再把软陶土放在方框里切好成一个个单字、用一块平铁板把字迹这一面的厚度批平、放进瓷窑里面烧制成坚硬的白瓷,一副白瓷活字也就这么产生了。
不要小看手工刻字和用模具压字迹这两个工艺上的小改进的效果。因为钱惟昱做的陶瓷活字字体大小都比较小,而且字迹的笔画粗细也远比同时代的雕版印刷字体要纤细。而如果采用直接雕刻陶土坯子的话,就很难雕出这么细的笔画因为雕刻阳文的时候,如果笔画太细,字迹是很容易被雕断的;而雕刻阴文的时候,就不存在容易雕断的问题。
现代人看那些古代的线装书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古书怎么字体印得那么大,大多数书一页纸才那么一两百个字,最多的也就三百。而现代的打印机动辄用小四、五号字打word文档,一页一两千字很平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古代的字模笔画没法雕刻的太细,所以字就不得不大了。
这也就意味着:哪怕给冯道的那套活字被人山寨出了配方,而且不考虑雕工的费时费力,单论到了印刷阶段对方的用料依然是钱惟昱的几倍。同样的纸张墨汁消耗条件下,用钱惟昱的核心技术弄出来的印刷术可以印出来的书的量是对方的至少两倍!这,就是巨大的成本优势。
。。。
。。。
第73章 王室营生
在原本的历史上,活字印刷术虽然最早是北宋毕升发明的,但是因为字印的材料只是胶泥,在耐用性和清晰度上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依然是并存的,并没有彻底把雕版淘汰掉。
所以,那时候出一些冷僻的书,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最常见的例子,比如一个家里有钱、但是文名并不昌盛的文人,想把自己一生所作的一些诗词出成诗集。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名家,就算印了诗集也不会有多少人买,所以书商遇到这样的书,都会要求出书的人自己掏雕版费
这就好比几百年后,那些不是大神的写手要想走实体书出版路子的话,往往不仅赚不到稿费,还要给出版社掏“排版费”,一个道理。
有考古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说是从南宋到明朝正德、嘉靖为止之所以这个数据只能到嘉靖为止,是因为后来隆庆开关之后,活字材质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流入了西方反哺的新材料。隆庆、万历之后的中国印书成本,又有了一个台阶性的下滑如果一个没名气的诗人要出自己的诗集,不足百页厚度的单册那种。以一次性印五百本为例,就需要耗费五百贯钱。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本书要一贯钱的成本了,当然,如果可以加印数量的话,雕版费平摊到每一本上会低一些。
如今正是五代时候,哪怕不考虑战乱导致的文化萎靡、书籍市场的需求下降带来的规模效应无法提振。按照市价,一册百页以内的四书五经等常用书,售价也要四五百文钱,而如果是非常用书,则要七八百文不等。
蒋衮是生意场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了,对于市面上百业产物的行情自然是比较门清的,不用钱惟昱给他科普。
因此,蒋衮按照钱惟昱给他列出的目前他们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活字印刷术,和将来别人有可能从钱惟昱送给冯道的那套活字上山寨出来的技术之间的差异,很快就算出了其中的市场差价价值。
“如果按照这么算来,今后市面上的雕板书仍然要卖至少40000文一册;雕刻瓷活字的书则要250~300文左右;模具挤烧的瓷活字印的书,哪怕卖80~TXT小说:…③ūωω00文都有得赚,就算抬价到200文,照样可以比别家的都便宜,而且赚头依然有至少三分之二!”
“算的不错,这也是小王准备找你合股的第一桩生意。”
“合股?卑职怎敢……这印书的生意,虽然也薄有利钱,但是终究是文人雅士的生意。卑职一身铜臭,能够随附小王爷骥尾已经是万分荣幸了。不如这样吧,开展生意需要的匠人、作坊、材料先由卑职代为办理,日后还是小王爷另寻心腹自行经营吧。”
蒋衮一听钱惟昱的建议,立刻就谦逊地表示愿意退出印书的生意。如今战乱年代不比后来两宋明朝那样读书人泛滥,全天下要买书的读书人估计也就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就算生意做大到天下每个读书人都买你十几本书,撑死了也就是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
而且考虑到读书人大多也不富裕,这几十万两还不是一两年内能赚到的。细水长流的话,将来就算生意稳定了,也就是一年三五万两的进项。相对于钱来说,这个生意更多的是图个风雅,可以帮人在文人圈子里赚取更多名声,宣传意义大于经济利益。
蒋衮如今靠着钱惟昱给的改良海船和新领航技术,光是跑日本、高丽的老本行一年至少进项五十万两以上,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这三五万两的收益自然当是孝敬钱惟昱,图个远期合作了。
钱惟昱听了蒋衮逊让,也就不再坚持,算是受了蒋衮的这桩好处。
“看来,这几年跑海和开荒琉球真的是让蒋公赚到盆满钵满啊,这点小钱都看不上了不过,小王手头也没有经营营生的得力之人,到时候,蒋公还要派些得力的账房掌柜帮小王搭理这些生意才好。”
“这个好说,卑职觉得……”蒋衮满口答应着,一边又眼珠子一转,让一旁的服侍的丫鬟附耳过来,低低说了些什么。
须臾,那丫鬟从后院带来了一个少女,看上去也就和钱惟昱一般年纪而已,甚至有可能再小一两岁。
不过虽然年纪幼小,旁人第一眼看到这少女的时候却绝对不会生出轻视之感。只见她容貌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红眉翠、肌骨莹润;更兼举止娴雅、步态娉婷,行止之间颇显端庄。
钱惟昱乍一看去,便觉得这该是蒋衮家中的晚辈女眷。不过这女子生在豪商之家,却看不出每日淫浸于钱财之中的俗气。服饰只是无纹的素色锦面襦裙,头上也仅挽起黑漆油光的水髻儿,看上去不见奢华,却又一股大方得体之气油然而生。
除了这个少女之外,蒋府的丫鬟还带上来一个精壮的黢黑汉子和两个山羊胡子的枯瘦老丈,看上去前者像是跑海之人,后者则是朝奉、账房一类的角色。不过,美女当前,这几个男人自然是被钱惟昱无视了。
“此乃小女,蒋洁茹,今年十四岁了小王爷莫以为她年纪幼小,对于经济营生、待人接物,卑职属下的寻常男子也及不得得她。”因为还要相互介绍,所以蒋衮也没对钱惟昱解说太多,就转向自己女儿那边,“这是当今大王亲侄、先王嫡子富阳侯,还不快快拜见。”
蒋洁茹微微颔首,侧身万福了一礼,不失端庄地轻声答应:“见过小王爷,旧闻小王爷文武兼通,在金陵时,词名就已传遍天下。也幸亏小王爷是个胸有大志的,看不上经济营生的俗务,不然哪有小女子胡乱打理的机会。”
蒋衮的家业,如今在两浙豪商中已经是无人可比的了,经商的本事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于蒋洁茹的经营本领钱惟昱虽然还没有领教,但是管中窥豹也能略见一斑。此刻只是观察了蒋洁茹待人接物的一点皮毛,钱惟昱心中就浮现了一个名字。
这莫非是一个薛宝钗式的人物?嗯,也许姿色上还达不到那种程度,不过没关系,钱惟昱本来就不会和商人女子产生什么深度的交集。当下钱惟昱也就大度谢过了蒋衮的安排,表示对蒋洁茹很满意。
随后蒋衮又略略介绍了一下那个看似跑船的汉子,和那两个账房、朝奉。那个精壮的汉子是蒋衮的堂弟、名叫蒋正明。其父乃是武肃王早年时候出使日本国的专使蒋承勋,也是蒋衮的叔父。
蒋氏一门乃是明州奉化的望族,从唐武宗年间开始就是跑日本航路的海商世家,至今已有百年。武肃王在位的前二十年,每次出使日本新罗都是蒋承勋操办,后来蒋承勋年纪大了,得子又比较晚,才让侄儿蒋衮接过这个营生。如今蒋承勋年纪已经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