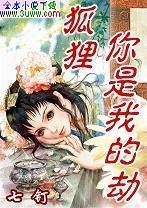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楸ɑ雇ūㄋ牵凡兜闹匾宋铮床呋挚剐卸撸蟾沤小痢涟⒉肌つ潞蹦拢窗⒗ㄌ卦缒甑幕弧K拿执笾诨共惶私猓陨邪踩帧靶帘刺亍保骋伤谠嫉┖游靼读斓加位鞫有卸4镅锴鬃灾鞴苷庖蛔凡丁<谝陨腥瞬扇∈侄蔚难侠餍裕颐巧钚旁诟们疃陌屠账固褂位鞫右驯涞萌硕嗍浦诹恕! �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兄弟”。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恐怖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恐怖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母亲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母亲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军事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母亲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母亲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名人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3)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母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我母亲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242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母亲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母亲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他的母亲曾是以色列左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母亲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朋友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母亲给我解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的兄弟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
第二部分爱在“克里荣”点燃(1)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女郎。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的战士受到热烈欢迎。
在距突尼斯城北六十公里的比塞大港口,瓦西拉·布尔吉巴夫人和政府成员亲临迎接满载数百名巴勒斯坦战士的塞浦路斯船只的到来。在场人群向他们表示欢迎,高呼与巴勒斯坦事业团结一致。然而,在船就要靠岸的时刻,一批突尼斯军人上船,收缴了巴勒斯坦人离开贝鲁特同意携带的全部武器。只有一些保安人员允许保留个人所持的枪支。
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等待着阿拉法特:他的军队分散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在苏丹、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军营,远离战场。
他需要完全重新整编其军队,同时重组巴解组织的民事和财政机构。事实上,巴解组织具有庞大的国际管理机构,要向世界各地的人员发工资和抚恤金、助学金等。在贝鲁特,银行机制允许他能充分支配使用捐赠国和巴勒斯坦侨民提供的亿万经费。而在突尼斯,情况更为复杂。巴解组织因内部争吵而四分五裂,对阿拉法特的指责也纷纷而来。有的指责他把个人的战斗强加给巴解组织并使之陷入困境。
相反,并非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不会再受到以色列人的侵袭。事实上,1985年10月1日,数架以色列飞机凭借充足的空中补给,经过远程飞行,悍然侵入突尼斯城南部海滨小浴场哈马姆沙特上空。昔日,那里曾是贝伊(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住过的地方。以色列战机上午轰炸了巴解组织的军事设施,造成六十多名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关于这次空袭,以方竟视为是对三个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港遇害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也同样在突尼斯,阿拉法特忠实的两位朋友、法塔赫运动共同创始人惨遭杀害:一个是阿布·吉哈德,1988年4月16日被以色列突击队暗害;一个是阿布·伊亚德,1991年1月15日被身边的一个卫士枪杀。这一起神秘罪行的指使人,至今尚未查明。
亚西尔·阿拉法特几乎每天都受到巴解组织一部分人的责备。曾有好几回宣布他要下台,但他每一次都像猫一样巧妙地摆脱了麻烦。在哈马姆沙特被炸后的几天,1985年10月7日,意大利的“阿希力·洛罗”号邮船被巴勒斯坦突击队劫持。一个名叫“克林霍弗”的美国残疾人遇害后连同他的轮椅一起被扔进大海。这次劫船行动的组织者阿布·阿巴斯是巴解组织中央执委会委员。其中两个突击队成员是从突尼斯城过去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对此表示愤慨,他当时同意接待巴勒斯坦人的条件是不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军事行动基地。他本想立即驱逐在突的所有巴解组织的人,这些人约有六千。总统夫人瓦西拉成功地劝阻了总统这一做法。
1987年11月7日,布尔吉巴去职以后,巴解与新总统本·阿里气氛好一些。阿里总统促成美国—巴勒斯坦双方1988年12月至1989年8月的谈判。
在这些年中,阿拉法特恢复了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对话,并经常住在安曼。
1987年夏,塔维勒全家在安曼度假,拜访了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蕾蒙达很自豪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孩子,其中有苏哈。大家互相祝贺,合影留念。蕾蒙达始终是阿拉法特的忠实拥护者,而且,她的长女狄安娜嫁给了巴解组织驻巴黎代表易卜拉欣·苏斯。
1988年11月14日和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苏哈和哈拉在那里又见到阿拉法特。
会议吵吵嚷嚷,阿拉法特重新起着领袖作用,并再一次取胜。会议赞同联合国242号决议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基础。同样,巴解组织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与此同时,阿拉法特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此举是在“青松俱乐部”进行的,这是一家多功能的饭店,用于重大事件的会议厅。俱乐部位于海边,距阿尔及尔几公里。
这个完全是象征性的宣言,旨在回答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声明,但也包含美国提出的开展关于尚不存在的对话的必要要求,即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放弃恐怖主义等。巴勒斯坦人要求他们的权利所使用的提法,与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他们重申自己的祖先早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阿拉法特发表的演说是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撰写的,开头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是向人类披露神的启示的土地,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故里。其民族和社会的生存在人民、土地与历史之间从未间断的和未起变化的有机关系之中更加根深蒂固。”
为唤起记忆,在此也引用了1948年5月14日由戴维·本·古里安宣读的以色列国独立宣言。开头如下:
“以色列国度是犹太人民的诞生地。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其精神的、宗教的和民族的特性。与流亡在外相反,犹太人民忠于以色列故里。”
阿拉法特的演说,为他打开了欧洲各国首都的大门,首先是巴黎。多年以来,巴黎在中东发挥着巨大而审慎的作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与他强力维护以色列国前途是一样的。他保持着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路线,始终致力于法阿对话及以阿对话。
人们知道,阿拉法特的助手之一伊萨姆·萨塔维曾多次充当尝试和平之路的中间人。1983年4月10日,他遭阿布·尼达勒集团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从此对话终止。而参加对话的巴解组织驻英国代表赛义德·哈马米也被同一组织暗杀。
这类对话往往通过以色列的左派,并经与以色列领导人一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