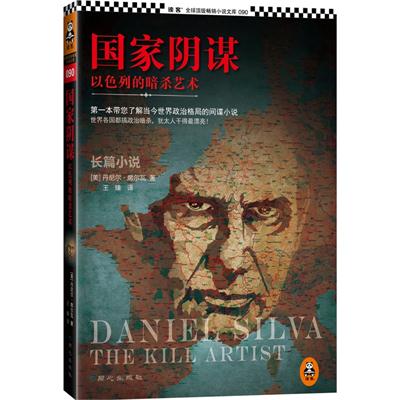暗杀-第2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掌柜沉思着说:“那么一来,日本人扫荡三战区一战毕其功后,便会挥戈东来,全力从三个方向挤压咱们的江北根据地,形势可就严峻了!”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吸引住日军主力于皖苏边界,屯兵于山区屡攻不克,进退失据。而江北一线,咱们部队就可以放开手脚,先行攻破他们眼下全力构造的沿江通道,恢复和江南友邻部队的交通联络。”
他们的构想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新四军相关部门后,得到上级的赞同,命令随即下达,争取挫败敌方情报机关的意图,力求保证许家母女的安全,尽可能创造机会,将她们转移出海陵。
繁昌接到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心意。但是,眼下的局势却不在他的掌控之中。繁盛将许怡接回家后的当天,日本宪兵队便在本田的指挥下,将许宅严密监视起来。住到周家的许怡,也被繁昌派来的手下牢牢看死在宅内,无法外出。繁昌去了万字会南部的司令部,和南部密谈了两个钟头,达成一致意见,借着许府这块饵食,引诱潜伏在海陵地区的军统情报人员出手,一举聚而歼之,扫除日后清乡行动的隐患。另外,在海陵城内放出风去,说许太太已经答应写信给儿子,劝他向日本人投降,率部归来,识时务为俊杰。日本人准备裂土封赏,将海陵及周边的两个县作为他们的驻军地点。还有,汪政府将委其以中常委、集团军上将的重任。
一时间风声鹤唳,又见许府门前日本兵守卫,城中的老百姓人人信以为真,骂声不绝。
(五)
这时,本来心急火燎的周繁盛忽然间静下心来,一改那几日的急躁,恢复了以往的悠闲状态,往返于益丰粮行和周宅之间。过后的近半个月时间里,除了上述两个显明的变化外,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许宅内依旧佣仆进出买菜买粮,繁昌、南部、本田这些关切此事的人一个都没有露面,登门造访。似乎那些满天飞的谣言都是肥皂水的泡沫。只见其形,难探其质。
《暗杀》第七章(8)
周宅内,周太太听说了此事,气恼之余又有几丝高兴。眼前的实际情况,令她无法去责怪大儿子投日附汪的行径。毕竟,许家的事情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警告。乱世中的生存,没有见风使舵的手段是不行的。至于日后会产生什么恶果,虽然难以预料,也就蒙头不去多想了。这次许怡回来,她倒没什么意见。心中甚至还有点暗暗喜欢。老大繁昌结婚多年,玉茹至今未能生育,焦急之余,请了原来康复医院的美国医生安得森检查诊断过,玉茹的身体无恙,好像根子不出在她的身上。至于繁昌,是身体原因,还是其他缘故,她也不便去问。好在周家还有两个儿子,决无绝嗣的担忧。
而且,繁盛已经结婚,虽然在外面花天酒地地胡来,家里的媳妇肯定是不能空旷着的,完全可以在今年内怀上孩子。这样,虽逢乱世,有个小孩降临人世,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出于这点考虑,她亲自出面,加强了对于繁盛的监管力度。嘱咐他每天必须回来过夜,不准在外面胡来。繁盛不敢硬行违拗母亲的话,每日天色黄昏时,便离开益丰粮行回家去。但这样一来,王小姐却是不依了。
这天,见他又站在院子里看手表,忍不住醋意十足地冷笑几声,说:“又要回家陪老婆了吗?这倒奇怪了,难道你和日本人有了默契,让他们逼着你把她弄回家去,正好遂了你的心愿。这样可不行,我得去你们周家,登堂入室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才是你们周繁昌遵从民国法律娶的正房妻子。那个姓许的算什么?”
繁盛啼笑皆非,没想到她这时来插上一杠凑热闹,劈面一把揪住她的衣襟,拖到了厢房里,竭力压低声音,严厉地说:“这节骨眼上,添什么乱?找死呀!”
王小姐奋力踢空了两脚,一下子泄了气,双手死死吊住他的脖子,号啕大哭,再不肯放手。繁盛好不容易掰开她的手,说:“你怎么就沉不住气?眼下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得倾全力去对付,切切不能再出乱子。这益丰粮行办得容易吗,门外至少有两个他们派来监视的探子,风吹草动,难以隐瞒。万一露出马脚来,这半年来的辛苦以及自家的性命可就白白送掉了!”
王小姐松开手,拿起手帕来抹眼泪,抽抽噎噎说:“对不起,刚才失态了。你去吧,我待会儿就没事了。”
繁盛整理了一番方才争执中衣服上的皱褶,拿起礼帽戴在头上,放松了一下脸部的肌肉,洋溢起满不在乎的笑意,走出店门去。
他沿着大街走了百十来步,眼光瞥处,陡然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此人靠在米糕摊前,快速地冲他使了个眼色。繁盛会意,加快步伐与他擦肩而过,在前方十字路口疾闪向右,不到五六米拐入一条迂回转折的悠长巷道里,继续走了十来分钟,然后静候在一处隐蔽地点,抽烟歇息片刻,没有发现尾随者,这才放心地从另一条巷子返回了街头那个米糕摊子。
那人已经买了几块米糕,借着买烟坐进了对面小店里,喝着茶面带笑意望着他,轻轻咳嗽一声,和小店掌柜的说:“这烟不错,吸起来让人有精神,又不呛口,比大炮台还要好!”
老板笑道:“是的,价钱还便宜呢。两盒抵大炮台一盒,还是马儿好啊!”
繁盛过街,伏在柜台上,笑道:“王老板,烟卖完了没有?我那粮行里还有百十盒存货,看样子,又要出城去进货了。”
店老板是从繁盛那儿进的货,听他这样说,着急道:“那您那些存货就甭要给别人了,我全要。只不过……款子可能要赊个三成,半个月后还清。行不?”
繁盛点头,也坐进去,佯作惊讶道:“原来,李兄也抽这烟。足见货好自有知音客。”
那人正是李明善,呵呵笑着作揖说:“几天不见,周兄憔悴了不少。事物繁忙吧?”
繁盛长叹一声,感慨万分。
李明善放下手中的飞马烟,从兜里取出盒大炮台来,认准了其中一支抽出来,敬给他说:“抽支烟,去去烦恼,万事皆安了。”
《暗杀》第七章(9)
繁盛读出他的目光中露出的含意,也是一笑,结果香烟在鼻尖嗅嗅,趁着没人注意,将它滑入衣袖,伸手去取过飞马烟来,自取一根,叼在嘴上点起火来,微微笑道:“人不如新,烟不如故。还是飞马吧,我喜欢。”
晚间,吃完饭后,繁盛提前回到了院中,让许怡在后宅陪陪母亲。他拉亮电灯,坐在书桌前,将那跟大炮台烟拆开,掏空烟丝,从中段取出了张折压得紧密的纸条来,展开看去,是一组数字。他转身去拿起那本床头上的沪版杂志来,就着灯光亮处一照,找出了针划的痕迹来,逐一比对,译出了那些密码的含义:
利用有利身份力保人质脱险
繁盛划了根火柴,将这张纸条点燃了丢进烟灰缸里,化为灰烬后,凝神望着这团焦黑的东西出了会儿神。感觉到于公于私,这个指令都是搁在自己肩上的一负重担,无法脱卸了。周家也因为这缘由也拴上了许家的马车,一路奔向深渊。如此捆绑在一起的窘困,令他备感疲惫,脑海中接二连三闪掠过几个方案,都感觉不妥。
正绞尽脑汁时,许怡在院门口同大嫂玉茹道别的声音传入屋来。他去用冷水洗了洗额头,借此清醒一下头脑,放松了情绪,走到门外迎候妻子。
许怡轻盈地走进来,悄声道:“先前,大嫂转告我,说我妈眼下境况尚好,虽然不能出门,但也没有受到日本人的侵扰,你看会不会情势恶化呢?”
繁盛放松摇摇头,说:“这个就难以预料了。也许,他们投鼠忌器,不敢真格地动许家。也许,这仅仅是先礼后兵的招数,达不到目的就会撕破脸皮。他们做得出的!”
俩人正在月下谈话。巷道里传来脚步声,然后是老三繁茂的声音,试探着问:“二哥,你睡了没有?”
繁盛说:“正和你小嫂子在院子里聊天呢,快进来坐坐。”
繁茂踱进院来,见他们脸色严肃,知道是在为许家的处境担忧,不由也叹口气说:“飞来横祸,老大在海陵甚至整个江苏省也是上数的人物,居然也保不了亲戚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
许怡勉强笑道:“这件事,我猜大哥也是尽力了。如果不是碍着他的面子,只怕日本人就抓人了。眼下,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繁盛苦笑,说:“老大也犯着难呢。日本人的饭碗好端吗?弄不好,照样也是完蛋。”
繁茂忍不住笑道:“你们二位倒是蛮体谅他的。门口派来两个站岗的,是他的杰作。他也怕走了小嫂子,没法向日本人交代。一切都是吉凶未卜呀!”
繁盛深深呼吸了一下夜来静谧的空气,仰望着天边皎白的月色,说:“这时候,我倒想起个人来。若是他在的话,说不定还能预见祸福呢。”
繁茂会心大笑,接口道:“你说的是箫老道吧?”
繁盛点头,苦笑道:“这道人却也见机得快,金蝉脱壳而去,不见踪迹了。老大念叨过好几回,你方才也是。若是他在,摇上一卦,心里多少能有个数。不像现在,六神无主、难勘未来呀!”
(六)
就在繁盛、繁茂兄弟俩慨叹箫老道之后的第三天上午,周家大少爷繁昌的炭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大约四十来岁,身穿中山装,头戴礼帽,手中提着手杖,步履甚是轻快,面白唇红,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繁昌不知他的来历,但看其气度不凡,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急忙迎入客厅沏茶招待。
此人稍加寒暄后,从兜内掏出一封信来,呈奉于他面前。繁盛看了看封皮上的落款即笔迹,心中一惊,郑重说道:“原来是李部长荐来的朋友,失敬了。”
这人微微笑道:“人不如新,衣不如故,果然如此。周先生,咱们小别时间不长,居然就不认识在下了,真是令人伤感啊”!
繁昌一愣,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仔细端详一番他的容貌,果然是有几分熟悉,但却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这人也不出言提醒,坐在沙发之中抚摩着手边斜放着的那根手杖的顶端雕像,依旧笑容可掬地望着他。繁昌思忖了良久,从他的眉目间依稀想起个人来,可又不敢确认,迟疑道:“你,莫非是,箫……”
《暗杀》第七章(10)
那人哈哈大笑,站起身来,在他面前走了两个来回,说:“不错、不错,我容貌大变之后,周先生依然能看破端倪,眼光果然非同一般!”
繁昌见他承认了自己的臆测,不觉惊愕非常。他居然就是前些日子悬衣匿迹的箫道人,简直不可思议。此人失踪后不过一两个月,竟然又手持李士群的亲笔信函登门来访,可见其身份非同小可,而且,还分外添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令他如坠云雾之中,难以捉摸此人的底里分量。
他心中嘀咕,脸上却流露出兴奋的神情来,连连请他喝茶,说:“我那两个宝贝兄弟,倘若知道你这样重又现身海陵,不知要吃惊到什么程度呢。”
这人摇手道:“旧时道人已还俗,鄙人姓方,名世成,南京政府清乡委员会清乡督导局一介专员而已。道衣褪去着紫衣,空持残蜕徒悲秋。现在已是春天,万物竟长,欣欣向荣。今人、故人,并非一人。周先生可明白在下的心思?”
繁昌点头,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周某人领教。世上本无箫道人,只有方专员。方专员是督导地方清乡的高参,绝非白云观中摆卦设爻的道士。”
当下,这两人便心存默契,避开了白云观中的旧事,只谈眼前的俗务。原来,方世成是南京汪政府新委任的清乡督导局江北区专员,负责江北区的清乡检查事宜。李士群再三邀请,将其延入帐下,兼带起辅佐江北情报站的工作来,他的出现,令正值春风得意的周繁昌惊疑不定。首先,他难以估摸这位前道人后督导专员的真实底细。再加上此人过去游迹江湖时种种诡秘,更令他心中充满了戒意。其次,李士群让此人来到海陵,插上这么根木杠,是出于何意?对自己近期取得的成果不满足?还是对此产生了尾大不掉的担忧,想再遣人来掣肘,以防自己在江北地面上作大,不听总部的号令?
这位方世成似乎对于繁昌的疑虑没有任何的觉察,好似脱胎换骨样伸展了一下身体,完全没有昔时做道士的老态和稳静。他望着方才一直言不由衷的繁昌,说:“我的督导专员署设在北山寺,和孙良诚的留守司令部在一起办公。周先生何不移驾,一起去坐坐,顺便在那儿喝几杯呢?”
繁昌听他提到北山寺,想到了去年因繁盛旅途被劫一事求助孙良诚的经历,心中油然觉得仿佛是恍若
![[张卓] 暗杀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