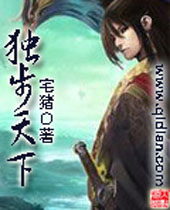危险的脚步-第2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秸呙遣豢赡茉诘碧焱换鞯巧隙シ逯笤俜祷鼗赜辽傩枰谥型竟灰梗樟巧秸呙切藿ǖ恼庾皇杖∪魏巫∷薹训摹案呱铰霉荨保耆且恢稚缁岣@乱怠! �
20世纪50年代,我国登山运动员在高加索学习登山技术时,也有十几位中国人曾在这里过夜。里边只有一些木制床和桌椅,做饭要靠自己随身所带的煤油炉和食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防风抗寒的休息站而已。但是第二次大战前的法西斯军事特务也以登山者的身份多次前来攀登厄尔布鲁士峰,他们也看上了这个“高山旅馆”的战略重要性,前边所讲过的1942年8月21日率领德军高山部队占领厄尔布鲁士的两位军官库马罗和盖马拉上尉,就是1934年到1937年多次前来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的军事特务,他们对上山路线、气象条件、地形早已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专门对攻占这座欧洲最高峰进行过多次演习,所以后来才极为顺利地占领了它。而苏军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命令仅仅只有夏装和一般常规武器的苏军夺取被占领的厄尔布鲁士,从而招致了极大的损失,战死的、冻死的不用说,许多指战员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就冻掉了双手和双脚。所以说登山运动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军事体育性质。
厄尔布鲁士总是给人一种危险的错觉:伸手可及
中韩联合登山队从6日开始适应性行军训练,并由一名俄罗斯高山向导负责。向导名叫阿里,40多岁,在厄峰已经做了20多年登山向导,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尤其是对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现在李致新他们才明白韩国队不着急的原因,原来他们把登山的宝押在这位教练身上。第一天行军的垂直距离只有200米,距离约12公里,时间用了6个小时。
湍急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绿色的山野、白皑皑的雪山,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登山,而是在旅游。李致新不停地说:“这里的山太美了,怪不得欧洲人愿意登山,欧洲出这么多登山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我天天都愿意登山,我要当欧洲登山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行军的距离和高度比第一天增加了许多,也听不到李致新嚷嚷着要做欧洲式的登山家了。就看到他一个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缺乏训练的后遗症在李致新身上显现出来。
3天的行军除了高山适应性得到加强外,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韩国队员和厄峰的情况增加了了解。韩国队员中有4—5人登达过8000米的高度,尤其是韩国队厄尔布鲁士队长张炳虎曾登顶世界第一和第二高峰珠峰和乔戈里峰。
从实力上看,登顶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厄尔布鲁士变化无常的天气,需要登山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而他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按照计划,12日他们将撤离厄尔布鲁士峰。也就是说,12日之前如果没有好天气,他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的出现。阿里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9日,他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米,然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他们送到4200米。到达营地后,跃入眼帘的是一座由铝板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个三层楼房,有60间6平方米大的房间,每个房间有4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平方米,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20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休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王勇峰和李致新商量,12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李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了,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眼前。除了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种感觉就是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他俩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10小时的攀登时间呢?他们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小时登顶,1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
当他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的天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雪中迷路失踪。他们必须听从熟悉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到达4900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王勇峰对韩国队长说,登山计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还给他列举了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他们对韩国队长说: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还是睡不着觉。10日凌晨3时他俩起来开始摸黑做早饭。3时半,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他们不要单独行动,他们答应,如果天气不好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了。
4时半,李致新、王勇峰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他俩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面前。为了尽快登顶,他们没按登山常规1小时行军休息1次,而是连续走了3小时。
大缓坡翻了无数个,可就是翻不完。突击营地倒是离他们越来越远,而顶峰离他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出了错。看来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
这时候,李致新脸上出现了倦容,脾气也变得暴躁了,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雪太深,看起来是耍脾气,其实都是疲劳的症状,王勇峰把重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包里,并且独自承担起开路任务,希望以此来减轻李致新的疲劳程度。
这段时间,王勇峰的训练没有中断过,可李致新因为公务缠身,身体状况明显不好了。
1997年·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1997年 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3)
在无尽无休的路线上,韩国人劝王勇峰: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
6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他们到了海拔5300米的位置:厄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李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了,李致新出现极度疲劳。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迅速降低而死亡。
王勇峰给李致新做着工作:“千万别睡呀。”李致新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睡觉。”
没有办法,王勇峰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两人身上所有保暖的衣服都给他了。李致新睡着了。
王勇峰在一边冻得来回跺脚,每隔5分钟就去摇摇他,以防他真的睡过去。
看着雪地上睡着的李致新,王勇峰突然感到了恐惧,如果他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王勇峰不敢想下去了。
20分钟一到,王勇峰赶紧把李致新叫起来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王勇峰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跟上来了。王勇峰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高山适应吗?那人说,看他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王勇峰一听,心里算是有了点底儿,李致新真的走不动了,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
看着歪坐一边的李致新,那个韩国队员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吧。王勇峰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王勇峰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
王勇峰开始和李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李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他建议王勇峰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等着他们回来。
王勇峰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你在这里冻成了冰棍儿了。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怎么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也难过,但看到这个时候李致新已经脱离了危险,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正做着下撤的准备,李致新说,现在感觉好点儿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可这时候王勇峰已经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想着李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拒绝,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李致新体力的恢复让两个人都看到了希望,抬腿就走却忽略了一件事,李致新垫在身下睡觉的一件风衣被丢在了雪地上,王勇峰本来要把这件衣服留作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纪念的,却丢在了七大洲的第五站了。
攀登厄尔布鲁士最难的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到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大坡。30度的坡度对登山者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经过李致新这么一折腾,王勇峰也开始感到疲劳了。让李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
每当他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一把
李致新和王勇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座”、“登山福将”。
王勇峰经常爱引用一位登山家的话:登山的伙伴有时比妻子还重要。这也是他们20年的感受。登山中,对伙伴的信任是成功与安全的根本。登山最忌讳的就是和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一起登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烦恼,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登山已经显示出了队伍简单的组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王勇峰也总说,和李致新在一起登山我的运气总是特别好。在旁人眼里,他们确实是一对天才和汗水的组合,李致新的判断力与决策力无论是在登山过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极其鲜明地显示出来,而王勇峰的坚忍和执著都是常人极难相比的。
当然,他们自己也总结了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上天”总会帮他们一把。其实,更应该说,每一次都是他们的决心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感动了上苍。
也就在他们眼看着登顶的希望一步步远离的时候,眼前一亮。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两位“苏联老大哥”,他们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把最后300米路踩出来,他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他们的狼狈样,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上天又一次拉了他们一把。
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他们一步步向顶峰迈进。
大坡到了尽头,顶峰已近在眼前。
李致新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
6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6分,王勇峰手中的摄像机出现了李致新和两名俄罗斯人,一名韩国人,在欧洲的最高峰上,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高点上。
图片说明
■ 高山适应途中的王勇峰
■ 远远望去厄尔布鲁士总是那么迷惑人仿佛伸手可及
■ 中韩队员在进行高山适应。
■ 观察路线。
■ 突击营地是一个大碉堡一样的建筑。
■ 正是成功渐成泡影的时候,“苏联老大哥”(中间两人)如同神兵天将出现在眼前。
■ 在厄尔布鲁士顶峰上展开国旗的时候王勇峰眼睛湿了
■ 同以往一样顶峰上的李致新泪流不止对着镜头他说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上来的
1998年·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998年 乞力马扎罗·浪漫的旅程(1)
乞力马扎罗 非洲最高峰 海拔5895米
南纬 3度东经 37度05分
1998年1月7日7时40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知道豹子为什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这是他们在非洲一直问自己的问题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
1998年1月5日晨7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站: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