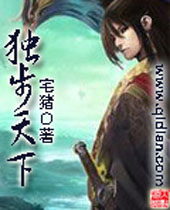危险的脚步-第2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5年·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 1995年 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1)
阿空加瓜峰 南美洲最高峰 海拔6964米
南纬 32度39分西经 70度
1995年1月9日12时5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这给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带来一个改动
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加拿大人兰迪的时候,我就怀疑他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因为即使是在冬天,他也要把强健的肱二头肌露出来,摇头晃脑地要和人摔跤。1993年到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教英语课的。
果然,他是一个让人不太放心的老师。当年的很多学生还记得这个“外教”,因为每次在课堂上不能提起“登山”二字,只要有了开头就没有了结尾,他可以把整堂课和课间休息时间都让给这个话题。他喜欢北京喜欢得要命,当时的梦想就是卖掉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建一个攀岩馆。课堂上也总是要和学生们讨论这个理想,学生们一看和老师实在是话不投机,就给他介绍了李致新和王勇峰。
见到李致新、王勇峰那一刻,兰迪封存了自己的梦想,不建攀岩馆了,要和他们去登山。
2001年,我在北京一个吃烤鸭的小饭馆见到兰迪时,王勇峰指着他介绍:这是加拿大彪,兰迪。
因为兰迪的原因,他们南辕北辙
彪乎乎,是大连的一个俗语,形容人很鲁莽,天不怕,地不怕,被李致新引进了中国登山队。这个本来是贬义的一个词却在登山队备受欢迎,每个人都自诩为“彪乎乎”,还因此形成了一个“彪团”,在运动队,无论教练还是队员都以年龄排序,互称大彪、二彪、三彪……王勇峰是三彪,李致新是四彪,王勇峰尤其喜欢“彪乎乎”这三个字,连自己的女儿也被他叫做小彪乎乎。
登山队的老教练刘大义给了“彪乎乎”一个最好的诠释:没有点彪乎乎的劲头是登不好山的。
1994年,王勇峰给了加拿大人兰迪这样的解释:“彪乎乎”意味着特别勇敢,特别热情。兰迪爱死了这个词儿,非让大家从此也叫他彪。
一定要说说这个“彪乎乎”兰迪的故事是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谜底。那就是,1995年1月,李致新、王勇峰去炎热的南半球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时候,为什么要先飞去寒冷的北半球的加拿大。
还要从1994年说起,兰迪一见到李致新和王勇峰就决定了要和他们去攀登阿空加瓜。当时,这两个人正在为经费的事情头疼,兰迪说他也不要教书了,回国找赞助去。
为登山的经费筹集和繁复的申请准备发愁,这是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有着共同的困难。在日本,从事摩天大楼外墙清扫的专业人员中大多数是业余登山家,据说,这不仅是筹集登山资金的好办法,也是攀登悬崖峭壁的一种特种训练,无论是系绳的技巧还是臂力、腿力的锻炼,据说登山和擦玻璃原理相同。他们擦玻璃挣了钱去登山,登山回来再擦玻璃为下一次做准备。
对于这种烦恼,兰迪很熟悉,他一回国就寄出了100多封信,在漫无目标的等待中,加拿大航空公司回信了,他们愿意提供所有人员的优惠飞机票,但没有直飞的,要先到加拿大,再转机去智利。
北京这边也有了好消息,北辰体协拿出30万元资助这次攀登活动。在国内,企业赞助登山这是第一次,那个时候人们对登山的理解几乎是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苦,登山能得到什么?这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也是哪个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次和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的合作也是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让人难忘。
1994年12月3日,北辰体协南美登山队终于出发了。领队是北辰体协副会长白建强,三名队员: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
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刘文彪跟随李致新和王勇峰采访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时是个随队记者的身份,而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的,正式队员。这个身份让他很骄傲,他在《踏遍艰险人已归》的系列报道里写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为此激动难眠,一心想成为第一个登上一座独立山峰的中国记者。
似乎每个采访过登山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是以一个观察者采访者的身份登山,但很快,他们难以自拔,要成为其中一员,成为一个真正的攀登者。当然,很难有人能逃脱这种命运。
“登山是一种甜美的苦役,”刘文彪总这么说,“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山就是为了等待我,而在那里历经沧桑几千万年。”他妻子冥子说,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登山了,刘文彪会拿出在山里用的头灯和冰镐,细心地抚摩着。随后,拿起雪杖,在家里煞有介事地一步一步走着,尖利的雪杖把地毯戳得满是印儿。冥子有句名言,被很多登山队员的妻子所引用,“为妻子的我是嫉妒山的。然与其嫉妒,不如和丈夫一起爱山。”
因为他们的这次攀登,
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从1995年开始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动
1994年12月28日,在兰迪的故乡,加拿大埃德蒙顿进行了三周的攀冰训练之后,白建强、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和兰迪及他的朋友达戈组成的登山队飞向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这里进入阿根廷。他们飞行了18个小时,2万公里,经历了春夏秋冬。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00分,在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属于阿根廷,靠近智利,海拔6964米,是与珠峰遥望的西半球的最高峰。
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空加瓜之前,除了它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两位登山家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年,国内出版的地图上,南美洲的最高峰还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而不是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即使是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也是如此——汉科乌马峰的标高略高于阿空加瓜。
出发之前,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南美洲最高峰的分歧很早以前就存在,可到了1994年,世界上的认识基本统一:南美洲最高峰是阿空加瓜。各国登山家也都把阿空加瓜作为南美洲最高峰来攀登。
当时,李致新和王勇峰,包括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当年,青海的玛卿岗日还曾经被美国人测量成9000多米呢,随着人类的攀登和测量技术的发达,很多模糊的概念就慢慢清晰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件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
成功攀登了阿空加瓜之后,国内很多媒体做了报道,“中国登山家登上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引来了很多读者的抨击,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连最高峰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瞎登什么山呀。”读者来信越来越多,中国登山协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了。
联系地图出版社的时候,热心的编辑端木先生接待了李致新,看过了李致新收集的各方面资料之后,端木先生还把出版社一张珍贵的藏品地图拿了出来,和李致新带来的资料进行比较。
地图出版社发布地图信息是根据各国对外发布的资料而来的,在阿根廷之前,玻利维亚就已向世界发布了南美洲最高峰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虽然汉科乌马峰和阿空加瓜同属安第斯山脉,但他们每一次公布的标高都要比阿空加瓜稍高一些,因此,地图出版社始终都是尊重这一资料的。
但是,地图出版社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次在国内引起的争论,出版社特意和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联系,咨询当时的情况。玻利维亚大使馆确定:南美洲最高峰的确不是汉科乌马峰,此前的测量有误差。
多年的一个悬案有了定论。从此,中国出版的地图,从1995年开始,从地图出版社开始,全部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动:南美洲最高峰是海拔6964米的阿空加瓜峰。
两位登山家攀登阿空加瓜而引来的一场风波也由此落定。
1995年·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 1995年 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2)
在阿空加瓜,每个登山者出发时都要穿越60位先驱者的墓碑
阿空加瓜峰是一座闻名世界的险峰,自1897年1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登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在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脚下的那60座墓碑,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在世界最著名的最艰险的三大陡壁中,阿空加瓜的南壁位居首位。愈危险愈有魅力,这似乎是登山中的一个法则,但,来的人多,归的人少,这使得阿空加瓜的攀登史成为一部壮烈的英雄传奇史。
李致新、王勇峰此次选择的路线是阿空加瓜的西北壁,虽然没有南壁那么危险,但路线漫长,尤其是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高差为1100米,往返需要十几个小时,对于攀登者的体力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虽然从这条路线上达到了顶峰,却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遇难。就在出发前两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阿空加瓜遇难者的照片,他头枕着登山包,左腿跷在右腿上,安详地躺在顶峰上。他就是登顶后体力耗尽无力下撤的,这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年仅28岁。
阿空加瓜山脚下的60座墓碑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命运如此,那些墓碑上镌刻着遇难者的姓名,但大部分没有遗体。那些墓碑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每一个上山的人都要穿过这片碑林。
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小镇出发,需要走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第一天的宿营地设在海拔3300米,路程是8公里,要走8个小时。
大批的登山物资由骡子运输,大家自己背的只是帐篷、睡袋、食品和路上要用的个人装备。就这些东西,每个人一米高的大背包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再加上绑在背包上的海绵睡垫,背包的人都被埋在了背包下面。
刘文彪提起自己的背包掂了掂,足有40多斤。
他看着大背包有点发愁。出发前,他也每天进行了强化训练,背着五六十斤的书,从1楼爬到13楼,再从13楼跑下1楼,如此往复,一天七八趟。但今天,看着这硕大的背包,他还是有些犯憷,背上40多斤的包走8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他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前几天,在加拿大攀冰训练的时候,汽车差点翻了,他的肋骨撞在了一个箱子角上。从那以后,一碰受伤的地方就疼。到了出发这会儿,索性不能大笑,不能咳嗽了,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能颠着。
李致新和王勇峰很担心刘文彪的肋骨,一直在问:“怎么样,能上山吗?”对于刘文彪的实力,他们不太担心,毕竟在麦金利已经有过考验了,但刘文彪的伤势他们实在心里没有底。
刘文彪心里还算有数。出发前一天,他给自己上了一贴膏药,出发的时候,已经感觉好多了。他对着背包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把所有的东西又都拿出来,斤斤计较地开始精简。毛袜子、毛帽子先拿出去,估计3300米的地方还能抗,头灯的电池由8节减到4节,两支圆珠笔减成一支,两个小药瓶拿掉,倒出几粒药装进一个小塑料袋里……
领队白建强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他身材瘦小,且常年坐办公室,平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训练的,让他连续不停走8个小时就是个考验了,更何况还要负重。白建强一句话也不说,任由王勇峰把背包背在他的背上。他的包相对轻一些,也就30斤。
李致新和王勇峰背包的重量要远远超出刘文彪和白建强的,那小山一样的大包他们似乎没有放在心上。
攀登是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向上开始的。山谷两侧陡直的峭壁像两扇打开的门,门的中间是一个清澈的小湖,湖水的四周是嶙峋的石峰,湖水的中央,一座山峰清晰的倒影,那便是阿空加瓜了。抬眼望去,洁白峭立的阿空加瓜南壁顶天立地地盘踞在奥考尼斯山谷的尽头。
1月份,北京还是隆冬,但此时的南美大陆则是最炎热的夏天,但大家出发的时候,还是都穿着风衣,并不是因为怕冷,而是为了挡风。阿空加瓜的高空风是最著名的,狂风带来的滑坠和冻伤的例子有很多,风,是阿空加瓜攀登者最大的威胁。
人在山谷中行走,阵风来时飞沙走石,吹得人打晃。奥考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