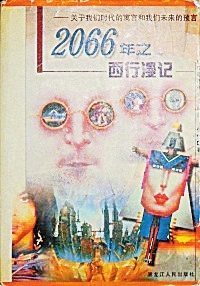3366-绿色安息日-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快乐的天堂。母亲则坚信“天堂”这个字眼在道德上所有的意义,但她是个无神论者,宁可相信山里的神仙和美人鱼,也不相信任何神明。当母亲把我支遣上床后,父亲总会蹑手蹑脚走上楼,每当我挺直腰干,双手合握,向上帝祷告时,他就坐在床前,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股温暖而喜悦的感觉。就在此时,我们便会经常听到这栋18世纪老屋的木梯发出吱吱嘎嘎急促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是母亲站在房门口,正等着父亲离开后熄灯。有一回,我听到她在问:“看你在教那孩子什么废话?”
我一个人被留在黑暗的屋里,怀疑着到底谁才是对的。祈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父亲那种单纯的信仰所带来的温暖,有时会穿透我全身,但母亲冷静的科学思维,则让我变得很理性。有时我害怕独自睡在这古老的大房子里,虽然我不相信巫婆和魔鬼真的存在,但总是会梦到。
尽管我分享了父亲对自然的热爱、母亲对动物学和原始部落的狂热,但我却明白,为什么他们对当代人类切断与自然界关系所作的抉择,保持着如此高度的热忱。他们是不是被达尔文所勾勒的死后情形吓倒了?他们准备迎接祖父母那一代生长的世界所发生的任何改变,并且把这种改变称为“进化”,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改变。“进化”等于是与自然保持距离。设定好进化路径的成人,利用他们的能力来发明及改造现存的世界,急于前进,却没有为最终的架构规划出蓝图。一个人造的环境是显著的目标———然而由谁来负责建造呢?我的国家中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人既不是英国国王,也不是美国总统。每个打造明日世界的发明家和制造者,只不过是针对个人所擅长的事,抛块砖或丢进一个齿轮而已,而结果如何,完全要靠下一代的我们来发现。
学校教导我们,人类的大脑大约十二岁就会停止发育。然而,现在我们已经十六岁了,还是被当成只有半个大脑的人。成人只是把我们刚发育成熟的心智推进教育机器,塞满老一辈的教条,他们怎么会相信以我们的年纪,思考可能比他们还清晰?就是“现在”,趁着我们还年轻,我们必须思考;就是“现在”,我们必须加快判断是否要被推进成年人那班没有动力的列车,盲目接受他们的安排,对号入座。
在学校里,谈论进化的主题是用一种不直接且不实际的方法。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来自天堂的进化。老师好像在走高空绳索,一手拿着《圣经》,一手举着科学,左摇右晃。他们成功地延伸了上帝的意义,看起来好像是上帝曾经找出创造人类的方法。达尔文已发现上帝是先创造猴子,再利用进化的方式将它变成人类。人们也认为,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世上所有生物。但《圣经》也提到,对上帝而言,一天等于一千年,一千年等于一天。爱因斯坦同意时间有相对性;时至今日,成人也都同意这说法。自然科学曾经得到和数千年前的《旧约·创世纪》相同的结论:地球上的生命从海洋开始,而非陆地。当时,海水里充满生命,空中充斥着长翅膀的生物。后来有那么一天,爬虫类和地球上的种种生物,开始爬到干燥的陆地。写《创世纪》的不知名的圣哲甚至主张,这个世界充满动植物之后人类才出现。在那之前,所有的事物都已经开始运转,所有的生物也各自具备功能,不需要花工夫就有自己的肺脏,有自己的心脏,有自己的感觉,有自己的大脑,也开始交配繁衍。
天堂设计复杂,没有任何错误,这一点,即使《圣经》和科学也是一致的。上帝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十分满意,他发现这世界十分美好,所以在第七天停止工作,开始休息———留下赤裸裸的人类。不过,就像之前的各种鸟类或动物,上帝也充分供应人类生存所需。
根据科学的说法,如果自然界不供应人类生存所需,人类不可能从兽类展开进化。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广为各方认同。
然而,虽然上帝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人类却不这么想。上帝确定自己已经给人类一个完美的环境,一个人间天堂,但人类并不赞同。当上帝休息时,人类接管一切。人类想要进步,再一次为进步而远离天堂。
人类和上帝一样工作六天,并认为如果在第七天休息,可以取悦上帝。尽管人类曾争辩过星期天(或是星期六、星期五)是否要休息,不过,不管是基督徒、犹太教徒或回教徒,都会在第八天急于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奋斗,以便制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这样,人类发展了几世纪、几千年。
第一部分进化的迷思(2)
上帝没有想过要发明炸药。当他看到我们做到的事,是否会了解自己的短处呢?他是否同意我们将他所完成的一切,几乎全都加以改造?信仰宗教的成人似乎相信,是上帝导引我们的脑子,让我们确定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步骤都是为了进步。然而,我们也被教导过,上帝已离开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的星球负责,他赋予我们建造和破坏的能力与自由,让我们前进、后退,让我们欢乐、受伤,单纯地运用曾经被赋予的智能、直觉和良知来导引自己。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在我们死后,上帝会依我们的行为来奖励或惩罚我们,这件事也一定是真的。然而,真正让我困惑的是成人所说的:上帝曾经创造自然。因为成人表现出来的行为,仿佛是脚下被邪魔恶鬼缠住,除非斩断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无神论者也讨论过,是自然界创造了人类,但是他们的表现,似乎把自然当作人类古老而天生的敌人。
十六岁那一年,我开始觉得不安,对成人的信心产生动摇。他们并没有比小孩子聪明多少。即使对某些观念不认同,他们也容易受困于那些观念而显得僵化。他们正把我们拉向一条目的不明的道路,没有目标,只想逃避自然。一场恐怖的战火最近正在蔓延。如今他们发明了新式武器,却比以往的武器更糟糕。不论是政治、道德、哲学或宗教都遭到否定,追随着这样一个世代的脚步,谁会感到安全?最好能开始寻找一条安全的支线!我开始像一名罪犯,想悄悄地跳离这列走错轨道的列车。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人会想到违背父母或学校的意思。我对自然史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不只看到大自然的美,也看到构建这世界背后的超凡智能。不论何时,我都会尽量亲近森林、山岳和开阔的海岸,并且对那些把人类带离自然环境的文明趋势心生怀疑。我们是不是正在做一些疯狂的事呢?
最后,我必须把不断滋长的不安和某些同龄人分享。有一天,在体育课之后,全班都在更衣室,我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
“我不喜欢机械。”我脱口而出,对坐在身边正拉扯衬衫的男孩说话。
“不会吧?”他只用一种傲慢的表情回敬我,并轻蔑地笑着。这话让我很想爬进正要穿上的鞋子里,在头上用鞋带打个结。我说的是一些十分荒谬的话!我嘴里再也吐不出半个字。
不过,班上有个男孩阿诺·杰科比(ArnoldJacoby),慢慢让我觉得可以向他吐露秘密。他是个高大的家伙,不像其他人喜欢运动,也不像我一样喜欢在树林里漫步,而是喜欢读书、写诗,沉缅于哲学的梦境。我渐渐敢向他开放我的心思,他也瞪大了眼睛听我诉说。我告诉他,我打算抛弃一切,所有的一切,去某处热带地区寻找自然,在那里,人们从树上就可以摘取食物。我不打算在欧洲度过自己成年后的生涯,在这里,灾难正潜藏在角落,20世纪的理想之塔不是正要倾倒,就是会把人类带向另一场恐怖的全球战争,我们最好躲得远远的。自此以后,我开始有了可以倾吐心声的对象。
这个美梦如何成真?缜密的准备是必要的。首先,我必须锻炼身体,改变多病的体能状况,因为前方将有苦头等着我。我的另一个朋友艾立克(Erik)是个高大粗壮的家伙,初中毕业后,他曾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到海上跑船。为期两年的海上生涯,带给他我正需要的那种肌肉。艾立克对当代的进步也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一直幻想在非洲中部或巴西的马托·葛罗索(MatoGrosso)高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区。我的野心没有那么大,我只想找个愿意跟我一起分享这种亲近自然的实验的女孩。
和艾立克及其同伙在一起,我开始接近运动:在森林里越野赛跑、下雪天就去滑雪。寒假里,我们开始进行一些当时在挪威十分罕见的运动:把帐篷和食物放在雪橇上,拖着前进,然后到蛮荒的山里住几个礼拜,远离人群。很快地,我们出门不带帐篷,而只带着向居住在遥远北方的拉普人(Lapps)买来的温暖驯鹿皮睡袋;我们在已经半硬的雪地上,替自己挖个舒适且可挡风遮雨的洞穴,或者把雪切成一块块冰砖,建造爱斯基摩式的冰屋。旅费都是靠我写些关于探险的文章赚来的,其中搭配了照片和插画。后来,我从一名挪威运动员马丁·梅伦(MartinMehren)手中得到一只西伯利亚爱斯基摩犬(Siberianhusky),那时,他刚带着狗拉雪车和雪橇,从横越不知名的格陵兰中部地区回来。得到这只狗,使我们的山中探险走得更远,也更加疯狂。我们替这只狗取名卡山(Kazan),靠它拉着我们的粮食前进。冬季,艾立克和我建造可供休憩的冰屋,甚至有时在挪威最高峰和最高的冰河区罗丹峰(Rondane)与约顿汉门冰河(Jotunheimen),我们也这么做。透过冰屋的门口,可以看到黄昏或月亮升起时,脚下世界那种令人屏息的景象。只有在这样的荒野假期,我才能真正感受到宁静。更棒的是,在蓝天之下,林梢之上,我真实地感觉到,我正在世界的顶端。在这些假期中,我们亲密地接近所有与大自然结合的元素,这些进入荒野的旅行经验,以及我从母亲馆藏丰富的私人图书馆里读到的原始文化资料,对我来说,比学校教科书还具诱惑力。我的高中成绩平平,不好也不坏,惟独自然史例外。我并不在意成绩,只想知道如何更友善地与自然亲近,以及在这个比较单纯且所有人都只是自然产物的环境中,人类与动物如何繁衍。
女孩也是我所渴求的自然产物。我对她们有极高的兴趣,但是我太害羞,不敢接近她们。打从孩提时代被父母强迫参加三期舞蹈学校的课程起,我就不敢和异性交往。她们那么神秘,不像是真正的人类,令我不知如何聪明地与她们交谈。不过,在这迷人的族群里选到一位可相伴同行的人之前,我绝对不会回归自然。
第一部分准备圆梦
在某次毕业舞会中,我在峡湾码头上的一家餐厅遇见了里芙(Liv)。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学校生活已经结束;除了我之外,大家都在跳舞。我独自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望着随着小船行驶在黝黑海水上闪烁摇晃的月光。突然,我身边多了一个同伴,他从别的镇上载来了一名我不认识的女孩,浓密的金发,快乐的蓝眼珠。对不起,我不跳舞。那么散散步吧?不想?那我们聊聊天吧!好啊!话匣子被打开,从笑话说到哲学。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实在值得我一试。
“你对回归自然有什么想法?”我幽幽地问。
“我们必须这么做。”她坚定而毫不犹豫地回答。
成功了!她抓住重点了!
这个女孩将会分享我的实验。在前往奥斯陆接受大学教育之前,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我依照意愿,将学习动物学和地理学;而她则被父亲强迫,学习让我害怕的社会经济学。我主修动物学的目的很明显,选地理学则是为自己的实验作准备,以便找到可以进行实验的地点。我对原始部落和外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我的焦点摆在波利尼西亚广布在东太平洋各岛屿上的史前人类。然而,如果我在任何大学修人类学,学到波利尼西亚文化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小时。幸好我的运气不错,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全世界有关波利尼西亚最丰富的图书文献收藏,属于一名住在奥斯陆的富有的挪威酒商毕亚讷·克罗匹林(BjarneKroepelien)。他年轻时曾在大溪地最伟大的酋长提利尔卢(Teriieroo)家里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回到欧洲之后,便开始搜集所有波利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相关出版品,不管是哪个地方或哪个时代印刷出版的。我告诉克罗匹林我们的秘密计划,这激起了他的兴趣。他让我使用他的图书馆,待我宛如家中的孩子。虽然我正式的专业
![[133]妃子笑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