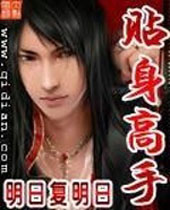邪派高手-第16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老头设了两个炉,一个是用来烧鸡和烧果狸的,另一个是用来煮蛇羹的,他边做边唱歌,他唱的是山歌,是两广一带常常听到的山歌。
小老头的歌唱得并不好,但他的烹饪手艺可不赖,一阵阵烧肉类的香味随风四插,首先嗅到的是凌起石,他一连吸了几次气,实在好闻,垂涎了。他轻轻揉拍着吕玉娘的肩胛,在她耳边低声说:“玉娘,快醒醒,你师父的手艺真好,你嗅一下,多香!”
吕玉娘惺松着眼,撒娇地说:“你干什么吵醒人家,我不饿,我要睡觉。”她并不肯坐起来。
“你还说不饿,你听,肚子咕咕叫啦!”
“你真是,我说不饿,就是你嘴馋,想吃……”吕玉娘在一阵吹过的风中也嗅到了香味,不错,确是很香,她却不肯承认,轻打凌起石一下说:“都是你,吵得我无法再睡。”
两个人拉着手,循着香味找去,只见得小老头自唱自听,自得其乐。
吕玉娘道:“大哥,你知道他唱的什么?”
“他在唱我们,你听,他说你又懒又贪睡,将来会变成大肥猪……”
“胡说!你骂人,我不依你!”她打他,他并不回避,却呼痛,还皱眉头。两个人闹着,玩着,很是开心。
老头子见到他们,高兴地说:“你们来得真合时,我一切全制好了。你们看着,不要给野兽撞泻,不要给烧焦就行了,我去洗个澡,等一会回来就可以吃了。”走了几步,停下来又回头说:“小心点看着,刚才我看到有耗子,别给耗子偷食了。”
小老头去了一会凌起石忍不住了,刚要撕一支鸡翅吃,吕玉娘“嗤”一声笑说:“大哥,有耗子偷食了。”
“这是一只不怕人的大耗子呀!”他一把搂住她,亲她一下,她只是笑,没有躲避,凌起石把鸡翅塞到她嘴巴里,笑着:“让耗子先尝尝味道!”
小老头回来了,并没有责备他们,却把一些蛇羹给小猿,鸟是吃鸡肠吃够了。
三个人围着火,倒是别有风味。
吕玉娘真会逗小老头开心,不断赞他烧得好吃。小老头开心透了。那只小果狸首先被吃掉,然后是鸡,一锅蛇羹实在太多了,怎也吃不完。
凌起石想起了杜松龄,说他应该是醒转的时候了,怎么还是无声无色?他去察看,原来他已经坐了起来,正在那里饮泣,泪流满面。
凌起石见状,吃了一惊,以为他又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替他诊脉,却是十分正常,更觉得莫名其妙。
杜松龄为什么如此伤心呢?原来他是感怀身世,也觉得惭愧,凌起石劝他不要婆婆妈妈,要有男子气概。
凌起石说怕吵醒他,所以不早叫他,替他留下一碗蛇羹,请他尝尝小老头的烹煮手艺。
杜松龄对于蛇,他本来不敢吃的,但见各人都吃,他也想尝试,但他才吃了一口,很快就把蛇羹吐了出来,脸色也变了。
“就是这些,我记起了,也是这个味道的!”杜松龄叫道,神情十分激动。凌起石色然而喜,道:“杜兄,如果真是这个味道,就好办了。你不用急,也不用怕,再试试,细心点,慢一点,看看有什么不同。”
杜松龄面有难色,但他发现凌起石是那么兴奋地等着,他点头同意再试。他自己告诉自己,这是解药,是试探自己中毒情况的药。但是,尽管心理上有此准备,仍然抵受不住,吞下去,又吐出来。
“杜兄,请你忍耐一下,再试试。”凌起石说。随后他问小老头制蛇羹的配料,然后把每一样配料分别给杜松龄吃,他都没有反应,唯一有反应的是蛇,不但吃不得,嗅到蛇皮蛇骨的腥味也受不了,要作呕。
于是,凌起石得出一个结论:杜松龄中的是蛇毒。
他说:“如果仅是蛇毒是容易医的,就怕不止一种毒,不过,见一步行一步,医好了蛇毒再说。”他说完,马上就去找治蛇草。
什么叫治蛇草呢?原来有这样一个传说:凡是毒蛇出没的地方都有一种足以疗治该毒蛇所伤的草药,所以叫做治蛇草。
凌起石去找了一会,果然找到几株不同的治蛇草,捣烂榨汁,给杜松龄喝下去。
杜松龄喝下之后,泻了几次,精神反而好了许多,他试行运功,也较为畅通了。凌起石替他把了脉,皱了眉头道:“不错,你的毒是清除不少,虽然末除尽。仍有蛇毒在,却已较淡得多了。再说,所留存未清的毒,相信不会是蛇毒,不同的毒要用不同的药去解,杜兄,你且安心,有机会时,我们再行疗治,现在急也没有用。”
“我明白!”
凌起石道:“我有点奇怪,你不该醒得这么快的,但我似乎又觉得你应该在这个时候醒的,所以我才来看你,而你果然醒了,这其中必有道理,但我不明白。”
“我是睡着的,但不知怎的我觉得周身有很痒的感觉,我就醒了。”杜松龄说。
“晤,原来是这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中了蛇毒,白天是没有什么,毒蛇是多在夜间出动的,我们杀蛇烧蛇羹,你的感觉就更烈,就是这原因!”
“凌大侠,你的意思是,若果碰到其他与我的毒有关事物,我也会有反应?”杜松龄问。
“不错?可能是这样,杜兄,你真聪明。”凌起石说。
“杜大侠,你吃不得蛇羹,我们又没其他东西留给你,怎么办?”吕玉娘说。
“不要紧,我不很饿,平时也不习惯午夜吃东西,你不必替我为难。”杜松龄说。稍顿之后,又道:“我现在已经好了许多,这地方我住了两年,最熟悉了,天亮之后,我陪大家走走,看看这石林的秘密。”
“秘密?有什么秘密呢?”凌起石问。
杜松龄道:“有的,有许多秘密,我初时也不知道,后来实在无聊,远的不能去,只好在这里转呀转的,结果,给我发现了不少秘密。”
“什么秘密?”吕玉娘问。
“黄金、白银、珍珠、珊瑚之类。吕女侠,你想不到吧!在这众多石山当中,居然有金山银山,它不是天生的石山,而是人工制成的金山银山,里边还藏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你说算不算秘密?”
“这就奇了,不知是什么人藏的?”
“我也不知道。”
“这秘密,老毒物可知道?”凌起石问。
“相信她未知道。”
“我也这样想,如果她已经知道,你就活不到现在了,杜兄,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凌起石说。
“过去我是没想过,现在明白了!”杜松龄回忆地说:“怪不得她每次到来,都把我调开,检查我的东西,我因为她是暗中调查,也就诈作不知情,当时我只感到奇怪与不高兴,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危险啊!假如我贪心好玩拿了其中的一件玩物,给老毒物发现了,她一定会严刑逼供,那就苦了!”
“杜兄,你不是说她这一两天就会到来,她会不会已经来了?躲在一旁愉看我们?”
“不会,我的小翠、小袁都没有发现外人,若果有人来,它们会来通知我们的。”小老头很有把握地说。
这一晚平静地过去了,老毒物没有来,一切都平静得很,到了第二天,杜松龄把大家带进石林深处,观察秘密。
各人看见几座山,手艺之精,若非杜松龄预先说明,谁也不易看得出来。吕玉娘到底是女孩子,比较细心,她劝大家不要在那儿逗留太久,以免给老毒物在脚印等细微处看出破绽。因此,他们只在那儿打了个转,便离开了。同时,在其他许多地方都故意留下痕迹迷惑老毒物。他们与老毒物在斗智,要斗倒老毒物,使杜松龄获得完全自由。
第二日的晚上,老毒物来了,跟她一起来,除了那个少妇之外,还多了两个中年男子。杜松龄如常的傲不为礼,怒目相向,老毒物看了两年,早已习惯,不以为意了,但两个中年人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是对老毒物极大不敬,要教训杜松龄。
“你们想怎样?想打架是不是?”杜松龄一派挑战的口吻,使那两个人更难下台了,他们都看了老毒物一眼,她没有表示,其中一个便迎面走向了杜松龄。杜松龄屹立不动,中年人缓缓提起右掌,耳边只听得老毒物说:“不可要他的命!”
“是,我知道。”中年人说。他只把内力提到了七成左右,猝然向杜松龄拍去,出手快极了,而且掌影四晃,令人难以防备。但杜松龄却不畏怯,凝视着,等到对方掌力迫近了,他不但不退,更挺前一步,手中剑“铮”的一声射出光芒,一发便收,对方随着一声狂呼,便留下一只手,倒退回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感到惊骇的是老毒物,她是一个大行家,一看杜松龄的出手就知道其中起了很大变化,杜松龄已经不是受她禁制的杜松龄了。
她感到奇怪,杜松龄怎可以消解她的毒?她一直以来都自视为使毒能手,无人可及,亦无人能解,两年了,杜松龄都无法自解,现在突然解了,一定是有奇遇,她决心要追查明白,因此她喝问杜松龄,杜松龄未答,老头子先回答了,他说:“你的使毒手法是不错,可惜还未到家,如果不信,咱们不妨斗一下!”
“怎么斗?”
“你我先将身上解药丢到水中,然后,你吃我的,我吃你的,看是谁会死去,你看这办法如何?”老头子说。
这确是个可怕的办法,老毒物有怯意了。她佯作沉思,实则已放出虫毒,不料老头子屈指弹处,嗤嗤声中,便见有毒娥坠地,老毒物仍然不心息,骤然打出一大把毒虫,老头子大袖几挥中,一道劲风已射中老毒物,她也真了得,一声狂嚎中,夺命奔逃,迅即失了所在。那少妇也十分知机,逃了,只有两个中年人落在老头子手中。
一场凶险过去之后,老头子除去假发,恢复本来面目,原来是凌起石,杜松龄佩服用得五体投地。
他们料想老毒物半月十日之内不会再来,便一起去龙门看胜迹。杜松龄说他去过一次龙门石窟的,仍记得路,亦大略记得石窟中情景,可以作他们向导。吕玉娘说好,就由他作向导。凌起石笑说:“玉娘,你这不是要走回头路了?龙门在昆明西山,我曾经和你去过,你怎么就忘了?那龙门削 壁巍峨壮丽,气势万千,你还赞它是个好地方,值得一游,怎么现在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吕玉娘听得恍然大悟道:“怎么,就是那个地方?我记起了,登龙门,纵声高呼,可以传出去很远!”
“就是那儿啦,我们已经去过,不必再去了,你要看雕塑,这儿多得很,有的石佛高可数十丈,有的小如指头;有的睁眉怒目,形象可怖;有的慈眉善自,一派祥和,包保你看得高兴。”凌起石说。
“好,我们去看,明天玩一天,若兴未尽,可多玩一天,然后就跟你师父到广西去练功。”凌起石说。
“广西?你们要去广西?好极了,我亦可以作向导。”杜松龄说。
小老头听了他说,问道:“你很熟悉广西?你去过?去过哪里?”
“我过去在桂林七星岩住了几年,我师父曾带我到芦笛岩,他说那儿住着一位武林奇人,武功极高,已到不可测境地,又说金沙洞住着两个恶魔,叫我千万不可走进去!”
“不错,你说得出芦笛岩同金沙洞,足证你是去过那儿,令师是哪一位?怎么称呼?”
“家师人称七星老人,姓名我亦不详。”
“原来你是七星老人的门人,这么说,该是我师侄了,我与令师虽非同门,却时相过从,令师生平只传了两个人,你该是第二个。”
“不错,我是第二个。”
“你未见过师兄?”
“不曾!师父不许我称他师兄,还说纵有见面机会,亦不可认为同门,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
“这事嘛……令师现在哪里?许久没有他消息了。”
“家师现在怎样,我也不清楚,可说生死未卜。”杜松龄说:“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与家师到了贵阳,是去选药制药丸的,不知怎样,家师突然把桌子一倾,菜饭都倒了一地。我正怔忡着,老毒物出现了。她说我们师徒都吃下她的毒,三天之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