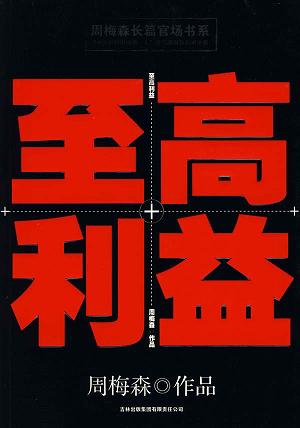根本利益-第1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粮”的,肯定是宽裕户。所以她家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崔良娟长得娟秀,干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宽敞,难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村上有人喊着要筑一条“万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她家后院的一垛墙,一条集体用的“金光大道”侵占了她家的宅院两米多宽,还说这是考验她是不是甘愿“走社会主义道路”。
“凭什么占我宅基地?这是我们男人家祖辈传下来的。再说你们也事先不打个招呼,既然都讲大公无私,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大道’先从自家院里通过?”崔良娟把气出病的老婆婆送上医院后,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责问道。
“你家男人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你家不带头贡献谁还带头?要我说,别说是大队修一条金光大道占了你们两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筑到你们院子的中央,你也该有个好觉悟嘛!”
崔良娟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公社的一位干部告诉崔良娟说我们只管“革命”大事情,你这个人的私事我们没时间管,也不会管的。说完继续写他的大字报。
“这怎么能说是我个人的私事?再说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凭什么推倒我家的墙,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干部,哪想会碰到这样的只讲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气得在那位公社干部的办公室里直打转。
那时崔良娟才32岁,在别人眼里她丈夫在外面吃“商品粮”,每月会给家里寄几十块钱回来,日子一定好过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处,她上要照顾八十多岁的婆婆,下要拖带四个娃儿,供她们吃喝穿着上学。丈夫虽然在外,但一个男人啥事都不会料理,所以崔良娟还要时不时到太原去帮丈夫收拾收拾,尽尽做妻子的义务。那会儿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经常旷工,也算是觉悟问题。好在崔良娟那时年轻,里外都不耽误,不过这份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给我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会儿她得一个来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几岁,正是需要女人热被窝的年龄,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里孩子小,婆婆年纪大,都需要人照顾。四个女娃儿,上学的,吃奶的,排着队缠着她。而生产队里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中,女人们个个被搧惑得像疯婆似的,整日整夜里抢活干,不知死活,不知时间,也不知劳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儿们和婆婆还等着她做饭吃呢!于是她只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里忙碌。怪也就怪在这儿,村上的男人和女人们见这里外忙得几乎是四脚朝天的崔良娟,不仅从没倒下过,那成熟少妇的样子还越来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粮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热热闹闹的婆娃整天围着乐哈哈,有宽宽敞敞的大院子。农民嘛,这些就是顶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说不出什么道理,反正村里人觉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处太多,就该在什么地方作出点“牺牲”,也好让村里其他人心头出口气。
事情就这么个理,虽然摆不上台面,但有人心里头就这么想的。
崔良娟哪知道这些理儿?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嫁给上董村的张家来,就要操持好这个家,不能让张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但现在村里修路,没动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将她家的院墙推倒了,而且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种通情达理的说法。崔良娟觉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里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老宅基地占了一块,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没解决问题,便跑到县上找领导。找县领导比找公社干部难上好几倍,更何况,那是“文革”打砸抢和揪走资派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县长在某个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儿就被几个造反派逮住了,问她干什么的?崔良娟说我家里有事找她。造反派说县长已经是走资派了,你这个女人还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总觉得这个俊少妇跟当走资派的县长有什么关系。“搜!”几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个遍,查出了她身上带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说是自己做的,准备“上访”期间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话,说肯定是那个当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亲信”(那会儿还不叫情人一类的词,但意思差不多),这四根麻花很能说明问题。然后又说,现在是“伟大领袖”指引下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候,你一个女人出远门搞什么上访,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动。抓!崔良娟就这么着被稀里糊涂地关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给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电话,才弄清了她并非是“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人,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还未踏进院子,就听院内传出孩子们悲伤至极的哭喊声:“奶奶,奶奶你别离开我们呀……!”“你别走啊,好奶奶——!”
崔良娟顿时双腿一软,瘫坐门槛上。婆婆的死是与宅基地被占有关的,医生证实,当时老婆婆住院时一则气虚,二则她的胳膊有积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无辜被占后气的,后者是那次村里来人推墙时,婆婆上前阻止时被人扯着胳膊拉扯了好一阵。婆婆年岁本来就大,哪经得起这折腾。其间又听到儿媳妇到上面反映情况遇到的坎坷,这一气一忧,结果带着未愈的伤势和冤屈离开了人世。身为媳妇的崔良娟为之打击巨大,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作为张家的媳妇,在男人没在家时,自己既没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这回豁出去了,她并没有马上把老母亲的死讯告诉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干部,想用婆婆的死来换取上级领导的公正说法。公社干部一听事情到了这一步,赶紧派人来崔良娟家做工作,说无论如何先把老人的后事给解决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们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级政府哩!得相信我们。崔良娟是老实的妇道人家,公社干部立下的保证她能不信?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叫回丈夫,擦着眼泪将老人入了土。
可崔良娟发现,等她把婆婆的后事处理妥当后,公社对她家的宅基地问题却没有任何动静。她找那个曾经拍胸脯包她解决问题的领导,公社干部告诉她那位领导已经调走。那就找新领导吧,崔良娟不得不又从头说起,新领导说一定过问一下。可他的这一过问就没了“下回分解”。等十几天后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领导,人家说这事还得找村里的干部。崔良娟发现,自己磨破了几双鞋,结果还是转到了原地。
“你去上面告呀?别看生产队队长官儿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3米,长17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从统一规划。”崔良娟通情达理,去太原前将院子的大门钥匙交给了一名村干部。
可是半个多月后回来一看,崔良娟拍着大腿喊屈:前院已经按村上筑路要求给刨走了一大片,本该往后挪移的地方却被住在后院的邻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墙,并在此墙靠崔良娟家这边又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规划中让崔良娟家后移的地盘,后院人家却不准她后挪一寸。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头就找村干部说话。村干部为难地说,不是村上办事不公道,而是你后院住的几户人家心里一直妒忌你家。他们眼红,认为你崔良娟和孩子虽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个女娃,又都是读书人,将来一出嫁,谁还会回这驴子都嫌穷的黄土丘来?将来你崔良娟老了跟着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们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说透了,你崔良娟家这块风水宝地早晚也是我们的。哼,现在不跟你说透,我们先占着用又有何妨?
崔良娟好不生气,心想我娃儿多大?男人和我也还有几十年可活,人家却如此给我们料理“后事”呀!村里解决不了,她跑到乡里、县里。三级政府意见一致:崔良娟的宅基应当按集体占用的面积后移,后面的住户不得擅自占用她家的新界宅地。1984年,乡镇政府法律服务站调解三户占用崔良娟家的邻居倒墙还地。但由于这三家邻居仗着他们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势众,拒不还宅腾地。案子交到县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判决,责令那三户人家按时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决,崔良娟觉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法院规定的日期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气人的是其中一户姓张的邻居仗着当过多年村干部,现在又在镇政府工作,镇上县上认识的人多,不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且变本加厉地在崔良娟的院子里建厕所,倒垃圾,并且每天将十几头牲畜赶到她院子。崔良娟实在没法忍下去,便上镇里县里告状。哪知她每告一次,回来得到的是更多的报复:不是这不见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恶的是一次她带着小女儿到太原看病,几天后回到家一掀油罐盖,油不见了,里面尽是粪便……当她含辱洗刷干净油罐后,划火点柴准备做饭时,突然“乒乒乓乓”地响声大作,一团团火星儿直朝她身上窜来……等到她从惊恐中回神过来,瞅着自己衣裤被鞭炮烧焦的一个个窟窿和表皮上渗出的血迹时,不由伤心得抱头大哭。而此时,她的耳边,是从后院传来的阵阵狂笑。
欺人太甚!崔良娟又重新走上过去十余年的上访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得不屈不挠,年复一年。而在这条漫长的上访路上,由于我们的一层层干部和办事人员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使这位当年标致的年轻少妇,成了一个满头发白的老太太。
32年啊!在人的生命里能有几个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守护属于自己的一块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访路。
今年春节前一个星期天,我见到了这位年已68岁的老人。当她得知我是从北京专门来了解她的事情时,不由又一次老泪纵横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头上,然后拿出一个布袋,“哗啦”从里面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样的纸和信封。崔良娟告诉我,这都是她在32年里上访、打官司留下的“纪念”。我拿起翻了翻,有县“革委会”的介绍信,有地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出示的公函,更有镇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和这些政府下属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信访处理意见书”。而在这叠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别多的是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书记、副书记……的一份份批复,那些批复虽然字迹各式各样,有龙飞凤舞的,有中规中矩的,圈儿有画得圆的,有画得鸭蛋似的,但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决”,“请某某部门阅办”,“为什么她的问题拖延如此长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