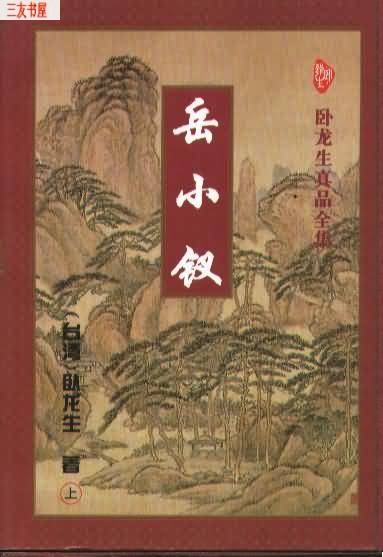岳小玉续-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钱有多道:“初时,它的确是令人不在意的,但等到我赢了八局棋之后,那胖胖的富商却公然把剑从鞘里拔出来。”
方孟海屏止了呼吸,神色紧张地问道:“那是一把怎样的剑?”
钱有多道:“剑长长,剑弯弯,剑圆圆,剑花花。”
方孟海楞住,过了半晌才道:“剑长长这三个字,晚辈是一听就懂得的,但剑弯弯、剑圆圆和剑花花又是什么意思?”
钱有多道:“那是一把三尺三寸的长剑,但在剑锋之上却有两道裂痕。”
方孟海一怔,道:“一把好剑,上面又怎么会有裂痕?”
钱有多道:“这两道裂痕,是铸剑师父在铸剑的时候故意留在上面的。”
方孟海奇道:“铸剑师父为什么这样做?”
钱有多又道:“那是因为这把剑铸造得太完美了,所以铸剑师父就认为有此必要。”
方孟海更加不懂,道:“太完美不是一件好事吗?”
钱有多道:“你听过乐极生悲这句话没有?”
方孟海道:“这句话晚辈是听过的,但却和铸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不,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十分之大。”钱有多缓缓道:“快乐的极点往往是悲痛,爱的尽头往往会变成仇恨,甚至是毁灭力量的泉源。”
“铸剑之道也是—样?”
“不错。”钱有多沉声道:“太完美的兵器,往往会变成凶器,变成不祥之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不少例证可以作为稽考的事实。”
“所以,这位铸剑师父就故意在那剑锋之上,加上了两道裂痕?”
“正是如此。”钱有多道:“在剑锋其中一边,它的裂痕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就叫剑弯弯,而另一边的裂痕,却串着五颗圆圈子,所以又叫剑圆圆。”
方孟海听得不住点头,道:“那么剑花花又是什么意思?”
钱有多说道:“剑花花又可以叫眼花花。”
方孟海道:“何以会眼花花?”
钱有多说道:“剑太锋利,而且精芒四射,使人看得连眼都花了。”
方孟海道:“如此好剑,难怪前辈一看见就舍不得走了。”
钱有多说道:“若不是那把剑实在太诱人,老夫也不会跟杨大官人再对弈了一局!”
“那个胖子叫杨大官人吗?”
“不错,他看来什么都不像,就只像羊牯。”钱有多道:“他知道我很喜欢那把剑,便道:‘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可惜钱兄并非什么烈士,而是一个赌徒。’我听见了灵机一动,道:‘咱们可以再赌一次,就只怕杨大官人不敢奉陪。’杨大官人立刻给我气得哇哇怪叫,道:‘赌便赌,怕你的是龟儿子。’老夫见他这副样子,心中在喜,便道:‘怎么赌法?’杨大官人道:‘赌注太大不好,赌注太细小也是乏味,反正这是最后一局,就赌五万两好了!’”
方孟海陡地一呆,道:“什么?那把剑值五万两吗?”
钱有多叹了口气,道:“不要说是五万两,便是五十万两也是值得的。”
方孟海吸了一口气,道:“神兵利器,果然是无价之宝。”
钱有多道:“就是这样,老夫就再跟胖子下第九局棋了。”
方孟海道:“以前辈的棋艺,大概足可以应付得来吧?”
钱有多说道:“老夫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方孟海道:“结果怎样?”
钱有多嘿嘿一笑,道:“结果却是他XX的输了。”
“他XX的输了?”方孟海一愕,忍不住又道:“到底是他输了?
还是前辈输了?”
钱有多苦笑了一下,道:“是老夫他XX的输了,而且输得好惨好惨!”
方孟海一怔,道:“输了就是输丁,何惨之有?”
钱有多道:“这一局棋,杨大官人才显露真正的本领,初时老夫还占了上风,正在沾沾自喜以为又可轻易再下—城之际,冷不防对手妙着连施,不到三几着就已形势逆转,直把老夫逼得面无人色,手忙脚乱兼汗出如浆!”
方孟海说道:“这是人有错手,又或者是稍有疏忽所致而已,又怎可因一局之败,从而断定杨大官人之棋艺犹胜于前辈呢?”
钱有多道:“当老夫败了这一局之际,心里也是这么想。”
方孟海道:“即使换上晚辈,也—定会感到大大的不服气。”
钱有多道:“但不服气又怎样,这重要的一局棋,老夫的确是输了。” .方孟海道:“一次之败,不足为辱,况且前辈在这—局之前,曾经屡胜杨大官人!”
“所以老夫立时提出再赌之议。”
“那杨大官人怎么说?”
“他说:‘好极,但五万两呢?’”
“这个容易,先付给他好了。”
“但老夫身上何来五万两银子?”
“前辈不是已经赢了他四万四千两了吗?”
“不错,老夫是赢了四万四千两,但还欠六千两又怎办?”
“难道前辈……”
“老夫身上,本来只有五两!”
方孟海陡地呆住,道:“这……这岂不是……岂不是……”
钱有多嘿嘿一笑道:“你是不是想说老夫是个骗子?”
“不!晚辈不是这个意思……”方孟海连忙解释道:“晚辈只是认为前辈艺高人胆大而已。”
钱有多瞪了他一眼,忽然又轻轻的叹了口气,道:“做骗子,也是必须艺高人胆大才行的,总不见得猪会向狐狸行骗吧?”
方孟海讪讪一笑,半晌才道:“前辈,后来怎样了?”
钱有多道:“当然是把赢了的银票全都拿出来。”
方孟海道:“还有六千两又怎办?”
钱有多道:“赊帐。”
方孟海说道:“杨大官人肯让你赊帐吗?”
钱有多道:“不肯。”
方孟海皱了皱眉道:“这可不妙,前辈的确是输了,又无银子可以付清赌帐,这种事若传扬出去,只怕不怎么好听。”
钱有多道:“不好听也没法子,谁叫自己一时贪心?”
方孟海道:“杨大官人既不肯让你赊帐,那便如何是好?”
钱有多道:“只有用另一种方法来还债。”
方孟海道:“怎么还法?”
钱有多道:“做他的奴隶三年。”
方孟海吃了一惊,道:“这可苦也!”
钱有多道:“当然是苦之又苦也,但除了这样之外,老夫又还能怎样了?”
方孟海道:“不可以一走了之吗?”
钱有多说道:“老夫没有走,原因有二。”
方孟海又道:“是走不掉?还是不想走?”
钱有多道:“都给你说对了。”
方孟海道:“前辈轻功不错,怎会走不掉?”
钱有多叹了口气道:“因为那时候,我已知道杨大官人是谁。”
方孟海道:“他是谁?”
钱有多说道:“羊牯坑的主人杨羊山也。”
方孟海“噢”了—声,道:“这羊牯坑的主人,真的这么厉害吗?”
钱有多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江湖中人直至现在还是所知不多,即使是老夫,虽然做了他三年奴隶,对于他的一切,也只是略知少许而已。”
方孟海道:“前辈就是为了那六千两赌债,在羊牯坑做了三年奴隶?”
钱有多道:“不错。”
方孟海道:“羊牯坑在什么地方?”
钱有多道:“羊牯坑距离洛阳不甚远,大概三百里左右。”
方孟海道:“当年前辈跟着杨大官人到羊牯坑下棋,莫非在下棋之前完全不知道那地方就是羊牯坑?”
钱有多道:“当时,咱们是乘坐马车前往的,到了羊牯坑的时候,老夫只看见‘杨家庄’这三个字的牌匾。”
“杨家庄?这三个字看来倒没有什么特别。”
“天下间有无数杨家庄,老夫就算想穿了脑袋,也绝想不到,这杨家庄庄主原来就是羊牯坑的主人杨羊山!”
“这也难怪得很,那杨羊山额头上又没有凿着‘羊牯’这两个字。”
“他是明知老夫身上绝不会有几千两银子的,所以才这么摔我一跤。”
“前辈到现在还不服气吗?”
“不,我现在很服气了。”钱有多叹了口气,道:“人家是用真材实料的棋艺赢了自己的,正是高手遇着了师爹,输了那是千应该万应该,再抵赖下去就太不够意思了。”
方孟海道:“晚辈会好好记住这个故事的。”
“这不是故事,是真事!”钱有多瞪眼道:“你记住它是很好的,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正是前车可鉴,切莫随便把别人当做是羊牯。”
方孟海道:“前辈说在羊牯坑见过练老魔,是不是真的?”
“半点不假。”钱有多道:“老夫在羊牯坑里做了三年的奴隶,就在最后那一个月,羊牯坑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就是血花宫宫主练惊虹!”
他才说到这里,长乐楼头忽然飘下了一条人影。
从长乐楼飘落下来的影子,看来就像是一朵从半空而来的云。
只有云,才会这么轻盈,也只有云,才会这么好看。
那是一个穿着蓝裙的女郎。
她的裙蓝得好看,但更好看的却是她的脸,和她脸上可爱之极的笑容。
但钱有多一看见了她,却比看见一条毒蛇还更惊惧万倍。
方孟海不禁大奇,忍不住问道:“前辈,你怎么了?”
只见钱有多的脸已变成了一片灰白之色,他摇了摇手,道:“老夫没事!老夫没事!虽然口里这样说,声音却是不停的在颤抖。”
方孟海更奇,怔怔地瞧着眼前的蓝裙女郎,道:“你是谁?”
蓝裙女郎嫣然—笑,说道:“你说我美不美?”
方孟海眉头一皱,道:“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美不美又是另外一回事。”
蓝裙女郎道:“女人最重要的是容貌,名字如何,反而是一点也不重要的。”
方孟海道:“莫非小姐之名,不可以向别人说出来吗?”
蓝裙女郎道:“就算我说了出来,你还是要死的。”
方孟海一凛道:“我为什么要死?”
蓝裙女郎说道:“那是因为你犯了罪。”
方孟海奇道:“我犯了什么罪?”
蓝裙女郎道:“你和这个老骗子在一起,这就是罪。”说着,向钱有多伸手—指。
钱有多深深地吸了口气,忽然大声道:“老夫今天倒霉,老夫愿意受死,但这小子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他和我在一起,就加罪于他!”
蓝裙女郎冷冷一笑道:“不行,我早巳说过,只要下次给我碰上,你和你身边的人,都一定要死!”
“荒谬绝伦!”钱有多怒道:“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小子跟老夫只是片面之交,可不是老夫的什么亲戚朋友。”
蓝裙女郎还没有开口,但方孟海已截然地说道:“钱老前辈,谁说咱们不是朋友?”
钱有多冷笑道:“我们不是朋友,从来都不是。”
方孟海大吼一声,道:“但我却巳把你当作朋友!”
蓝裙女郎淡淡一笑,道:“你不是一直都称呼他做‘前辈’的吗?”
“既是前辈,也是朋友!”方孟海昂起脸道:“这又有什么不对了?”
蓝裙女郎道:“你说什么都是很对的,我也不打算加以反驳,总之,你们有什么遗言,快点说出来好了。”
方孟海哈哈一笑道:“不管你和他有什么过节,你今天若要杀他,首先就得从我的尸体践踏过去!”
钱有多喝着道:“你准是神经病发作了。”
方孟海冷笑说道:“我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病,我只知道,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蓝裙女郎“哦”了一声,嫣然道:“你怎知道我不是个好东西?”
方孟海沉着脸,道:“我的耳朵没有聋,我听见你刚才正跟一个人猜拳行令,而且好像猜得十分兴高采烈!”
蓝裙女郎吃吃一笑,道:“是又怎样?难道这是犯了王法的事情吗?”
“犯不犯王法,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那人是谁。”方孟海冷冷说道:“跟你猜拳行令的,就是饮血峰血花宫宫主练惊虹!”
蓝裙女郎淡淡—笑,道:“是练宫主又怎样?”
“物以类聚,你和练老魔那样的老魔头混在一起,当然不是什么好人。”方孟海冷冷的说。
蓝裙女郎脸色一寒道:“难道你和钱老骗子混在一起,又是个好人了?”
方孟海沉声道:“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好人,但我最少不会滥杀无辜。”
蓝裙女郎目光一转,瞧着钱有多,道:“你这个晚辈朋友,说起话来另有一套,果然不俗。”
钱有多冷冷道:“老夫早已说过,这小子不是我的朋友。”
蓝裙女郎说道:“不是朋友是什么人?”
钱有多道:“是羊牯,一只自以为是的小羊牯。”
蓝裙女郎眉毛倒竖,盯着方孟海道:“你跟他下过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