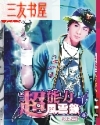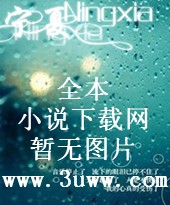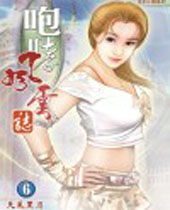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晋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衣食都很简单,只有在美国当大使期间,他比较讲究。
西服的料子、颜色和做工,在国内都尽可能找最好的,衬衣有时一天换两三次。
记得我们到达华盛顿不久,美国报纸及华文报纸刊登了相当大篇幅的文章,介绍章文晋大使。那时台湾派去的代表钱复抵美也不久,文章经常把两人作比较。一些报纸说钱复是台湾的“青年才俊”,但却难以与老外交家相比。他有一点优势,是美国留学生,可能更易适应美国的环境。有趣的是,在我们举行到任招待会的第二天,有报纸评论章大使的衣着,大概是说,中国首任联络处主任穿毛装,第二任穿西衣,而刚到任的章氏,不仅文质彬彬、风度潇洒,而且所穿西服很为考究,不仅合体而且做工精细,可见大陆的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虽非留美也难以相比,等等。尽管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事,但影响却不小。
在美国有不少正式的晚宴,请柬上写明男士须穿“黑领带”即穿短的晚礼服。以往在这种时候,中国大使都穿黑色毛式服装。毛式服装作为民族服装是可以的,但这种场合每年有二三十次,老穿这一种款式,就有点儿显眼和不合群。所以在1983年秋天,文晋和我商量再三,是否可以做一身“黑领带”?我们都有些顾虑,怕太资产阶级味道了。最后决定,既然可以入乡随俗,那穿一身普通的“黑领带”也未尝不可。结果,文晋做了一身,开始穿来不习惯(主要是里面的衬衣吊带等穿着麻烦),慢慢也适应了。新闻媒介居然又有议论,说中国改革开放确实不假,大使居然穿上“黑领带”了。
注意大事,也不忽视小节,这是在国外工作的一条法则。穿衣服虽是小事,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其实,作为个人来说,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穿衣上,我们常常为此感到烦恼不安,但如果为了工作,能给工作带来方便,我觉得那也是应该做甚至是需要做的。
关于美国人的穿衣习惯,我听到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美国人穿衣服很随便,大街上穿什么的都有,并不讲究;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妇女穿衣服很讲究,尤其是上层妇女,衣服穿过一次就不再穿了。文晋在80年代曾两次到美国,接触过各方面的人物,他的意见是宁愿讲究些为好。当时外交部发给大使夫妇的置装费是每人1900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这点儿钱肯定不够,决定把自己的积蓄添上。我们穿得好也是国家的体面。
第五部分第53节: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
1983年5月31日,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会在芝加哥市举行。这是中美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早已商定的重要项目。我们于5月30日赶到芝加哥市,午饭后即去约翰·
汉考克中心大厦拜会市长。该大厦是仅低于当时世界最高层建筑西尔斯塔(共110层)的高楼。而芝加哥市的高层建筑物一直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在高层建筑上鸟瞰全城,但见高低建筑物错落有致,形态各异,隐约还能见到连接密歇根湖和密西西比河水系的运河,相当美丽和壮观。
芝加哥市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位于伊利诺伊州北部、密歇根湖的南端。全市区人口有700多万,仅次于纽约。面积为9300平方公里。城市初建成于1837年。19世纪以来是美国经济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20世纪60年代,其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机和家用电器的生产居全美国之首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芝加哥市举行的各种展览会,比如贸易展览、博览会和各种国际会议,每年有4次以上。同时,它也是美国内陆港口和铁路枢纽。铁路装备和服务水平都居美国之首位。芝加哥市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
5月31日晚,我们去参加了开幕式,市长和芝加哥不少知名人士都出席参观。当天晚上,大雨滂沱,展览团的同志估计天气会影响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岂料,来的人非常踊跃,甚至出乎我们的意料。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曾在欧洲展出过,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赏与好评。这个展览主要是展示1000多年前中国科学的几大发明创造,如纺织、造纸、火药、天文等,还有艺术上的成就。中国是文明古国,这些古代的科技成果曾经给予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以许多重要的影响。这次展览的实物引起观众很大的兴趣。比如纺织,从使用最原始的纺车、织布机所织出的布到极美丽的丝绸织锦,特别是唐代的丝绸织品使观众赞叹不已。在展览现场还有中国宣纸制造工艺的演示。宣纸的生命力极强,直到现在,我们的国画和书法仍然是在宣纸上来进行创作的。
中国的古老文明使世界各国的人民十分喜爱和羡慕。我们也为此而感到骄傲,回顾近百年来我们的发展却如此的缓慢,也不禁生出无限感慨。
我们在芝加哥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也和当地的华人和华侨相聚了。最早时,芝加哥的中国侨民不很多,近百年来,从西部尤其是旧金山一带移民过来不少,所以在芝加哥也慢慢发展了“唐人街”。“唐人街”的中国人很多,中国的各种食品和货物也都十分齐全。新移民到此的有许多是知识界人士,有大陆去的,也有台湾去的。在我们到达芝加哥的当天晚上,华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会,有近200人参加,气氛很热烈,就像接待亲人一般。其中有不少从台湾过来的学人,文晋和他们热情交谈。这时在餐馆外边,有零零落落的呼喊声。主人忙向文晋解释:这是一些台湾国民党的“雇佣军”在瞎嚷嚷哩。文晋毫不在意地笑着向大家说:“我们坐在这里吃饭、谈话,大家都感到很惬意。难为那些人在外面站着,不时还得叫几声。我看他们还是很辛苦的哩。”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在芝加哥反应不错,因此,到1984年2月末,又再次到美国北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展出。文晋趁此机会也去西雅图访问。我们于2月28日抵达。这个城市虽位于美国西北部地区,但天气并不严寒。1869年建设为城市,是美国临太平洋岸的最大城市,也是通往亚洲和阿拉斯加的门户,景色极为优美,因地处通阿拉斯加内航道南站,故发展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雅图发展造船和飞机制造工业,经济繁荣。工业以宇航、机械、木材为主,海洋科学和电子工业也很发达,波音飞机的总公司就设在这里。近数十年,不少华人也迁移至此以求得发展。
我们到达西雅图后即听说,主办展览的科技中心为这次展览募捐了200万美元。我们难以想象要这么多花费,但当我们到达展览场地时发现,这里的主办者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做宣传:沿途有大幅的招贴画、广告牌,展品的陈设也比芝加哥合适。这次展团的组成也有所改变:有25名技术、艺术人员当场表演,从纺织、造纸以至刺绣等都在现场为观众讲解和操作,这样就可能引起观众更大的兴趣。展览的董事会主席是一个食品公司的大老板,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对中国古老文明很感兴趣,对中国人也很热情友好。他告诉章大使,他非常愿意把中国的文明介绍给美国人民,他估计这次展出可以吸引100万以上的观众,不仅是西雅图人,美国西部、北部都会有不少人前来参观的。他认为多花点儿钱来办好这次展览是值得的。
1984年3月1日举行了开幕式,气氛热烈而隆重。州长、市长及许多企业家、名流都来参加了。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来看展览。我们差不多午夜才回旅馆。这次我们住在西雅图的麦迪逊饭店,从国内来的展览团体也都住在这里。文晋午夜去看望团长和全体人员,他们一面为展览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同时也觉得太劳累了。这批团员与去芝加哥的那批不是同一组人员,他们出国的待遇很低,除了吃住几乎没有零用钱。那时还沿袭“文革”期间的供给制,实在太难以适应美国那样的社会生活了。
第五部分第54节:艾奥瓦的国际笔会
艾奥瓦大学教授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先生与美籍华人聂华苓女士,对中国一直持非常友好的态度。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在北京会见过她和其他几位美籍女作家。聂华苓女士的书我已经读过几本,她那朴无华的流畅文字,尤其是她一片思乡念国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3年我们到美国任职不久,安格尔夫妇即到华盛顿来探望我们。文晋非常高兴,在大使官邸接待他俩并请安格尔吃中国饭。安格尔把他刚出版的一本描写中国的诗集送给我们,并约请我们一同去观赏德国的一出话剧。
那是我们首次到肯尼迪中心小剧场去看话剧。据说,那是德国剧团来华盛顿用德语演出的话剧。遗憾的是,对那出现代派话剧,我简直没有留下一点印象。文晋的德语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他也一点儿没有看懂。
聂华苓女士又热情地邀请我有机会去艾奥瓦看看他们的国际笔会。她知道我曾在文艺界工作多年,是半个文艺家吧。她说我去参加一次至少可以认识些朋友。我说,我也非常愿意能有机会去艾奥瓦看望他们。
我国不少著名作家,如丁玲、艾青、萧乾等人都曾到艾奥瓦参加过国际笔会,并在美国一些地方访问、讲学。我们到美国以后,记得冯牧和刘亚洲、徐迟和谌容也到过美国。1984年10月,我实现了去艾奥瓦的愿望。当然,我作为大使夫人不便参加笔会,而是由聂华苓女士特别为我安排了三天访问时间。我和大使馆文化处舒同志一起赴艾奥瓦,由聂华苓女士的女公子接待我们。据说,这年从世界各地来的作家有40多位,大多数来自亚、非、拉国家,也有少数从欧洲来的。当天晚上,我们即受到安格尔先生和聂华苓女士的招待,到他们家吃晚餐。
他们住在艾奥瓦市郊的一所山间别墅里,那里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当我和舒驱车到达时已是下午了。那天的客人除了徐迟、谌容,还有旅美台湾作家陈若曦、柏杨先生和他的夫人张香华。陈若曦女士我曾多次见过面,也读过她的作品,与柏杨夫妇则是首次见面。对柏杨先生我并不太陌生,我到美国后曾读过不少他的文章。他反对“酱缸文化”的杂文,有些我还颇为欣赏。在他被台湾当局囚禁九年之后,曾到美国访问过,并就此出版了《柏杨61》,在当地侨胞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欢迎。我也曾读过这本书,所以对他多少有些了解。柏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外貌,看起来与我国著名演员英若诚太像了,仿佛孪生兄弟一般。张香华女士则是台湾诗人。也许我们彼此都没有料想到会在这里碰面,当聂华苓女士为我们介绍时,只补充一句,说我到艾奥瓦来并非是作为大使夫人,而是作为一个文艺界的同行。安格尔先生又说,他们到华盛顿时曾会见过章大使,在大使官邸吃中国饭,并幽默地说,大使也像一个文化人而不像做官的。气氛立即平静而融洽了。安格尔刚刚大病一场,还做了大手术,看来身体还很弱,但是他特别高兴、活跃,很爱说话。华苓女士呵护地让他少说,让客人多说。这时,大家都快活地笑起来。谌容年轻,也是个活跃分子,看来她已经和不少参加笔会的作家们成为朋友了。
在艾奥瓦的第二天,我和各国作家们一起到一个小城镇参观。大概是主人的有意安排,我和柏杨夫妇以及谌容坐在一起。行程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柏杨谈到因为著文讽刺台湾当局而被囚禁,谈到在岛上监狱的一些事,然后解嘲地说:“我这人真冤,大陆有人认为我是反共文人,而台湾当局却给我戴了顶红帽子,这个世道的事真难说啊!”我们大家只有一笑置之。
在安格尔、聂华苓家最后一次会面时人更多一些。他们两位为了这个国际笔会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和精力,特别是为各国作家之间的交流作出了使人难忘的贡献。
我怀着敬佩与感谢的心情和他们告别,与柏杨夫妇话别时,希望他们两人在方便时来华盛顿大使官邸做客,并说主人可以是徐迟和谌容。他却说:“我有一天会回到大陆我的祖国探亲,那时候一定到你家去拜望。”我笑笑回答:“那我就回北京等你们了。”这句当时看似玩笑的客套话倒真引起后来的一次巧遇。
1988年秋,有一天晚上,文晋和我去北京饭店出席一场晚宴。当我们从东楼往西楼去的时候,在廊子上迎面碰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当时我想,英若诚也来参加宴会?又一想不对,我唐突地叫了一声:“柏杨先生!”他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