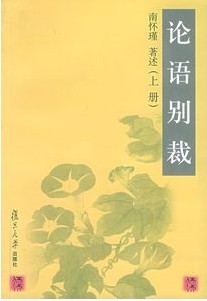论语注释-第3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患得患失的人自己也很痛苦,很无聊,活得并不自在,并不轻松。那可真是“熙熙攘攘为名利,时时刻刻忙算计”,结果还多半会“算来算去算自己”。对这种人来说,人生就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指出,是在痛苦与无聊,欲望与失望之间摇晃的钟摆,永远没有真正满足,真正幸福的一天。
麻烦的是,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以后,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患得患失的人们越来越多,而从容不迫,悠哉悠哉,保持平静心态的却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又怎么能够使我们自己不落入彀中,少一分虑患,多一分悠闲呢?
古今人物毛病谈
【原文】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1),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2),今之矜也忿戾(3);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注释】
(1)疾:毛病。(2)廉:棱角,这里形容人的行为方正有威严。(3)忿戾:忿怒乖戾。
【译文】
孔子说:“古时候的人们有三种毛病,现在的人恐怕连这样的毛病都没有了。古人狂妄还不过是放肆一点而已,现在的人狂妄便放荡不羁了;古人矜持还能方正威严,现在的人矜持便忿恕乖戾了;古人愚笨还表现出直率,现在的人愚笨却也知道欺诈,如此罢了。”
【读解】
现在的人连这样的毛病都没有了,不是真的没有了毛病,而是说没有了这样隐含着一定优点的毛病,而彻头彻尾是毛病了,是变本加厉而不可救药的毛病。
试看,古代的人狂是狂,但还狂得有一定限度,不过是说话做事放肆一点罢了,而现代的狂人却狂得来放荡不羁。比如敢把公款拿来豪赌挥霍,光大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完全是一种精神病态了。古代的人矜持还有一点矜持的原则,知道自己把握住自己,而现代的人矜持却忿怒乖戾,含血喷天,行为乖张,自视高得来“舍我其谁”,达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了。古代的人愚笨就一定直率,不知含蓄委婉,现代的人就连最愚笨的也知道弄虚作假,必存奸诈。不信,你就是到市场上去买一点最廉价的东西,比如说食盐,不也有工业盐在等着你,欺诈你吗?
孔子的观点是今不如古,就连同样是缺点,是毛病,也是今人更比古人坏。我们倒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把他所比较的古今人物毛病加以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反过来修养自身,减少缺点。
天何言哉?
【原文】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文】
孔子说:“我想不讲话了。”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讲话,那么弟子们又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讲了什么呢?春夏秋冬照样运行,天下百物照样生长,天讲了什么呢?”
【读解】
圣人有时候还真会开玩笑。教书先生突发奇想,居然说自己不想讲话了。不想讲话怎么教书呢?子贡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来回答,那就只好改开聋哑学校了吧。
可圣人却不这样回答。
圣人话锋一转,抬头望天。请问,天讲了什么呢?不是照样运行四季,化育万物吗?
原来,圣人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真的不想讲话,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引入正题,实行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啊。说到不言,倒是圣人的老生常谈了,还是“敏于事脑慎于言”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篇章已谈得很多,其例证可说是不胜枚举,只不过还没有哪一处像这里这样推到极端罢了。
至于说到“天何言哉?”,倒不只是孔子一人的看法。《诗经·大雅·文王》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记·哀公问》说:“无为而物成,天之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都是说的同样的意思。甚至包话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大音希声”之类的话,也都与“天何言哉?”有相通的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叉说这么多干什么呢?
天何言哉?圣人何言哉?
不屑之教
【原文】
孺悲①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②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间之。
【注释】
①孺悲:鲁国人。②将命者:传命的人。
【译文】
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加以推辞。传命的人冈灿房门,孔子便取下瑟来一边弹一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
【读解】
据《札记,杂记》记载,鲁哀公曾经派孺悲去孔子那儿学关子士的丧礼。这里的一段大概是孺悲初次去拜见孔子时的情景吧。
孔子为什么不愿意见孺悲呢?既然不愿意见叉为什么要让他听到自己弹瑟唱歌,使他知道自己不是生病而是故意不愿意见他呢?这些似乎都是一个谜,使人难以理解。
朱嘉认为,总是孺悲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孔子,所以孔子才装病不愿意见他,同时又故意让他知道自己不是生病,而是不愿意见他。
这样的看法,不是把圣人的心胸看得太狭窄了吗?
倒是程颐的看法比较独到,认为孔子的做法正是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见朱嘉《论语集注》卷丸)
原来,在《盂子·告子下》里,盂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意思是说: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那么,孔子之所以不见孺悲而叉故意让他知道自己不愿意见他,是不是正好采用的这种“不屑之教”呢?
“不屑之教”也是不言之教。看来,圣人真要不讲话,也不必改开什么聋哑学校了罢。
丧期要不要改革?
【原文】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①,钻燧改火②,期③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④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①升:登,登场。②钻燧改火:古代钻木取火或敲燧石取火。改火只与钻木有关,燧系连带提到。钻木改火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秋取柞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论语集解》引马融注)③期:一年。④予:宰予,即宰我。
【译文】
“宰我问道:“为父母守丧三年,为期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一定会被败坏;三年不奏乐,乐一定会被毁掉。陈谷子吃完了,新谷子不登场,钻火改木周而复始,一年也就可以了吧?”孔子说:“守丧不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花缎衣,对于你来说能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那你就那样做吧!对于君子来说,有丧在身,吃美味不觉得味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闲居也不觉得安适,因此不像你说的那样做。现在你既然觉得心安,那你就那样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真不仁啊!子女生下来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的守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我难道就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怀抱的爱抚吗?”
【读解】
宰我就是那个大白天睡觉的“朽木”,被孔子骂了个够。可偏偏这块“朽木”就是“不可雕”,挨了臭骂仍然是冥顽不化,这一次又提出了大逆不道的问题,居然想把天下人通行的三年丧期改为一年。
说起来,宰我的改革思路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守丧三年在我们看来也的确是太久了一点。但按照孔子的解释,守丧三年不过是对父母怀抱自己三年的回报罢了,没有什么苛刻的地方。何况,守丧不到三年,自己也于心不安。前一方面是理,后一方面是情。论情论理,守丧三年都不为过。而宰我于理不回报三年,子情能够心安,所以孔子斥责他是一个不仁的人,就像自己没有承受过父母之爱一样。
宰我既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行也”,又是一个不仁的人,真该被一脚踢出孔门!
可是,礼仪风俗,与世推移,到我们今天来看,不合时宜的反倒是圣人孔子而不是朽木宰我。守丧不仅不是三年,而且也不是宰我提出的一年,而仅仅是三天了。人死如灯灭,三天以后,早已是灰飞烟灭,形迹全无了。还守什么丧,戴什么孝,禁什么歌舞礼乐呢?不在三天内猜拳行令,麻将不休就算谢天谢地了。
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还是用孔子的那句话来衡量:“这样做,你觉得心安吗?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吧!”
只不过,你不是君子,而是像宰我那样不仁的“朽木”和“粪土之墙”罢了!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原文】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①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①博奔:博,即六博,古代的一种棋局游戏,近似后代的双陆,弈,即围棋。
【译文】
孔子说:“整天吃得饱饱的,一点也不肯动脑筋,这样的人可真是无聊啊!不是有下棋之类的游戏吗?玩玩这些,也比一点不动脑筋好啊。”
【读解】
孟子说得更为尖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膝文公上》)
虽然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是仁者叮咛,一个是智者雄辩,但两人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学,有所思,有所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好吃懒做,消极无聊地打发日子。而庄子却借广成子的口说:不看不听,清静无为,不劳动身体,不费心思,就可以长生不老。多用心智,乃是祸害的根源。(《庄子·在宥》)
由此可见儒道精神大异其趣。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能够真正做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说不定这本身还是一种难能的修养,一般人就是想修还修不成的坐定功夫呢?倒是在经济发达,生活超过了温饱线以后,一些人无所事事,闲得无聊,似乎采纳了圣人的建议,没日没夜地打起麻将来了。圣人若是知道了这情况,会不会感到哭笑不得呢?
君子尚义不尚勇
【原文】
子路曰:“君子尚勇①率?”子曰:“君子义以为上(2)。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注释】
①尚勇:尚同“上”,以勇敢为上,也就是崇尚勇敢。(2)义以为上:崇尚义。
【译文】
子路问:“君于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崇尚义。君子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惹乱子,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读解】
孔子尚德尚义而不尚勇,主张用礼义来规薄约束勇敢。当然,这并不是说勇敢这种品质不好,而是说如果不加以规范约和勇敢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问题。这就是他在“六言六蔽”里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以及在《泰伯》篇里所说的“勇而无礼则乱。”
尤其是对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来说,无勇倒还没有什么,一旦有勇,那便真会成为害群之马;肆无忌惮,无恶不作,闹得社会不得安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用道德规范或者说礼义来约束自己,特别是在那些容易引起“一时之忿”的场合下,多想想后果,以义为上,以免闯下祸乱,给他人和自己都带来危害。
君子僧恶什么?
【原文】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①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②而讪③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①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⑤以为知者,恶不孙(6)以为勇者,恶讦(7)以为直者。”
【注释】
①恶:厌恶,憎恶。②居下流:指处于低下的地位,晚唐以前的《论语》没有“居下流”中的“流”字,所以一般认为是衍文。③汕:毁谤。④窒:阻塞不通,这里指顽固不化,固执到底。⑤徼(jiao):抄袭。6)孙:同“逊”。(7)讦(jie):揭发检举别人的隐私或过错。
【译文】
子贡问:“君子也有僧恶吗?”孔子说:“有憎恶。憎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憎恶身居下位却毁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