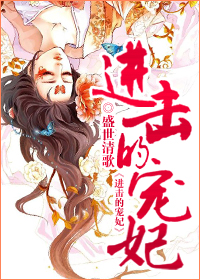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1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眼睛,就会觉得真是奥尔菲欧。
出来时我想到好格沃德,想到他用特别的乐器进行的文献般的演奏。这些乐器声音短促,回音不完整,整个演奏总是有点过快。因此,我出来时,当我看到面前的斯坦·劳雷尔和奥利维尔·哈迪的面孔时,我就带有被偷走了天堂的人的那种忧郁的印象。正如众所周知,《奥尔菲欧和欧里迪斯》。那两人的相片在休息室一面墙上挂着的镜框里,已经有点旧了,周围有许多人。斯坦利奥和奥利欧两人于1952年访问了该剧院,那时该剧院名叫恩皮雷。我待在那里注视着相片中的那两个人,德国游客们已经都走了。后来,过了一会儿,这个夜晚的气氛就变了。
在外面,在戏剧节的这些夜晚,爱丁堡到处是密集的人群。古堡里燃放着烟花,一群一群的年轻人看完一场戏又去看另一场戏,他们的头发有绿色的、紫色的;五十来岁的苏格兰人穿着短褶裙,非常优雅;人们坐在地上吃着用硬纸包着的比萨饼。到处都是公共场所的气味,那些难闻的气味使你的思想变得苍白;神经质的出租车总是从错误的方向开过来;(而这些人何时将决定让他们左边驾驶呢?)那些踩高跷的人在高街上下来。而在电视里,维阿利身穿一件怪怪的球衣,前面印着一家啤酒的商标,他注视着摄像机,用英语说着什么。真滑稽。当你在十几年后看见一个小学同学,头发梳得亮亮的,身穿灰色衣服,作为第十四选区的众议院候选人在电视上发表竞选讲话,这个时候你会有同样的感觉。有些悲惨的事情会让人笑死。如此一类事情。
/* 30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爱丁堡(三)
Holyroodhouse宫是像明信片上那样的一座方形古堡,在RoyalMile旧城中心的尽头,是女王到城里时的正式住地。在古堡旁边有一个仿佛是地质玩笑的东西,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火山坡。后面是一个公园。在公园里有一片大草坪,大概有四个足球场放在一起那么大。那草皮,就是在意大利米兰圣西罗足球场也都梦想要的那样的草皮。这里,像所有各处那样。这样的地方会使任何一位苏格兰人成为高尔夫球手,每一寸土地都会成为一个高尔夫球场,你在分流交通的花坛里也会找到球洞。但是这里例外。四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上面有二十万人,他们称之为〃星期天汇演〃。在这个星期天,戏剧节要让全国人民陶醉。有十七个舞台,数百个大小节目。全都免费。一家一家的人来(从爷爷到新生婴儿),可怕的朋克们,稍迟开放的花的儿子们,旅游者,骑自行车的人,记者们(最悲伤的人),以及数百条狗。在这里,这些狗都很奇怪,好像家具似的。人们在这里喝酒,吃饭,消费高、低、中级文化,仿佛被射入了后现代游戏机里。例如,在吃了夹着一块真正的牛里脊肉(排着这么长的队,这里毫不在乎疯牛病)的面包企图自杀之后,我在一个舞蹈舞台前面躺下(通用语,让你避免难堪的同英国人身体靠着身体)。小孩们,打着小雨伞的老夫人们,三个人身穿凯尔特族运动衣,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褶裙的男人沉睡着,打起了呼噜。这是涂抹皮肤的另一种人类的地面。紧接着,我看见舞台上五位黑人姑娘加上一位白人姑娘离开跳非洲舞蹈的地方,她们似乎是善良的漂亮女性;一个信仰佛教的团体表演一个善与恶的故事,结果善赢得胜利;我不知道是来自英国哪个边远小岛的一个舞蹈团,全体穿着制服,表演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经典舞蹈,类似阿尔卑斯山人跳的那种踢踏舞;一位日本男人可悲地裹在一套非常贴身的白色乳胶衣服里,身上到处挂着铁链,神秘地专心做着最低限度的编舞。
一分钟后,小孩子们开始啼哭和走开。于是我也走了。我爬上了奇形怪状的火山坡,然后转过身来,我看到了四个足球场和二十万人的小点点画面,以及整个爱丁堡后面,山岭,最后是一片大海,我从未见到过的最没有用处的海。我在记忆中印下了一张照片,就走了。我将把这张照片连同其他照片一起带回家去。有许多其他照片,但是这里的只有三张。
第一张是库尔特·马苏尔,他来自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台,正在指挥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最后部分,以其笨拙而善良的那种方式指挥(太对了,他连指挥棒都不用),让乐队跑去。那乐队由于没有刹车的那段音乐的下滑而不可抗拒地加速,他追随着乐队,而踩刹车太晚了,已经飞出去了,达到了肯定至少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那种速度。到最后几分钟,观众都屏住了呼吸。而后来:欢呼。
第二张是我看包波·威尔逊搞的《奥兰多》时所看到的那一切。特别是灯光变化。实在奇妙:他改变灯光,就像舒伯特改变调子一样。(这个解释起来会很长。无论如何,那就是:你待在那里,带有一定的灯光,或者有一定的调子,你感觉绝对完美,直至他们没有决定把你换到另一种灯光之中,在另一种调子之中,那么你就明白了,是的,这是完美,你确信如此直至没有给你打上一个背光,或一个d小调,于是一切再从头开始,可能没完没了,如果最后没有黑暗或肃静终于来到。就是这样一类东西。)
①帕尼尼(公元前四世纪或前三世纪),印度语法学家,其著作《词语解释》是关于书面和口头梵文的极有价值的一种系统语法译注。第三张是名叫尼埃尔·戈乌的人的一段小小的音乐。此人在我们这里不熟悉,但在那里却是神秘的,因为他是苏格兰Fiddle音乐之父,Fiddle是这里给小提琴起的名字。那音乐是我们可以想像的那种音乐,可以说是一种盖尔人的凯尔特人的西部的乡村音乐。是民间音乐,形式简短而初级,发声部位准确。好玩的是怎样起歌名,几乎全都是用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我知道的有《瓦尔顿·迪乌夫夫人》,或《卡尔洛蒂·康普贝尔夫人》,或《大卫·斯蒂瓦特船长》。仿佛是帕尼尼①形象。我无法很好地解释清楚,但是,漂亮的是没有像《走下斯蒂林山坡》或《甜蜜的水》那样的标题,而是活人的名字就得了。多好啊。好吧,再回来说说尼埃尔·戈乌。他生于1727年,1807年去世。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知道确切时间是何时他写了他的那个杰作,人们熟知的题目是《为第二个夫人之死而悲痛》。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这是奇妙方式的悲痛。以三个音符一组往前演奏。在仪式队伍中,仿佛有一个人在哭泣,慢慢地、毫无害怕地哭泣。只有悲痛,就够了。我在格雷弗里阿斯教堂里听到了由名叫阿拉斯戴尔·弗拉塞尔的一个人演奏它。在那个教堂的整个周围,有一个极好的无洞高尔夫球场,那里有写着名字和日期的石头。我们这边人说,那些是坟墓。
/* 31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波希米亚人① (1)
①1996年2月,时值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一百周年,都灵市歌剧院决定以这部歌剧的盛大演出来作为纪念(电视直播,米雷拉·弗莱尼和卢齐阿诺·帕瓦罗蒂主演两个年轻的恋人)。我们想在报纸上介绍一下普契尼,讲一讲这部歌剧的故事情节,使观众有所准备。因此便写了这篇文章译注。早一天或晚一天,音乐剧也是要死亡的:最终它确确实实像消耗殆尽的演员那样做到这样,在最佳时刻和以最佳方式退出舞台。它给予电影和音乐喜剧诞生的时间:它等待着它们的诞生,就像一位老人等待着派来的凶手把他杀死。然后,他选择死的时候穿的衣服,正如其风格那样,他选择了最富戏剧性、不知羞耻和爱慕虚荣的衣服,最轰动的、甚至有点粗俗,但无论如何是不可抗拒的、非常漂亮的衣服:普契尼。这不会是一种死亡,而会是一种胜利,最后的胜利。
真实的事情是普契尼埋葬了歌剧,而这又将永远不停地使其剧院不可避免地具有魅力。他以至今仍然令人吃惊的清醒头脑,一个一个地认清了现代特色中会产生的而歌剧又不再能够满足的所有各种愿望。他想像到会是我们这样的观众和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以及像市场、消费品、轻音乐这样的概念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想像到四十五转唱片,《你永远看不到的女人》就是例证。或者西部电影,就像在那十分荒唐的《西部少女》中所写的那样。诚然,他已经完全知道电影会是怎样的东西。在他的剧院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电影都像是一位受邀请而又永远不能来的客人。
他本来可以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或者挂笔并通知大家节日过完了。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他试图玩那不可能的杂技:用音乐剧的陈旧武器来推陈出新。发现新的,并以跑起来太慢、重击又太累的戏剧形式来向新的挑战。这是一场值得纪念的冲突:在撞击中,本来是歌剧的那东西无限地变形了。这里睡了,那里卷曲了,变成毕加索式的面孔,奇怪的面具,残骸,碎片的戏剧性汇集,瓦砾、废墟、遗迹的奇妙混合。一切都在一场爆炸的烈火中熔炼。后面留下了焦土。《图兰朵》不只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而是整个儿的最后一部歌剧。
从那场戏剧性灾难中又出现了普契尼歌剧,每次演出普契尼歌剧都像是一种文明的毁灭和宣告新世界的呐喊。普契尼歌剧于是成为同时是古老而又现实的某种东西。《波希米亚人》的一百周年既是伟大又什么也不是。鲁道夫和咪咪的故事犹如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地图,但是这张地图是用电脑画的。过去的折磨在一系列喷发出来的绝望动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动作自那天之后就会成为跳那种现代的通俗而又高雅的探戈的舞步。因此,痛恨和热爱那部歌剧就只是一个动作。不同意它和赞赏它,只是一个东西。而当你在剧院的黑暗中面对它时,笑与哭是一个不可预见的灵魂的毫厘之差问题。你不能先知道你会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正确地明白,事态的钟摆不管把你放在何处,都将是正确的位置。咪咪之死既是高尚的悲剧,又同时是拙劣艺术的不幸纪念品,是一切。而不管何处,都是看咪咪之死的正确位置。
(一)
在那里面,真的寒冷刺骨。你把手放进口袋里,在那里也冷。现在可能觉得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但真实情况是,只要那里面没有那种要命的寒冷,那么,也许一切都会有不同的进展。也许那两个人不会那么难受。也许她还会在这里。也许我们在心中也不会有这种云雾。也许。然而,在那里面寒冷刺骨。事情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发生了。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又是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说其整个事情的话。
事实是,他们没有钱来取暖。在那里面,在巴黎,在冬季,那是坐着都会冻你屁股的一个地方。他们四个人在拉丁区合住一套房子,一个你能看见全城的阁楼。你离天空很近,而除此之外,是一个臭屎地方。夏季是一个火炉子,你就是站着,屁股也出汗。还要说的是,他们是年轻人,因此都不在乎。他们是艺术家,在一些事情上有帮助。你可能是一个穷人,就只是穷人,这是一件让人悲惨至极的事情。而如果你是穷人,你写作韵诗,那么你就有所不同:你是第一位过来的女人的下一位情人。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就是那样一种人。马尔切洛画画,我们想这不坏,但他一幅画也没画出来,这就使事情有点儿复杂化。科利内研究哲学,总是带着很多书,只要他还没有把那些书卖掉的时候。绍纳尔德是惟一能拿出一点儿钱的人,他是音乐家,他给富家小孩子上课来度日。第四位鲁道夫,从事写作,写诗歌,有时也写文章、剧本这类东西。他是一个好孩子,他有着好孩子们都有的那种有点基本的聪明,心里一次只有一个主意,如果同时有两个主意,那就乱套了。音乐家绍纳尔德取笑他说:你有着一位男高音的脑子。鲁道夫感到难堪,但是只有一点儿。像人们所说,他是一个好孩子。
总而言之,那天真的寒冷刺骨。再说,又是圣诞节前夜,整个巴黎被白雪覆盖,是一种给人观赏的东西,一场戏剧。但无论如何,天气如此寒冷,以至马尔切洛在某个时候搬了一把椅子,说:算了,我现在把这把椅子放进壁炉里去,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实际上,那是一个好主意,免得冻死。如果你没有钱买劈柴,那么你总是可以烧家具,那是一个好主意。而鲁道夫为了说明他是那种人说:我有更好的东西。他拿起他的剧本的前面部分,就是他正在写的那个剧本,他拿起已经写好的那些纸,把它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