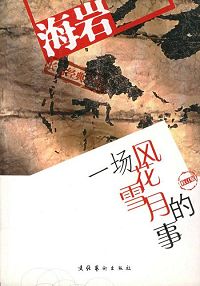正在发育-第2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看的书非常杂,主要是凭兴趣,或者是当代热卖的图书,不会逼着她看那些看不进去的所谓经典名著。名人传记,测字算命,流行杂志,卡通漫画,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当然对她来说,还是以文学作品为多。其他孩子,千万不要比着方舟的兴趣买书。总之多看书没有坏处,这才是提高鉴赏和判断力,抵制不良读物治本的办法。何况人的知识,绝大部分是通过间接经验,也就是读书得来的。
不少的家长认为,孩子功课紧,少看闲书为妙。但是越到高年级,就越能显出害处了。仅靠学课本,特别是语文,完全不能应付越来越开放的考题了。现在就连小学考试,非课本知识的比例也在逐渐加大。有一次考试,填词“脍炙人口”,全班只有方舟一个人做出来了。我可以保证地说:在整个小学阶段,方舟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这足以证明,看“闲书”,丝毫没影响到她的成绩。何况,以她奇快的阅读速度,看书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倒是她自己写的书,她翻了翻插图,就再也没看过第二眼了。
四早熟的苹果好卖
有人问方舟:“你是不是早熟?早熟到底好不好啊?”
她说:“我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早熟。早熟的苹果好卖。”
有人问方舟:“你这么早熟,会不会早恋啊?”
她说:“会啊会啊!我都早恋好几回了。”
她这样回答,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一直避讳承认和试图否认她是早熟的。孩子发育早,不管是指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大人来说,好象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代表着不好的发展方向:早熟等于早恋等于早衰,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意味着早早地接触不该接触的东西,早早地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早早地考虑不该她操心的事情,早早地变得不可爱不天真不纯洁不听话了。早熟,似乎还是拔苗助长的恶果和江郎才尽的前奏。总之,既然冠以“早熟”“催熟”的名称,那一定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反季节“农作物”,注定要收获扭曲变态并不美味的瓜果。
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早熟,在大人眼里,孩子再怎么成熟老道,到底是个小孩子。但经过旁人无数次的提醒,包括不很中听的批评言论,网上的“板砖”,甚至直言方舟和她妈妈是神经病。我这才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方舟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熟都熟了,俗话说“生米都煮成熟饭了”,再去“返青”或者“回炉”,只怕是不可能了吧?
我自己,是晚熟的例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大人刻意地向小孩子隐瞒实情:“这事你不要问,长大了自然会知道了。”“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于是在懵懂中稀里糊涂地长大了。但我自己的青少年阶段,并没有因为无知而变得纯洁起来,反而是吃了不少的教训,如此晚熟,似乎也未能阻止早恋的发生。既然晚熟,在我自己的身上,没见到良善的结果,所以我对“早熟”的看法,在没有孩子之前,就很坚定了:要是我有了孩子,绝不对他欺瞒任何事情!
要是知情权给了孩子,他就会迅速成熟,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传统里,一向非常畏惧孩子成熟。我想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吧。
一是出于非常自私而无用的考虑——天真的孩子,观赏性要强些,又因为无知,能说出些逗乐的言论,叫人开心。
二是相信一些奇怪的辩证法。比如:“小时了了(聪明),大未必佳。”“大器晚成”等等。有个人对我说:“你的孩子完啦,从此失去简单的快乐,思考不适当的问题。直到和所有的同龄人再无共同言语。结果不是郁闷反叛就是无情孤独地过一生。如果不信,这是一个20年的赌约,走着瞧。”这些说法,都建立在不确定的蛮横判断上。早慧的孩子,长大了平庸,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小时不了了,长大一定佳吗?小时了了,长大一定不佳吗?他又是如何断定,思考和快乐,是绝对不能相融的呢?
三是怕沾染病毒,人为地设立一个隔离带,最好是真空消毒过的。事实证明,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他迫切地想知道,总能找到渠道,也可能是地下渠道。
四是相信一些偏颇的理论,特别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年轻父母,很容易接受“顺其自然”“快乐教育”“自由发展”等等等等,外表上打扮得很现代很西化的理论。总之,孩子表现得不像个孩子,那一定是不对劲了,而孩子应当是什么标准,怎样才是一个最合规格的孩子,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父母常常做孩子的过滤器,把渣滓偷偷地丢掉,不让他们看见,只留下纯净水给孩子饮用。实际上,父母不会反对孩子接触世界,只是屏蔽掉几个信息:丑陋,黑暗,性爱,死亡。但是,只看到鲜花和阳光,他认识的世界肯定不真实,对世界的判断,一定误差很大。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光荣传统(4)
五让仿真文章走开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上“算术课”,中学才叫“数学课”;“图画课”,后来改成“美术课”,我不知道这样的变动有什么道理,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我觉得“算术”,表示初级,闹着玩的,还没进入正规的数学领域。现在都称为“数学”了,小学生到专家都一样。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音乐家,美术家,政治家。小孩儿和专家,学问高低不同,本质是不变的。
只有数学家,没有算术家。
那么“作文”呢?有文学家,有作文家吗?
为什么叫“作文”,不敢叫论文叫文学叫文章?
为什么要降格以求?几十年孜孜不倦地降格以求?凭什么不让孩子写真正的文章?如果美术课十几年只教孩子画简笔画,而不告诉他更不让他练真正的美术?这正常吗?少年足球队,踢的是仿真足球吗?少年琴手,弹的是仿真钢琴吗?你能接受孩子学十几年仿真数学,练十几年仿真田径吗?
人文领域,比如历史哲学文学等等,这些年,少年天才到底是出得太多了,需要打压,还是压根就没有?
小孩写了一两本书,就被一片声地呼喝为“天才”,如果不是恶意捧杀,那只能说,是前辈用慈祥和爱护的眼光,去看儿童组的竞赛。试问:这些天才少年儿童(如果方舟也算一个的话),有独立建树吗?如果根本就是在模仿和追赶成人,那能叫天才吗?我记得韩国的李昌镐,是把大大小小的棋手杀得横尸遍野,才得了“神童”称号的。
所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标准和要求,实在是低得可怜。
为什么作文一直被视为初级的,练习的,仿真的?而正经文章,比如散文小说论文,我们认定学生是写不了的?
从小学到高中,文体训练种类不少,最大训练量的文体是两大类:
记叙文,议论文。
试问:成人文章里有这两种文体吗?记叙文是什么东西?议论文又是什么东西?将来的工作实践中,用的最多的论文,为什么从来不练?
请仔细回忆,出了校门,你有没有被要求,写中小学那样的记叙文议论文,哪怕一篇?有没有?那些所谓优秀的记叙文议论文,明显带有学徒工的标记,说句实话,只能投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读物上去,搞自产自销。哪里能应付真正的写作呢。
现在我来说出真相:小学中学练了十年左右的作文,根本不是文章!文章不是那样写的!从学会写字到走出中学,我们的作文课,那些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训练的是什么?
是四不象的仿真文章!出了校门百无一用!什么都不是!
我建议,废除“记叙文,议论文”等概念!从小学到高中,学校作文的种类重新划分,写真正的文章,重头就是两大类:
论文,文学作品。
方舟从开始写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写书。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的真正的书。而不是油印的在亲友手里传阅的册子。是散文或小说,而不是什么习作!
有人说:九岁十岁写小说太早了嘛!是不是先写点日记?
甚至有人说:先写100篇日记,100篇游记,100篇杂感,100篇寓言,再来写小说嘛!
——按每篇500字算,四个100篇,就是二十万字!练了二十万字,才来写小说,他们以为小说是什么?核尖端啊?高科技啊?某些人的专利产品啊?
但是我们的作文不就是这样练的吗?以每个学生平均1万字/1年计算,十年就写了10万字。事实上,一般学生远不止写了这个数。为了慎重,我查了新版的《语文教学大纲》,上面有量的规定:小学高年级,各类习作共1。9万字左右,初中,各类写作5。1万字左右,高中课堂作文和各类练笔,超过5万字。加起来,已不止10万字了。10万字是什么概念?每个学生都能写一本书了!但是很多人,一出学校,就把写作视为畏途和终于摆脱的噩梦。十年练出十万字的四不象,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也太轻视孩子的智力了吧?
黄全愈博士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提到美国孩子8岁就写论文。有些人不屑:八岁能写什么论文?
黄博士列举了一些论文的题目,八岁孩子写得有模有样:
老鼠有决策能力吗?
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食物的色彩与消费者的心理;
狗靠什么来决定选择玩具;
猫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
——难道是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素质强吗?试问:这些题目中国孩子一定写不出来吗?问题是,我们几十年的作文课,出过这样的题目吗?
我们从来没有让孩子写过!我们压根不相信他们能写!
其他学科,整个的中国基础教育,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仿真。
我们一方面呼吁孩子参与社会,一方面又本能地把孩子阻截在社会之外,呼吁的声音高涨了,就给孩子提供一个模拟和仿真的,提供点边角废料给他们随便玩玩。怕他们把真实的事情搞砸了!
一旦孩子进入真实的成人领域,立刻惊呼:这么小就……这对小孩儿有好处吗?
很多的教育者,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阻拦孩子做事情。而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什么创造性培养,九法十八式。根本问题不解决,说得花哨有什么用?
创造性的培养,归根结底就是一条:
让孩子独立地干一件真正的正经事。
哪怕多小的事,是真的,而不是游戏模拟仿真的。告诉他成功的目标,对他说成功的好处,并提供条件,帮助他成功,肯定他的成功。就这。
方舟为什么一定要写自己的书,原因就在这里。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光荣传统(5)
不能让她的写作天分,耗费在仿真作文上。
那种带模式和套路的作文,只能把好好的写作天才写残废了,思维写残废了,语言写残废了。那种残废,是很难很难修复的。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很大的话题。
(六)关于修改
有人问:“你的作文都是自己写的吗?你妈妈给不给你改?”
方舟说:“她还没有我写得好呢。”
我说:“我要不是学中文的,是学理工的就好了。”
方舟说:“你要是个文盲更好。”
那样就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文字,出自她的手笔了。
第一本书出版时,要给一张图片配个说明。她是怎么写的:
“这是在大连的旅顺的蛇岛照的,这可是货真的蛇,价实不实我就不知道了,可这蛇是真的,可以证明的,只有这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我说:“不行,不通,改了。”
她大叫:“啊?怎么不行?哪里不通?就是通的!”
我说:“的字用多了。”
没想到,她还知道挺多,她说:“妈妈,你懂不懂啊?我们汉语里,‘的’字是用得最多的字,平均15个字就要出现一个‘的’”——她的说法没经过专家认证,可能统计有误。
我说:“好好好,我们来数数。”
加上标点是60个字,用了7个‘的’,平均8。57142857字,出现一个‘的’字,这回她无话可说。重新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