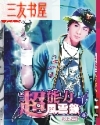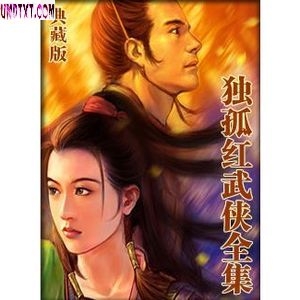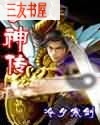萧克回忆录-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
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
取主动。”
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
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吁派出了强有力
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
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
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
而东。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2 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
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这时,我
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
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
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
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
心胆为之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
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
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
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80 多天,跨越敌境5000 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
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
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
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
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
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
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
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符坚的大军。大革命时
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
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
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也很少优势,要取得主动,
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
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
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贵州东
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60 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
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
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
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
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
锋。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
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
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
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
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
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
有直接责任。
1934 年10 月24 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
师。在此之前,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甘溪之战被截的17 师49、51 团之一部,
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二军团的一部先会合了。
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
欢聚一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
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佳
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
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4000 多人,六军团有3000 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
有万把人,其实只有8000 子弟。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与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
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
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
和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后来,在湘鄂
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游击战争,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
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二军团有了这
块不大的根据地,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利于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
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南、贵州
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 里,人口只10 万以上,人少粮缺,
从两军团会师后的发展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很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
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
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
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二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
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
陈渠珍部3 个保安团,和民警团防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
雷明九、廖怀中等部约4000 人,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
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
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
壮大,扩大部队。
10 月25 日,任弼时、贺龙等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以
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具体说明“两军团
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第二、在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
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同时,“主力由松桃、秀山间
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中央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26 日的复电中指出“二、六军团
会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依中央及军委指
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
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在(再)延误”等等。
对于中央复电,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对我们的实际情
况不够了解。为此, 10 月28 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
义再次电告军委,“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
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利于敌之各个击
破。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
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
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
只是在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
一些调整,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
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
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
一步加
强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六军团政治部、保卫部改为二
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六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六
军团抽调100 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
它工作。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欢欣鼓舞。在任粥时、贺龙、
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动了创建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然而,军委29 日复电夏、贺、关、任、萧、王,重申
既定方针: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保持两个军团组
织,两军团均接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住苏区休息,改
编后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
团则应背靠乌江,箝制印、秀之敌,向敌积极行动。要两、
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
直到11 月13 日,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
地域,两军团在同一地区行动。16 日,中央书记处给二、六军团来电,对建
立根据地、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作了指示。决定成立以任
弼时同志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
(即湘鄂川黔省委)。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
留二、六军团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
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粥时
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1 月下旬,军委电报:“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
应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
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沉水流域,主力应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派出
得力的游击队活动。。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军
委同意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军委决策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主观方面讲,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
区,转移的基本方针是进入湘西,会合先遣队红六军团和在湘鄂边活动的红
三军(即二军团)建立根据地。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
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李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听说二军团巩固了湘
鄂川交界处的根据地,觉得这块三角地区位于长江附近,是中国内地几个最
发达省份交界点,战略位置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很好的
立足点。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也认为只有到湘西和红二、六
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正是出于这个战略意图,他们要求红六军团
尽快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的到达和创建新根据地做好准备。
但是,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引起敌人警觉,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明中央
红军将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便调兵遣将,部署了5 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
张网以待。这时,军委对于第六军团的实力又估计过高,过多的给予红六军
团箝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也有不少不适合于游击战,运动战
的硬性指令与批评,如要求红六军团这支转战千里的3000 疲惫之师,继续去
完成打击强大的湘敌和深入没有群众基础地区的先遣任务,显然是不适宜
的。
军委对红二军团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当时红二军团已停止肃反,但已受
到严重的伤害,元气大伤,正处于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和创建新苏区中,军委
却要他们以黔东为依托,箝击黔敌,也是不切实际的。军委对湘西地区及敌
方情况掌握很少,而又作过多的具体指导,很不利于下级的灵活机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的两军团首长对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
提出了建议,并在向军委申述意见的同时,从实际出发,见机而动。不久,
取得了十万坪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沉
陵,从而调动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