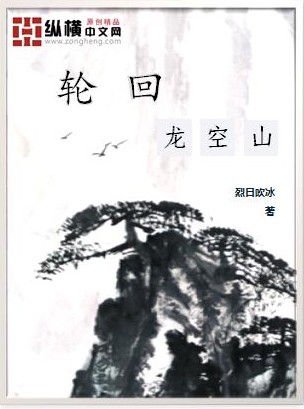空山疯语-第2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稿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熔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
何谓现代派,不去管它——一个名目越下定义就越定不住它的义,最后反而以乱哄哄的眉目淹没了原来好端端的名目——反正是指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那么一伙子诗人写出的一堆有那么一股子独特气味的诗。气味独特在何处?也可换句话说与先前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曰:东方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枪毙了旧体诗。新诗向何处去?先是穿起了白话的外衣。然而,光凭一剂白话药,并救不了诗的命,“大黄月亮真好看”算不得诗!自家的衣钵既已毁弃,异域的香火自然分外诱人。于是歌德海涅惠特曼、拜伦雪莱泰戈尔纷纷光临,一时间高朋满座,浪漫主义诗歌几年内在中国跑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稍后,李金发等人又将波特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仑这一路象征主义大师奉为上宾,刻意仿效。中国新诗贪婪地吮吸着西方的乳汁,而西方本身的推陈出新也正源源不断,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意象派……令人目不暇接。在各种外国现代派的蜂拥浪激下,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象征派发展的末期诞生了。它的基调是西方的,但是它的色彩却闪耀着东方的光泽,它的意象中结合着意境,旋律里潜藏着韵律,尤其是诗体建筑的“软件”中,充斥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基因。凭借这样的东、西方双向的美学追求,现代派诗歌登上了30年代诗坛艺术的高峰。
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这一批诗人,具有颇为深湛的古典诗词修养。他们在诗里有时随笔套用甚至直接仿造、嵌入古诗的句子。如卞之琳的“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音尘》)便是糅合了“古道夕阳”和“西望长安”两个最常见的古典画面。戴望舒的“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是糅合了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和“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两个古诗意境。还有,戴望舒的“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夜思》)化用了李商隐的“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何其芳的“空想银河落自天上”化用了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他的“沧浪之水清兮”(《枕与其钥匙》)则是直接搬用了上古《沧浪歌》的句子。
当他们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时,闻一多等正在大力倡导新格律诗。戴望舒虽然在诗的内部结构上受魏尔仑等的影响,走象征一路,但在外部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响应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如《塞风中闻雀声》、《自家悲怨》、《流浪人的夜歌》等早期诗作都是字数齐整,韵脚分明。但这种豆腐块似的格律体很快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画地为牢。戴望舒自己说:“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论诗另札》)戴望舒终于为自己制出了鞋子,他虽然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同上)但这指的是表面上的声韵和那种所谓“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词汇的准确。一切优秀的诗篇中都少不了音乐和绘画,不过有内在外在之别而已。
不懂得古诗的人,往往以为古典诗词的美只是体现在押韵、平仄上。其实,许多古诗(尤其是先秦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音乐性,为什么人们仍然爱不释手呢?没有内在的艺术之美,仅凭声律的外壳,中国古诗怎能雄霸千载,至今衰而未朽,垂而不死?美的内容必然要求有美的形式,“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语)旧体诗蜕变为新诗,决不意味着、也决不可能完全抛弃几千年积累的艺术经验。没有拿来,固然没有新生;但没有继承,就会连“拿来”也无从谈起。初期的象征派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