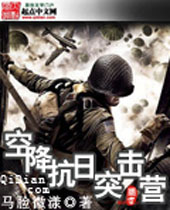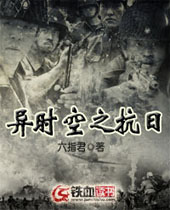抗日之虎胆威龙 作者:春来江水绿如蓝-第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嬲匠∠嗯浜闲纬啥匀站募谢魈啤V腥照秸亟て诨�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
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 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 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6'(p59~60)。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 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 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机轰炸重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 余人, 炸伤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6'(p26)又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 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p94)。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抗战时期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之伤亡人数, 共计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负伤13908人'9'(p81~82)。另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 炸伤市民9141人'10'。在这些统计资料中,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分歧较大,从二万人到近四万人不等。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近四万人之说似有夸大,可能是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二万人之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得出,而当时的统计由于多方面原因存在诸多遗漏。因此,我们认为伤亡二万四五千人之说比较可信。但这一伤亡数字中关于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计数字计入的。大隧道惨案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各种资料分歧也很大。当时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992人、重伤入院者151人'9'(p86~87)。而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亲历记》一文中认为“一夜之间因窒息而惨死市民近万人”'11'。这二种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较场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万人,惨死近万人说显系夸大。此案与防空当局玩忽职守有关,审查报告公布的数字当有保留。据当时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说,从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数为4000人'1'(p93~94)。因此,我们认为这次惨案实际伤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统计的数字多出2000人左右。这样,日机轰炸重庆的伤亡人数就应该在二万六七千人左右。
在财产损失方面,1948年2月,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估计为近64亿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其中私有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7'(p112、p220)。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损失情况没有包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企事业方面。事实上,除守卫重庆的空军和高炮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在渝国民政府各直属单位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如第21兵工厂,曾遭受日机14 次以上的轰炸, 财产损失达800万元左右'12'。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重庆市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注:见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第112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48年2月26日
单位:元(按1937年币值)
价值 公有 私有项目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合计农业 331371 331371工业 451004912 483397977 934402889电业 2002779 5903 2008687商业 902182820 87581086 989763906金融业 7603824 7603824交通运输业 3454382652 5855174 3460237826政府机关 382494 178196 560690人民团体 261607783 95024655 356632438普通住户 623861553 623861553合 计 382494 178196 5702977694 671864800 6375403184
日本对重庆轰炸造成的损失远不止此,在残酷的轰炸中,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三、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军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
反轰炸斗争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消极防空工作受到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 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经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也只有300余架, 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900架左右, 且飞机性能先进。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 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1939年春,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只有20余架,地面防空火炮也仅有10余连兵力。特别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战以后, 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由于积极防空能力的有限,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并在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严格实行防空警备等。
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在主持与组织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在反轰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挥和协调,包括有防护机构、避难机构和救济服务机构等组成的防空防护体制。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后经多次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关。 在指挥和协调防空情报网络建设、空袭警报传递与发布、防空洞建设与管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抢险救灾,建立了重庆市防护团等机构。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下辖消防、救护、工务和防护4个直属大队,人数最多时近2万人。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办事处下辖空袭服务总队,它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解决市民避难设施,先后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指导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筑。为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在日军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当然,防空当局在领导和组织反轰炸斗争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一些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当局就负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