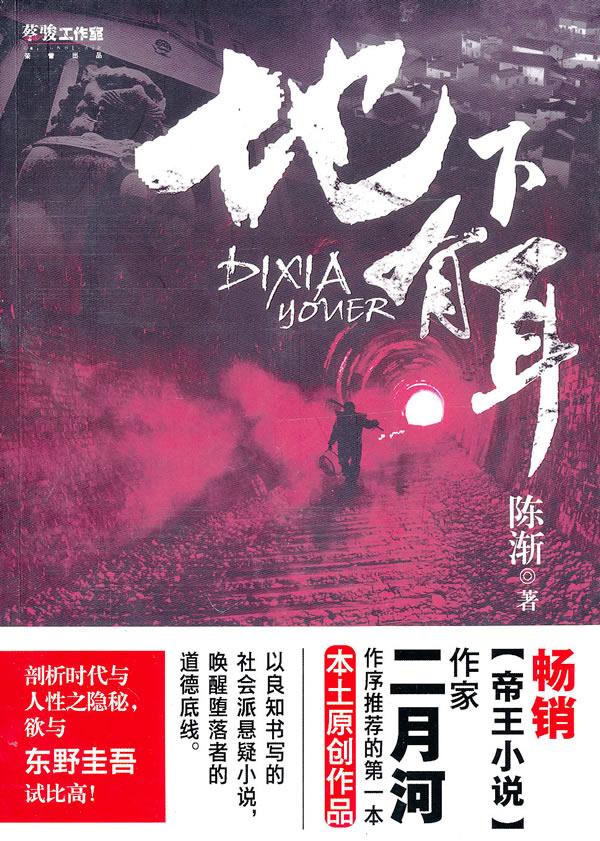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9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由于焦急不安和怜悯自己,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向游击队的宣誓、我是个共青团员——这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要枪毙自己的战斗姐妹的司令员。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如果您要枪毙我,还是我用手枪自杀好些。’
姑娘们,这样可以把自己毁了,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做。后来我还跑到自己的巴利茨基那里,投在他的怀里直流眼泪。他也有些焦急,骂起费多罗夫来了。但是他毕竟理智恢复得早些,想起了纪律。他劝我道:‘去吧,马露霞,证明一下!我们俩反正会得见面的。我相信这一点!’
我和他严肃地告别了,和费多罗夫也同样地告了别。费多罗夫没有和我握手,只望了望我的眼睛,可是我扭过头去,认为他十分委屈了我。
现在,你们听着,我明白了什么。每一个人,游击队员也一样,都可能受委屈的。姑娘们,焦急也好,委屈也好,只是这反正一样不应该危害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不好好地裹扎伤口,洗涤伤口;决不能在负伤同志的面前放肆起来,他是在等着你起死回生。精神上的勇敢在这种场合也许比在战斗中更重要。要克服自己,假如你感到不能忍受的话,藏到树木繁密的森林里去,在一棵树的背后耽上两分钟,然后带着微笑回到伤员身边去。就是因为这个,女卫生员才会获得勋章。
这样我就同伊凡·费多罗维奇的那个组走了,以便把两名重伤员送到谢明诺夫卡村去,他当过那里的党区委书记。任务是:把伤员们安置在村庄里的自己人家里;安置好以后,赶上队伍,但事实上没有办到。
我们在夜里推进,用担架把伤员抬在肩上。我们全组有十一个人,其中有轻伤员,也有病员;还有三个孕妇和一个带婴儿的。这些妇女,都是我们在前几天走过被扫荡队毁灭了的村庄时加入队伍的。在那里,扫荡队见人就杀,妇女和小孩子在一块儿被枪毙。这三个逃出了虎口。费多罗夫本来想把她们用飞机送到后方去,但那时没有反击。现在我们的小组应该把她们藏在自己人家里。第四个妇女的手上抱着五个月的婴儿。她的丈夫是游击队的向导员,是当地人,在德寇手里牺牲了。她也不能留在原地。
你们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的环境啊。我在两星期前才把自己的孩子埋葬了,而这件事使我回忆到,我常常躲在树背后哭。小孩啼哭会暴露我们。此外,还有疲倦。我们大家倦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睡得着。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露霞,这是一把耙,你躺上吧。’我也会躺在耙上睡着的。
姑娘们,你们可能这样想:‘她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惊心动魄和艰难困苦的事儿,在嚇唬我们吗?最好使我们回家,到妈妈、爸爸那里去。德寇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打死。如果被送到德国去的话,从那里可以知道——那里也是人,不管怎样,我们是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的。’
不,我讲给你们听,就同讲给亲爱的苏联姐妹们、战友们一样。我不是在诉苦,而是说:‘人能够克服而且应该克服的什么,假如他效忠于苏维埃政权、效忠于党!这是当着最野蛮的法西斯的嘴脸为自由而作的斗争。这不仅是在开枪的斗争中的斗争,这也是以后当扫荡队用饥寒与森林的潮气来折磨我们时的斗争。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个准备。也许死还比较容易些,当把你在群众面前带上绞架时,在那里可以表现得悲壮而且骄傲。万一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会坚持得住,我也同样坚持得住的。不过在这以前,应该为生命、而且不仅为自己的生命,为正在黑夜中冒着倾盆大雨、痛得在哼叫的咱们伤员同志们的生命而坚持斗争。
有两名受了重伤的是安德列·古拉克和谢尔盖·波马兹。我们把他们送到游击队员的一个兄弟住的农庄里。已经和他说妥,由他留下一名伤员。我们的伙伴们连夜去找他,说是我们来到了,伤员在森林里,可能过一小时就会给送到。而他回答说:‘你们要知道,红军正在节节后退。当红军还没有开始进攻以前,我不想帮助你们布尔什维克。’
‘你为什么早先答应了呢?’
‘老实说,我原以为红军比较强大。’
原来,他已在德寇那里干管理员的工作,彻头彻尾地出卖给他们了。
我们企图第二次安置伤员。勃列什涅有个游击队员斯捷潘·斯坦琴科的家属。他女儿普罗尼亚在我的队伍里,另一个女儿托霞是个教员,暂时还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侦察员——两名游击队员到村子里去了。老头儿对他们说:‘我同意留下一名伤员。明天托霞去把耙集干草,带些面包还有一点别的东西,要在你们那里一直逗留到黄昏,然后你们同她一起来吧,把伤员带来。’
托霞来了,在手提包里带来了一些吃的,并且说,德寇在两小时前到了勃列什涅——有一个多个扫荡队员。我们侦察了一下,果真是这样。只得留在森林里,给自己挖地下室了。
斯坦琴科老头把砖头和粘土送来给我们造了个炉灶。然后送来了面粉,把一些怀孕的带去,安置在各个人家。托霞和斯坦琴科老头把那个带着婴儿的妇女领到距离十五公里的另一个村子里去了。后来斯坦琴科突然失踪,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来。有消息说,老头儿们给德寇抓住,送到诺夫哥罗德-斯维尔斯克去了。他们俩在监狱里被拷打,受不住刑,都死掉了。托霞从德寇那里逃跑了,在另一个村子里住了些时候,过了十来天,她跑到森林里来找我们,开始和我们一块儿打游击。
我们的地下室是在枞林深处,在树木最繁密的地方。谁都发现不了我们。我们总是在天色微明的清晨烧炉子。我在三点钟起来升火,然后准备给伤员们包扎伤口。有时象个流浪者一般到勃列什涅去讨一条旧床单或毛巾。人家给的时候也不加过问,大概知道我是谁。古拉克开始有些儿复原,真叫人高兴!这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而他可以说曾经是一具尸体:浑身——满脸、满胸、满背都烧伤了。后来我的古拉克就开始行动了,甚至还请求站岗。
而谢尔盖·波马兹的盘骨被打坏了,只能躺着。身体倒是健康的,可是站不起身来。我为他忍受一切,给他洗涤……我很害怕坏病,他自己也害怕——由于这种害怕,他吃不下饭,瘦了,睡觉时大说梦话,好不嚇人。白天还好,他有些精神。他的创伤五个多月没有养好。大概我们甚至在冷天也把他放在太阳光下照晒而生了效吧,当我看到创伤开始收口时,我的谢尔盖微微地笑了。他开始请求弄些肉吃。这就是说,他复元了。
我们到伪村长那里去偷了一头羊来宰了,把肝儿炒来吃。大家高兴极了:‘瞧,目前这几天里大家会吃得饱了。’我把羊肉挂在树枝上。伊凡·费多罗维奇说:‘今天你做个羊糕,烧些菜给弟兄们吃个饱吧。’
我拿羊肉去了,走到跟前,只悬挂着一些骨头,完全给喜鹊吃光了。我们只得舔舔嘴唇……可是我把骨头煮了,清汤是很肥美的。我们再没有去碰另一只羊。村子里已经够惊慌了。
我们这样过了六个月。这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夜里两点钟,听到了脚步声。我坐起身来。我有两颗手榴弹,就这样决定:一个投向谢尔盖,把他炸死;另一个投向门口,而用手枪来自杀。吉洪诺夫斯基和其他三个弟兄正在玩骨牌。门突然打开了,有个穿白色罩衫的男子走了进来。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拿起手枪,我也挥起手榴弹。
‘住手,吉洪诺夫斯基,别开枪!’
这是我们的人来了。队伍回到了叶林诺森林,波布特连科立刻派人来找伤员们和整个小组。关于我们,有人说,全体给德寇抓去了,所有的人几乎全被打死了,而我却受了重伤。并且好象是后来有个德寇军官和我结了婚。简直是胡说八道。波布特连科不相信。
我们都坐上橇车,被送往营地去。是怎样迎接我们的——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大家都吻我们,还给我们唱了几支新歌。女炊事员特地为我们备办饮食……但这以后再讲吧……第一天我就知道格列沙不在。
格拉沙哪里去了?他健康吗?
‘据说:在莫斯科呢。’
我想:送到莫斯科去的只有重伤员。我问:‘他哪里受了伤?’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许他已经功成名就,被送往莫斯科休养去了!……’
但是总还是有人告诉了我,他鼻梁和一只眼睛给碰伤了……过了几天,飞来了一架飞机,我们跑去迎接。当我们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大家已经走出飞机。我跑去找巴利茨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而我在他一旁跑了过去……费多罗夫给我问了好,拥抱了我。
‘你为什么不给格列沙问好呢?’
‘他在哪儿?’
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个漂亮的男子,打扮得够俊,胖胖的,戴着高高的帽子。我想,这个焕然一新的人,不是格列沙。当我带着我们那组人走开的时候,格列沙是穿着棉袄,戴着便帽的……
‘而我呢,’他说,‘看着——她向谁跑去了,谁是她所最珍贵的?’
于是我抱住了他。这时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跟摄影员说:
‘快拍!’
我问格列沙:‘你的眼睛怎样了?’”
他淌下了眼泪,可是他说:‘能看得见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叙述完了。现在请别人来讲吧。”
马露霞讲完以后,大家好久没做声。可以听到篝火中的树枝发出拆裂声,就象马儿用牙齿咬嚼着青草一般。马露霞走进阴影里,坐在一个人的宽阔的背后。那时我想会有人详细问她。不,好像大家同意了,在这种叙述以后应该把思想集中一下。许多人瞅着巴利茨基,他就站在那里,带着很自信的姿态。我感到他不满意马露霞的叙述,甚至想推翻她讲的某些东西。他整个的体态、服装、风度,都可以看到他的豪华气派。他头上戴着一顶要掉下来的、飘有红带的黑羊皮高帽。天气早已回暖,还戴着冬天的帽子是可笑的;但巴利茨基不是人家可以来取笑的那种人。
在那个时期中,他的声名在我们队伍中是最卓著的。这是大无畏精神和军事上的幸运的声名。敌人的子弹都放过了他。不错,他丢了一只眼睛,但这是自己的冲锋枪的弹壳打的。
巴利茨基没有立刻就开始讲,不得不请求他。也许他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讲吧。早晨我和他争论过一阵。他是昨天从莫斯科回来的,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形。而今天他突然交给我乌克兰司令部的命令,里面指示我拨出一定数量的人员——普通的战士和指挥员给他,同样拨给他武装、弹药、口粮,建立一个以巴利茨基为首的新队伍,而且这个队伍要按着独立自主的行军路线前进。
没有办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命令是必须服从的。我对巴利茨基说,每一个大队的指挥员都会拨给他一部分自己人。但是巴利茨基要求我下命令,把他指挥过的第一大队拨给他。我们认为第一大队是我们联队里最好的一个大队,里面大多数是老游击队员,都是切尔尼多夫人,我坚决拒绝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用无线电征询了一下乌克兰司令部。那里支持了我。结果巴利茨基放弃了独立自主的任务。我们决定了巴利茨基留在联队里当第一大队的指挥员。
但是他显然到现在气还没有平。他不时向我这边含怒地斜着眼瞅看。毕竟被人家说服:他开始叙述了。他带着不太注意往事的那种人的样子叙述着。听众觉得他讲得有些儿自高自大,但是却原谅了他这一点。也许有些人还认为著名的游击队员应该这样说话哩。
“我们在这里感怀往事,甚至嘲弄自己。我们每个老游击队员都经过了许多次死亡。即使谦虚地来计算,我个人就逃过了二十二次死亡,而且继续在行动。有时我问自己:‘格里戈里,为什么你还活着呢!保护住了还是侥幸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战斗以后依然无恙——既不是你个人的幸福,也不是为了休息或光荣而留了下来,而是为了继续斗争到最后胜利!’
如果谈到抒情的和带诗意的事儿,对我来说,一直到战争结束,最带诗意的是敌人的死亡和覆灭……我是一个有目的的人,而且现在要同大家谈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过一位同志,他曾经很勇敢。但一切都精打细算,他说:‘我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接触了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我的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