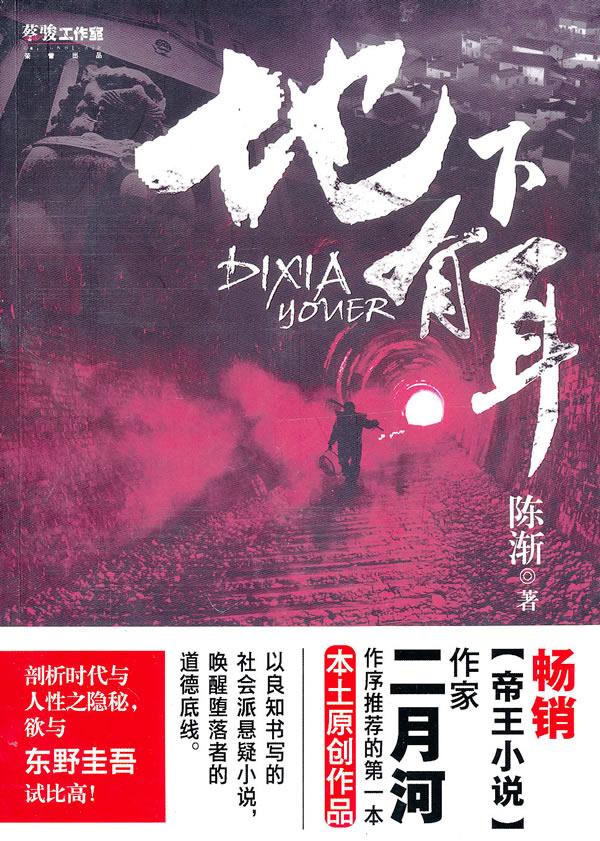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是一个相当魁梧的汉子,比中等身材高些,肩宽背阔,目光很聪明,甚至很坚定,据他说,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过来往。
“让我抽支烟吧。”
我们给了他。他卷了一支烟,把衬衫扣上,眼睛瞅着一边,开始说:“当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们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心里混乱地摸不到头尾。你们想想我现在有多大岁数了?”
“你怎么啦?”索洛伊德喊道。“你是在篝火旁边讲故事吗?你现在应该是回答而不是发问呀。”
加柳依向索洛伊德看了一眼:“打吧,你要想打就打吧……我为什么要问你们,我多大岁数: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快五十了。你们同意这一点吗?这就很好。而我才三十九岁。我是个疲——倦——了的人!清楚吗?你们要知道,我现在连喝酒都不感兴趣,因此也不珍惜生命。我从这种生活里,久已看不到什么好处。而你们说,过德涅泊河再往前走。我不须要去,我疲倦了,厌烦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谈这个缺德的人呢?我们当时把他看做是个行尸走肉,一种动摇的、懦弱的、没有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极端表现。他把自己不太长的生活里面所从事过的一些职业数说了一下。他曾经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炼钢厂里当过计时员,后来在几家饭店里做过两年的侍者……
“这是一种吃得饱肚子的事儿,但是要求很大的忍耐性,要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如果不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或者不会使用餐巾,那就只能抽抽‘拳击’牌低级烟,穿的衬衫也不会比棉布的再好……”
“噢,原来你是这样的观点!”
“是的,是这样的,”加柳依肯定说。“侍者这种职业的主要缺点是腿酸……最近八年来我是在弹子房里当记分员。嗯,记分员就不是侍者喽,不必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了。商业弹子房的记分员,如果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不是个胆小鬼,那就是个活神仙、审判员和军事长官……亲爱的同志们,我结了婚,仿照绸缎的花色把屋子油漆了,还买到了一项红木的衣橱。我的那个美人儿,活象个商店经理的太太:灰背大衣、八套中国绸子的长外衣……你们要知道,”他突然使劲儿带着优越感喊道:“我自己有两双漆皮鞋,不算麂皮鞋在内;有哔吱西服、上等的呢西服和夏季的咖啡色纯毛料子的西服。所以我有的是很好的生活,而我的浪费也就不少。况且爱情是象一种神圣的、最强烈的感情。唉,有什么可说的……”
“你在红军里服务过吗?”
“没有机会啊。德寇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来的前一天,我才被动员。那天晚上允许我回家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而第二天一早,一切就天翻地覆了……你们要听,我还可以继续讲讲,我怎样和爱人到索斯尼察她娘家去的,怎样我过去的爱人,原来是个小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衣服料子跟奥地利人跑掉了,怎样威胁我要把我好像是一个熟练的铉工似的抓到德国去:有这样的密告,说记分员加柳依实际上是七级铉工。我又怎样揭穿了这个诬告。这一切我都可以详细地讲一讲。”
“你为什么当了伪警呢?”
“就是这么当的。我并不否认这件事。我是内心极诚实的人。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段生活中,要不这样,就无法对付。你们要知道,我是为了弄到武器才干这件事的。我达到了目的。我把我爱人瓦列丽亚的相好当着她的面前打死了。我也想同样地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打中……”讲到这件事,加柳依喘不过气来,面目也憎恶得变了相。“但是反正那些奥地利人会把她害死,结束她高等娼妓的桃花运……”
“等一等,”我打断了加柳依的话,“您这是实现了报复私仇的举动,然后跑到我们这儿来的。您认为自己是个游击队员吗?”
“你们知道他们会把这个瓦列丽亚怎样摆布吗?你们绝对相象不到。他们会把她塞进兵士的妓院,在那里她是活不了两个星期的。她的心情过于柔弱了……”
“别乱扯了。我问您,在游击队里宣过誓没有?”
“我自己知道,宣过誓了。可是我不打算再走远了。我憎恨这样的德寇;对这些腐败的家伙,这些伪警,我是彻头彻尾理解、瞧不起、并且憎恨的。您下命令叫我射击,我会遵命执行,会趴下去用尽子弹消灭那些……我的瞄准是头等的,因为我是弹子房的记分员。而这里我是什么东西呢,已经有四天反正和苦役犯一样:推呀、拉呀、拖呀……看来好像是个健康的人,可是我现在只剩下了哆嗦。”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而他突然用很可怜的、哀求的声音说:“我什么都没有反对你们。你们须要这样做,你们有理想。这点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把我放走了吧。我自己会打德寇。稍稍休息一下,我就要用自己的非党人员的方法去打。”
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小市民,他为了自己,并且只是为了自己,活了自己的整整三十九岁。对他来讲,战争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他的报仇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痛苦,为了自己的感受。他健壮的身体因为长期的紧张状态而萎靡了,软弱了,甚至连生活的意志都丧失了。
不,我们没有枪毙他,虽然可能由于他临阵脱逃而应该枪毙,只是把他的武器收回了。我们知道,他赤手空拳离开我们是什么地方都不敢去的。我们叫他去锯劈烧饭用的木柴,而在战斗时递送炮弹和子弹箱。他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在以下的几章里讲到。
从贝瓦洛克过去,我们就按着预定的行军路线乘车前进,坐在滑木上简直拖不动了。多谢贝瓦洛克和附近乡村里的农民:给了我们货运马车、半蓬四轮马车、两轮车——一共给找到了大约二百辆马车。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橇车,外加二三十匹马给他们替换。载重车队不得不大大减少,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步行了。
我们平静无事地走了二十公里光景,主要是和解了冻的、泥泞的道路作斗争。突然一大队德寇从森林里来袭击我们纵队的前哨。没有打好久,敌人便乱七八糟地退却了,损失了十二个人,并且扔下了一挺重机枪。老实说,这不能算是战斗,只是小冲突罢了。但是在这次小冲突中,牺牲了我们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位是机枪连长耶菲姆·多罗申科,另一位是同一分队的女卫生员诺娜·波古略依洛。
我们把他们的遗骸安放在两辆大车上,以便在附近的居民点里尊敬地安葬。这是游击队的惯例——不立刻在作战的地方,而是尽可能在村庄附近的大宿营地埋葬在战役中牺牲的同志。我们经常竭力设法把这种悲伤的仪式举行得隆重一些,并且请当地的居民来参加: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和战友们告别的,让他们听听我们英雄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居民们和我们在一起致哀,在坟墓上献放花圈,有时侯还建立一些小型的、简单的纪念碑。
可是我们载着用旗帜盖起来的遗骸,常常经过几个沉痛的、十分沉痛的钟点,有时侯甚至经过几昼夜,当然,所有的游击队员都知道那辆大车上载着被敌人打死的战友。好朋友们和女朋友们长久在大车旁走着:哭着,发誓要报仇。在这样的时刻,队伍就好像是殡仪行列一样。歌唱咧,说笑咧,都停止了,人人都变得更严肃,更沉默。
有人说,战争会把人变得残酷无情。向右是死亡,向左也是死亡,甚至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觉得明天,或许过几小时、过几分钟就会有什么亲近的同志牺牲似的。自己牺牲的可能性也不例外。但是我前面写的对死亡“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这一行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当然,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怎么能习惯于想到自己的朋友,或者爱人,或者子女过一忽儿就会牺牲啊!坚决性在成长着,而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预先培养自己在人们面前不痛哭,不搓手等等。
这次小冲突以后,纵队在继续前进的时候,诺娜·波古略依洛的青年丈夫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抓住了躺着她的遗体的运货马车的边缘,跟我们一起走着。他是个青年人,共产党员,机枪分队的指挥员。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六岁。他热爱诺娜。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开始的,我虽然不知道;可是我肯定地知道,并且永远记得,我看出这一对是存在着那种可以称筽高尚纯洁的爱情的。
那时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啦。我的高尚纯洁的爱情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开始的。我很走运。我们的背后没有拿着冲锋枪的死神来威胁我们。谁也没有妨碍过我们赏月、或是在草原上游逛到天明;谁也没有喊过“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我们经常工作,可是黄昏呢,却一定是我们的。不错,有时侯要开开会;但是开过会就可以到草原上游逛的啊。
青年人阿夫克先齐耶夫为什么、由于什么缘故,明天该在他所不熟悉的村边的谁都不知道的墓地上安葬自己的爱人呢?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还不让哭。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是不能哭的。他是一位指挥员。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就起来率领红军的二十六名战士和军官,把这一小队带到了游击队里,并且竭力设法把他们全体吸收进支队。他也就是那个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整个联队对认为他是个沉着、聪明、勇敢的人。他从来没有对战士们粗声大气说过话……他没有拒绝过玩乐,可是一般地讲来,他是个严肃的人,并且首先是对自己严肃。
而现在呢,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的、瘦瘦黑黑的、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在走着。他抓住了运货马车,有时侯跌跌撞撞,大概是眼力不好——一路在沉思默想,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抑制着,但是如果现在发生战斗,谁也不会让他不去参加战斗的……
在世界文学中有一些广大深远的爱情题材,恋人们为了这种爱情而去受拷打,或是去犯罪。兵士霍泽由于卡门的缘故变成了逃兵、走私者,终于走上了绞架。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对这种顽强的人表示一种敬意。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他的情感的力量啊。再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彼此热爱的,他们蔑视那种使他们两家分裂的世仇。
有人存在着这样的见解,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恋爱衰落了,说什么,消失了奋不顾身的热爱的范例。也许有些读者谈到阿夫克先齐耶夫会说:“假如他真的爱她,那就会想办法使自己的诺娜预防子弹;而她也应该战斗中保持得更小心,不去螳臂挡车,应该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保全自身。”
可是我却不是那么想。阿夫克先齐耶夫爱上了诺娜·波古略依诺并不是仅仅由于她小脸儿漂亮、大眼睛好看、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次于卡门。他是爱她的勇敢、轻视死亡,爱她的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忠心。
我起码来到依里亚跟前,下了马,我们并排着默默地走了几分钟。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想说几句,却又找不着必要的话来。
“有一件事是不能饶恕自己的,”阿夫克先齐耶夫说出来了,头也没有向我转过来。也许他甚至多半是向自己讲的。“为什么允许她和我一起来……”
“说出来吧,依里亚,也许会轻松些。”
“阿列克赛·费多罗唯奇,诺娜只是为了我才来袭击的。您记得吗?她要是留在波布特连科那儿,也许就不会牺牲了……”
“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你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
他没有听我的话,继续说自己的:“现在她躺在这儿——我弄不清楚这件事——她突然死了,难道是我的不是……除了她,我什么人也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也没有……”
“唉,阿夫克前齐耶夫同志,你说的这些话,我真不爱听。你应该抑制自己。老朋友,你想想:她怎么会单为你一个人来袭击……”
无须来提醒他,他自己突然想通了,并且据我看来,这一个新的想头甚至使他高兴起来:“可不是,照我这样说起来,我太看重自己了……”
“你还年青,前程远大……”
我说这些干什么!的确,我说的这些话结果并不太妙。可是碰到别人有极大的不幸,我们就往往茫无所措,而讲些一般的安慰的空话了。
他是怎样地看了我一眼啊!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的眼光里现出了一种责备我不懂礼节的神情,甚至似乎是一种警告,好像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