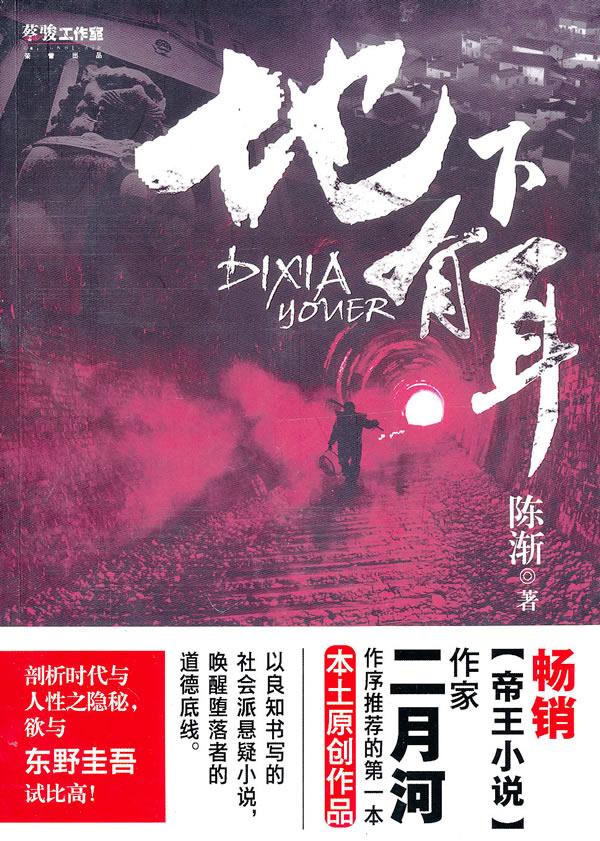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与他们当时工作的条件很少相同之处。
我以为巴丘克的问题:应不应该准备恐怖行动,应不应该组织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是由一个老党员向他提出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社会制度而战斗。因为德寇在他们占领的乌克兰还没有实施、而且远不能实施资产阶级的制度,虽说他们当然力求这么做。他们只是暂时占领了土地而已。战争还在继续下去。德寇不仅在对红军作战,而且在对全体苏联人民作战。我们,无论是游击队员也好,或是地下工作者也好,全是军人。我们在作战。扑灭那些指挥官、农产部长、头目以及一切其他部长,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而不是恐怖行为。扑灭人民的叛徒——伪村长、伪市长、伪警察——也不是恐怖手段。他们是人类的螽贼,不是某种新政权的代表,而只是间谍、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是罪犯,我们不是杀死他们,而是按照祖国的法律来处决他们。
卫国战争中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前者是在相当规模的军事化团体中生活和活动,后者是被迫个别地生活和更秘密地活动。
沦陷区的苏联人民极其明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甚至最落后的农民也很快就明白占领者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不断地高涨了。
但是假若我们留在沦陷区的千百万人民知道了敌人的全部实情,哪怕知道了早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统治乌克兰的敌人死的已比活的多,那么他们的抵抗还会增加好多倍。
由于对民众说明前线的真实情况,由于经常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由于揭露德寇的战略手腕——他们的土地法、‘自由乌克兰之友’的把戏、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其他等等鬼计,地下工作者振奋了人民的精神,帮助了游击后备队的建立。
在城市或乡村里的地下工作者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阻碍德寇法律、决议、命令的实行;组织企业和农业公社中的怠工行为;揭发卖国贼;收集和转递武器和军火给游击队;为游击司令部和红军进行情报工作。
然而我在这里未必能列举地下活动的战士的全部职责。他的权利和物质上的机会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他们是受更多的限制的。对于雅勃隆诺夫卡地下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去获得生活资料,我们只能答复一句话:同志们,去找工作吧,别管它是什么工作,你们要象老乡们一样地生活,要到处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去给暴发的富农和地主们做雇工,去参加劳动组合,到铁路上或者德寇的行政和经济机构里去工作。我们必须到处有自己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德寇的占领机器。不过你要脊柱,只能按照组织的指示到这种地方去。
至于说到那些因受恐惧心的影响,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情况’向德寇登记并去供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他们是没有辩护理由的。不管钳工尼坎诺尔多么令人同情,但奥斯捷尔组织拒绝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是正确的。而格列申科说起的小学教员也必须马上开除党籍。
为了在人民的面前赎罪,他们在沦陷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就是参加游击队。在这儿,如果他们被接纳,就能够在同志们的留心监督下投入战斗。
但是读者要问: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尼坎诺尔和那位自认缺乏胆量的小学教员不是都到党的区委来认过罪吗?他们只动摇了一下子,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叛徒。
倘使他们是叛徒,那么就枪毙他们。不,我们不但批准了他们的开除党籍,还要求同志们把他们开除的事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决不能把自己的良心打折扣,共产党员无权片刻忘记人民把自己当作掌舵的党的代表人。当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犯了怯懦行为时,他使我们的事业遭受的损失,要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分子带来的损失大得多。
德寇郑重其事地布置共产党员的登记,挂起‘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在此登记’的大招牌。事实上他们想出来的登记本身并不是为了要统计和保证共产党员的安全。自愿去登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当然,德寇事先也知道,只有卖国贼和胆小鬼才会去登记,所以这批人就是不登记也是没有危险的。不,他们使这次登记具有另一种意义,就是想在人民中间打击共产党的威信。
后来钳工尼坎诺尔果真证明了他不仅不是个卖国贼,甚至还是工勇敢的人。他参加了游击队,不顾自己多大年纪,打仗打得挺好。象他所表示的,当时他被自豪心逼住了,不愿向德寇机器匠让步。由此可见,机器匠的职业的自豪心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自豪心更强有力了。
而在这时候,人民对苏维埃人的不屈不挠的公民的自豪心特别重视。当成千成百的无名英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单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侵略者的鄙视而慷慨赴难的时候,我们怎能原谅一个哪怕只是稍微向德寇卑躬屈节的共产党员呢?
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农舍里,在某处烧毁了的村落的瓦砾场上,在游击队的确篝火边,你总能听到关于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老乡们非常喜欢那些关于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的故事,关于视死如归的儿女们的故事,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称它为疯狂的勇敢的故事。到处重说着、补充着、流传着这些故事。
比如,有一个关于奥尔洛夫卡地方的老头儿麦伏季耶维奇的故事。我自己听到这个故事便不下十次。它是有一九四二年初发生的事实做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打听到麦伏季耶维奇的姓。
我们共青团员侦察组——莫加·佐朱利亚、克拉瓦·马尔可娃和安德列·华哲采夫——动身到各村去收集指挥部所需要的情报,顺便把传单分送给我们的人员去散发;他们把五百张目的在于反抗德寇的传单塞在怀里。
在奥尔洛夫卡这个大村庄里,她们两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和一年青小伙子在街当中走着。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些老头儿、老太婆,以及象自己一样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侦察员象他们打了招呼,打听到磨坊去的路,带便把小小的方块传单塞到了行路人的手里。
关于德寇多远的问题,行路人答复侦察员说,一切都好,这里早就没有那些恶棍了。
就在这时候,几辆装满德国兵的卡车开着救火车的速度闯进村庄来了。我们这三个人是跑不了了:要逃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德寇一定会追赶他们。侦察员们继续顺着大路慢慢地走,一面希望德寇会把他们当做本地人。
有十五个德国兵来到村子里,行动古怪极了:跳下车来向四面散开,专著了所有碰上手的人——老头儿、老太婆、少年们——把他们赶到卡车边,拿枪托冲着,强迫他们攀上车厢。他们没有搜查,也没有询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装满卡车,便开足马力向区中心霍尔梅镇的方向驶去。
侦察员们走上了最后的一辆卡车。车厢里挤满了二十五个人。大家你拉我扯地站着,全都吓得胆战心惊,眼睛乱翻,面无人色。
最初,他们只是互使颜色,但过了约莫五分钟,便开始低声交谈了: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们运到哪儿去呀?”
“为什么逢人便抓呢?”
人们在卡车里东摇西摆,你推我挤;他们倒下来靠紧着坐在车底上。姑娘们尖叫着,老大娘们呻吟着;她们已经变成习惯自己新的环境了。
“娜契卡,干么你一股劲儿压下来呀?”一位大娘叫道。“你要知道,小鬼,我的膝盖已经碰伤了。”
“没关系,婶婶,将就行吧,”从人堆里传来了不知是谁的老年人的沙哑的声音。“你们该道谢才对。他们是不收车费的。早先到霍尔梅去,你得出三十个卢布,而德国恩人却自己出钱把我们送上绞架去……”
“嗳,咱们的演员又胡说八道了,”大娘的声音回答道。“你还是不是闭嘴的好,麦福季耶维奇,没有你已经够受的了。”
但老头儿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说了句笑话来回答,好些人欣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位麦福季耶维奇想必是位演丑角的老头儿,在这样的局面下也毫不失去自持力。
侦察员们没有细听,他们哪有心思听这种谈话。他们三个人站在车板边,低声商量着怎么办。各人怀里还留下一百多张传单。不用说搜查,抓住他们领子摇一摇就够了——传单便散开了。
卡车的速度开得无论如何不下每小时四十公里。它按着喇叭飞驰过一些居民点,活像救火车一般。卡车车厢里没有德国兵;可是踏脚板上都站着冲锋枪兵。他们虽然多半向前望着,而且和坐在驾驶室里的驾驶员交谈着,但人们要在开行时偷偷地跳下,当然是不让的。
莫加是我们三个人中间最有经验的侦察员,她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向自己人使了个眼色,小心翼翼地从衬衣里拉出一包传单来,她把拿着传单的一只手伸出车边,使劲把传单扔在地上。风突然把方块纸片托住,卷了起来,在卡车后面飘摇,象一团云彩似的升了起来。
莫加面红耳赤,好象等着打击似地蜷缩着身子。卡车里大家都没哼声。传单早已看不见了,而卡车里人们还是继续站着,紧张,肃静,互相投射着探索的眼光。
于是又响起了沙哑似的嗓音:“这么说,德国鬼子不仅在抓人,顺便还在分送宣传品呢。真象一所带着轮子的联合制造厂!”
引擎在吼叫着,卡车在路面的坑洼上颠簸得轧轧作响;然而我们的弟兄们却好象听到了共同的轻松的叹息。
谁知道人们相信真是德寇自己散布传单,还是单为这很好的说明很高兴呢。无论如何,老头儿已把局面缓和了。谈话又开始了。
麦福季叶维奇已经从人堆里爬出来,安顿在侦察员们的身边。他原来是个干枯瘦小的老头儿。蓬蓬松松的灰色胡须,迎风飘着,鼻子冻得通红。可是他歪带着帽子,一撇小胡威武地向上翘着,眼睛里燃烧着狡猾的火焰。他又高谈阔论起来。他说话时显然不加思索,只是热闹热闹罢了。
“喂,先生们,”他捻着胡须叫道,“我们现在和外国人坐在一辆汽车里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没梦想到这种新秩序……”
当有人回答他时,他用肩膀紧捱着莫加,很快地开始低声说:
“小姑娘,你别白白地把传单抛在草原里呀。那是供给老乡们的,我了解得不错吧?……就是说,这要散在人们中间……你瞧,就要开过村子了,那时候再扔吧……”
当卡车驶近一座村子时,麦福季耶维奇开始奋激地碰碰我们弟兄的腰眼儿:“扔呀,你们怎么的!别怕,我负责!”
不可否认,他有淘气角色的天才,并且能把人家也激动起来。弟兄们在村子里扔出了一部分传单。现在卡车里的人当然全都明白扔的并不是希特勒匪徒了,然而好象商量好似的,装作若无其事。
孩子们在卡车后面追逐着,捕捉着飘在空中的传单。卡车里的人都哈哈大笑,全体老少都给这种游戏迷住了。
当踏脚板上的几个德国兵疑心地转动时,一个满面愁容的大娘叫了一声:“藏起来!”
车边上出现了一个兵士的脑袋。他什么也不明白,一对眼睛只是困惑地瞅着这些古里古怪的俄罗斯人。“他们在笑些什么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咒骂着回过身去。可是现在他们当然不能再扔传单了。德寇已警觉起来。
麦福季耶维奇情绪昂扬,不能自持了。侦察员们还剩下三百张传单。
老头儿恳求道:“把传单交给我吧……你们别害怕,我想法来打发它,交给我,喂,快点儿。人们将在咱们村庄里读到它。别落得一场空……”
他把剩下来的传单往衬衫领子下面一塞,扣上皮短袄,洋洋得意地微微一笑。他那么狡猾地眯起眼睛,使大家都明暸:现在他要表演什么精彩的节目了。
不错,麦福季叶维奇差点儿从人头上爬到驾驶室去。
“让开!”他喊道。“好人哪,让我过去吧,我受不了啦!”
人们还不懂他打算干什么,给他让了道,他向前挤去,疯狂地槌打着驾驶室的顶蓬。所有的人都寂静无声。卡车刺耳地刹住了。
“你们等等,等一下,劳驾,劳驾,只要一下子就行,立刻,”他咕咕哝哝地说,一面急忙攀下车去。
德寇继续笑着,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这时麦福季叶维奇走到灌木背后,把传单藏好,还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