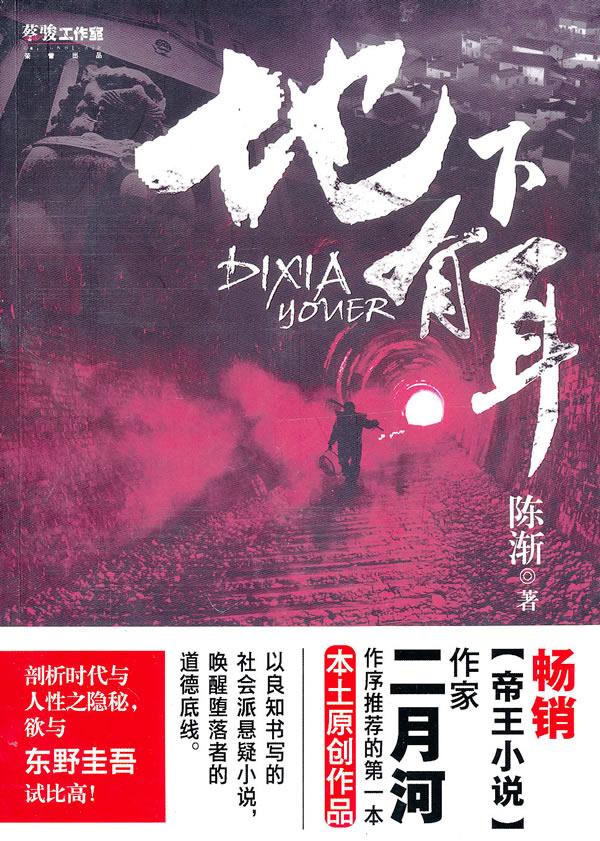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才知道其他的同情者早已先我们去了。我们哀悼了……
有一回我走着,碰到了科斯特罗马,可见她已被释放了。这么说来,我的话说对了,她和她的朋友马里亚出卖了我们的人。有个小伙子和她在一起,可能是个伪警。我把她叫到一边。她看我是个老太婆,并不害怕,走到我跟前。我悄悄地问她道:“姑娘,人家说你是信教的,常上礼拜堂去,是真的吗?”她答道:“真的,老奶奶!”并且拿无耻的眼睛瞧着我。“那么,姑娘,人家说,你是犹大的子孙,对不对?”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只是尽眨着眼睛。而我转身就走开了。
在我们共青团员被处决以后,大约只过了三天,老乡们当中突然又全都知道,苏联的传单在各个角落张贴开了。于是又和从前一样有从莫斯科广播的最新通报,此外还有科柳什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死也不投降!”这时人们才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你们虽然是自己人,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传单是谁印的……
我们得到报告,说是在科留可夫卡区·阿列克谢夫卡村边的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个快要死的犹太人。他不知怎的侥幸地从德寇那里脱逃了,现在害着斑疹伤寒快要死了。他说梦话时常常提到费多罗夫、巴丘克、波普科和波布特连科……
也许是祖谢尔曼吧?
这已经好久了,我一到省支队,便问起雅可夫。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消息。因此那时我同意这种想法,认为雅可夫在从依琴雅支队到省支队的路上落入德寇的手中而牺牲了。不管这种想法多么痛苦,但是要知道,战争就少不了死亡……
一天晚上,我摆脱了自己支队里的事情,邀请第一分队的指挥员格罗明科一起带了一小队战士,动身前往离营地三十公里的阿列克谢夫卡。
派在先头的侦察员报告说,村里没有德寇,而那里的伪警都是很恭顺的,也就是说,不过是一些胆小鬼罢了。我们直向指定的房子奔去。窗户里暗淡地点着灯。我命令随伴的战士们在四周布好岗哨,我和格罗明科上前敲门。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给我们开了门。她穿着一件外套走到台阶上,用背推上了门。
“西多罗夫娜有病,”小姑娘说,“她正在浑身发抖,吩咐我谁也不让进去。你们是些什么人呀?是警察吗?”
“我们是亲戚,”格罗明科说。
“您撒谎。西多罗夫娜根本没有亲戚,只有妈妈和我一个人……你们最好还是别进去,我们这里有人害伤寒。妈妈派我照顾西多罗夫娜奶奶的,给她弄吃食。我正在给她煮稀饭。”
但是我们还是走了进去。小姑娘那对灵活的、稍微有点儿古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屋子里月光比灯光还亮。墙壁都熏黑了,炉灶也好久没有粉刷;又冷,又不舒服。
老大娘在黑洞洞的角落里转着身,用嘶哑的声音问道:“是你吗?纳斯嘉?”
“西多罗夫娜,有几个人来找你,他们说是亲戚。”
“决不会的,把他们赶出去。”
她没有商量,就叹着气,转过身去,稻草垫子沙沙地响起来,看来她不是又睡着了,便是昏迷了。
“看见没有?”小姑娘说了。
“还有什么人住在你们这里吗?”没有等到她回答,我便故意大声喊道:“我是费多罗夫,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的这位同志也是游击队员。”
两条赤条条的细腿马上从炉台上放了下来。
“啊,原来是您!”我听到了微弱的嗓音。“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不错,果然是雅可夫·祖谢尔曼,我流浪时的老伙伴。他吃力地从炉台上爬了下来,用瘦长的手臂撑着,勉勉强强爬到了板凳上。他朝灯光坐下。我看到了一个憔悴不堪、胡须长长的老头儿。
事实上雅可夫总共才二十六岁。他长久地喘着气,看来从炉台上到板凳的这几步路使他够累了。他瞧着我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哆哆嗦嗦、断断续续的笑。只是那对大眼睛却显得喜气洋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可夫重说道。“这么说,您还活着哩。我早听人说过,可是不相信。这里有人说,费多罗夫离得不远,但是我病得很重,有时人们走来谈起您,后来我总以为那是我的梦话,而且不相信。”
大概格罗明科和我望着雅可夫,就象违反怜悯心一般望着必死无疑的人一样吧。
“您别以为我快要死了,”雅可夫说。“我已经死过两次,几乎被打死五次,但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快复原了。生的是斑疹伤寒,”他按着说,急急地想尽可能一口气说完。“老大娘和这位小姑娘可真是好心人。我不知道……”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我问。
雅可夫对格罗明科瞅了一眼。
“这位是我们的游击队员,你尽说无妨。”
格罗明科伸手给雅可夫。可是雅可夫没有把自己的手伸给他。
“我身上脏,”他说,“您别碰我。她们没有力气给我洗澡,可是她们这样对我已经了不起了。您要是有时间,坐一坐吧。我不要求您带我走。我欠着这两个人的人情,因为我在她们面前是有罪过的,我很感激她们。”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拿袖子抹掉了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我吃下了巴丘克的信,要不这样不成。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我很抱歉,有罪就该打,可是大概不会打象我这样虚弱的人吧。是的,您要知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是非常英明地叫我不离开您……西蒙年科在哪里呢?”
“他也走了。”
“他会到了妈妈没有?”
“我在她那里做了好几天客。”
“他是个大好人。象我一样,爱妈妈,爱家庭。您看他会牺牲吗?也许不会。也许他还在打仗,在打德国人,您认为怎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我们随身带来了一点儿面粉,一块油脂,一大块糖——这种糖,在卡普拉诺夫的仓库里还剩下半袋了。
雅可夫把这一切财物全放在板凳上,两手微动,嗓音里带着突然的贪谗心说:“我现在可以吃一点儿吗?您要知道,生过斑疹伤寒的人是很谗的……”
他啃着油脂,把纸包着的糖塞给了小姑娘:“纳斯琴加,给你……”他使劲地嚼着说,“大概我一下子不能吃那么多吧。我听到医生劝我忍耐。纳斯嘉,你别拒绝,我知道,所有的孩子都爱吃甜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她能象老大娘那样给孩子们讲打仗的故事。我真想念那些谈话,您大概认为我说的还是梦话吧。您有时间听吗?”
我请求雅可夫,只要是气力够的话,把自己遭遇的一切按着次序说一遍。他马上便开始了。有时侯他转上一口气,嚼着油脂,接着把它放在一边又讲下去。格罗明科说,他要在街上去等我。屋子里空气又闷又腻,好象在设备不好的医院里一样。我也有点不舒服。我向雅可夫提议立刻和我一起动身到营地里去。他摇摇头。
“我恐怕没有这种权利。现在我必须供养和看护这位曾对我这样关心的女主人。您别以为雅可夫不想当游击队员。我力求活命,好为所有居民的苦难和自己的苦难报仇。我已不相信妻儿还活着,不,您别劝我吧。等老大娘复了原,我准上您那儿去。您要注意,我现在还没气力从地上捡起步枪,不用说开枪了。那么,您听吧,如果可能,别走开,这真是个痛苦的故事!”
我在一张跛脚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本来要听听雅可夫的故事。他的罗嗦使我生气,但我懂得这是伤寒病和长期孤独的缘故。
“您以为这里真的没有危险吧,要不,您带了警卫队吗?”雅可夫问道,“为什么再添牺牲者呢?要是您为我牺牲了,那将是我一生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当然不希望您走。事情是这样的:我离开伊琴雅支队时,不知怎的想起了住在科留可夫卡的我老婆的叔叔,伊兹拉利·法因斯坦。他在炼糖厂里当马具工人,常在假期里骑马到尼真来,我们俩便在那里一起大喝烧酒。那时我们是快活的。他身体很强壮,有钢铁般的坚毅精神;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过十月革命,后来还亲自见过萧尔斯,甚至用情报帮助过他。我胡思乱想起来,说不定我的老婆已从尼真到他那儿去了,决不是在尼真被扫荡队抓去的。于是我拐到科留可夫卡去了。农民们告诉我,那边没有德寇,游击队完全控制一切,仿佛连苏维埃政权也组成了。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哪知一切完全相反。实际上,游击队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了。顺便说说,那边不知为什么没有德寇,或者他们害怕立刻进来吧。他们好几个钟头还不出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象在猛烈的暴风雨以前,雷电已经打闪的时候以后。
我上药房去,心里这样想:要是伊兹拉利还在城里的话,药房里一定知道。那边的药剂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药剂师不在。看门的女人对我说:‘快快逃跑吧,犹太人害怕迫害,全都躲在家里。’我问:‘伊兹拉利呢?您大概知道他吧?’看门的女人回绝我说,伊兹拉利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动身上尼真去了。那就是说大家正好走了相仿路。我刚在这么想的时候,机器脚踏车部队已在街上急驶过来。您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还没留胡须,外表看来近乎乌克兰人:小胡子长长了。我记得在尼真是,机器脚踏车部队横冲直撞为的是要强烈的喧嚣和恐惧,却不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停下来。这是安全的时机,于是我便勇敢地回到街上。我想,上哪儿去呢,上伊兹拉利住的那所屋子去吧,它就在医院旁边。您在听着我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还是已经打起盹儿来了。”
“你会累坏的,雅可夫,”我说,“吃吧,别忙。”
他又抹了抹额头,然后嚼了一会儿。西多罗夫娜在屋角里呻吟,小姑娘在炉子里放了几块劈柴,又向我要火柴。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点着了火,双手向它伸去,就那样长久地站在那儿,也不四下望望。
“整个的惨事在这儿,女主人被我传染了,”祖谢尔曼说。“她做好事花了极大的代价。她已五十出头了,现在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对伤寒病来说,最糟的是心里不快活。她可能死。在她那方面这是何等牺牲。您要注意,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预先警告过她,但是老大娘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上帝要带走她的灵魂,那反正是免不了。我本来早就要离开的,可是因为发烧害病,已经不能走动了。”
雅可夫谈了不下一小时工夫,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我不准备把他的全部引用过来,故事的继续部分是这样的:
德寇在第二天就挂出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集合地点去,随身带着全部财物。德寇已经大批开到。要逃出镇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药房看门人的妹妹在医院里当保姆。她和别兹罗德内医师说妥以后,就把祖谢尔曼放到病床上去,那时他还是完全健康的。
可是事情却这么发生了,当天晚上,德寇决定来视察医院,为的是要把它改成陆军医院。他们把守门人推在一边,径自走进病房来。
祖谢尔曼听见他们在隔壁病房里这么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什么民族?”
逃走已经不可能了。窗户朝街,房门通走廊,而德寇就在走廊上。就在这儿他把巴丘克的信吃掉了。
“我已经完全同生命告别了,因为我知道投案登记意味着什么。为了要记住巴丘克写给您的信,我很快地把他的信过目了一遍,然后急忙把它嚼烂了咽下去。我尽打噎,但德寇没有听到。这时候药房看门女人的那个亲戚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保姆。她们带着一副担架,并且低声对我说:‘躺下吧,病人,你现在是死人啦!’我躺了上去。她们拿被单把我盖上,从德寇和伪警身旁抬过。我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妇人象说家常话一般很镇静地回答:‘害伤寒病死的。’有个伪警把被单揭了一下。我大概苍白得好似尸体,因为他漠不关心地说了声:‘啊……’,于是我便给抬进了院子。但是那里也有兵士,妇人们把握抬进了停尸室,抛在板台上。那里躺着三具尸体。因为有些人实在是生伤寒病死的,特别是那些脱逃的俘虏里头的。我躺着,躲在死人中间,可是比他们更难受。我那么躺了一个多钟点。从这时候起,在九昼夜之内,德国人一走近医院,我便飞奔到停尸室去,躺在那些可怕的伙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