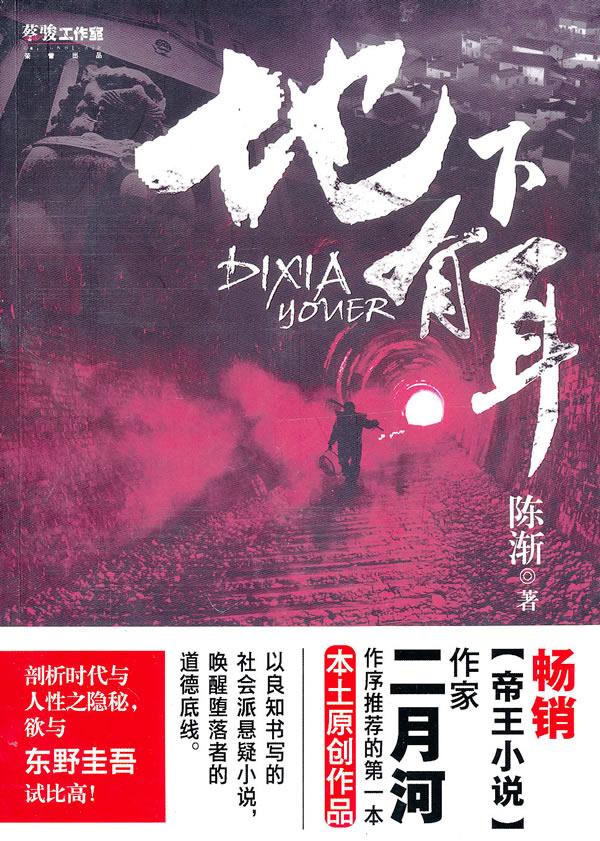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柯伏顿已经上了年纪,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签名参加了游击队,早在沦陷以前就到森林里来了。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格利沙和他一块儿当了游击队员。爷儿俩被编进了彼列柳勃支队。
柯夫顿是个沉默寡言、体格强健的人,他自称是军人,而一举一动也象个有经验的老兵:他不大参加谈话,也不惹指挥员的注目,但一定完成一切任务;哪怕是削马铃薯、砍树、给地下室挖个坑,或是去摸一条“舌头”,都同样干得很好。
在这次战斗中,柯伏顿奉命去悄悄地除掉司令部门前的哨兵。他爬过去,发现是个双岗:两个德国兵正站在房子的两角。柯伏敦等待着信号。当火箭在波戈列察上空升起时,他就扑向最近的的一个哨兵。可是那个人还是来得及开了一枪,子弹击碎了挂在柯伏敦胸前的望远镜。这一枪并没有使他住手。他跟这个德国兵扭成一团。他们俩翻倒在地,德国兵压在他身上。另一个哨兵在旁边直跳,不敢开枪。后来柯伏敦自己说,他是为了不让另一个德国兵开枪,才有意让那一个压在自己身上的。
游击队员们跑近时,柯伏敦立刻把德国兵摔开,跳起来,用足平生之力拿枪托给他当头一击。枪托裂成了碎片。
另一个哨兵开了几枪,把柯伏敦的军大衣打穿了两处。柯伏敦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去,拿刺刀把他刺死了。
这时,格利沙赶到了。
“没有受伤吧,爸爸?”他焦急地问。
“没有受伤,孩子,没有受伤。”柯伏敦答道,同时从哨兵僵硬的手指中拔出了步枪,又冲进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游击队员们在作战以后,整天谈着这一次的决斗。可是柯伏敦本人总是保持沉默,只是当人家纠缠着非要他说不可的时候,才给予严正而确实的答话。
“阿尔先齐依伯伯,那个躺在您身上的德国人重不重?”
“他不是躺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身上打着滚。”
“是个身体结实的家伙吧?”
“结实不结实倒没有关系。只是他嘴里那股酒味太大了。他灌足连甜酒。舌头跟那种狗舌头似地伸了出来,又嗳气,又打噎——简直不知有多少……”
“您怎么会把枪托砸碎的呢?难道说它的脑袋那么坚硬吗?”
“要知道他戴了顶钢盔啊。而且他脑袋也确实重。再说,我用的是一支波兰步枪。质量不那么好……”
我们离开波戈列察大约十五公里时,天色已经大亮,听到那边又有射击。先是迫击炮、机枪,后来是大炮;有十发炮弹爆炸了。
侦察员走来报告道:“德国人在打德国人。增援波戈列察卫戌队的部队从谢明诺夫卡开来了,留在波戈列察的德寇认为又是游击队,开了火。谢明诺夫卡的德寇也揣度着,以为游击队在村子里巩固了阵地,开始用大炮轰他们。他们打了半个钟点。”
“让他们永远这样打下去吧!”我们的英雄柯伏敦说。
从此以后这句话就这样传开了。如果我们使德国人打德国人,匈牙利人打德国人或者波兰人成功了,大家便说:“让他们永远这样打下去吧!”
我们回到了那座森林,是省支队在波戈列察战斗以前在那儿驻扎过的。这里,从前住过一百个人,现在却住了三百多人:所有的分队再加上波戈列察补充队。天气极冷,经常吹来冰冷的劲风。冬季不过才开始,还有更厉害的严寒在前面,而且粮食的情况愈来愈糟,存粮快要完了。”
但是人们好象已经暗中替换过了。他们变得更守纪律、更能工作,能够迅速而乐意地执行一切命令。要是你晚上打篝火边走过,你会看到,弟兄们总是在研究德国的步枪、自动枪和机枪,掌握敌人的技术。
“同志们,干得对!在最近的将来,谁也不会给我们武器。克里伏达战士,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谁是乌克兰游击队的主要供给者?”
克里伏达站起来敬了个礼说:“希特勒!”
“停住,克里伏达战士!你还没有搞清对象。小孩子①,您怎么说?”
【 ①小孩子的俄语发音是马尔奇克,与下面所提的侦察兵马拉赫的姓同音。此处是一字双关。】
侦察兵马拉赫·马尔奇克实际上已是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他在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从前做过看林人、木匠,灵巧、敏捷、能干,是个万能博士。他和两个成年的儿子、一个女儿和女婿一起加入了游击队,他现在当侦察兵,在森林里就象在家里一样。任何村子里都有他的朋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轻轻笑了一声答道,“我们的主要供给者是游击队的勇敢。”
“不是,”谢明·吉洪诺夫斯基打断了他的话,谢明是个酷爱和捏造神话的人。“游击队的主要供给者将是信心。你要是相信胜利,你就会获得胜利,达到胜利,而且战后还能活上一百岁。”
“你瞧,有这么个自信的人!”
“噢,那当然!你听到过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关于包围的辩论吗?”
“说吧,谢明·米哈依洛维奇!”
吉洪诺夫斯纪无需人家再请求了。
“噢,一个德国人碰见了一名游击队员。德国人说:‘缴枪吧,我快要围歼你了。’可是游击队员回答说:‘你是只愚蠢的鹦鹉,不是别的。当你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而且再也没有地方躲的时候,你怎能包围我呢?’德国人放声笑了:‘哈哈哈。’但自己向四下望望说:‘我要到达乌拉尔,元首在领导着我。’但他又向四下望望。游击队员又说道:‘要是你老是转动着脑袋,眼睛尽往后瞧,那你怎能包围我们,怎能获得胜利呢?而且也不向四下瞧也不行,因为人们的眼睛打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那些眼睛里闪着愤怒和你的死亡。’德国人嚎叫起来了:‘闭嘴,要不我就打死你!’但他坚持不住,又向四下看了一眼。这时候游击队员便把他打倒了。”
我就这样从这堆篝火到那堆篝火地走了一个黄昏,听着游击队员们的谈话,瞅着四周。怎么一切都变了样啦!不过在两天以前,人们还是垂头丧气、沉默寡言的,而且一抬眼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往后怎么样?”
真是奇事,现在连树林也不是那么样了。看起来树林也漂亮了。晚上,在篝火的亮光下,简直是一幅壮丽的、甚至可以说是庄严的风景画。空气是清新的,大家的脸蛋是菲红的,到处是笑声、嘈杂声、喧哗声。有人在雪地里摔角,有人在开始唱歌。蒸汽在锅子上腾起,晚饭快要烧好了。
我走到篝火边,挨近它坐着的是些年青的切尔尼多夫本地人,大部分是工人弟兄。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便等候着不做声了。
“怎么啦,小伙子们,你们累了吗?在战斗中和行军中吃了苦吧?”
“不,费多罗夫同志,我们很好。只是缺少音乐,我们需要一支游击队自己的歌子。”
“那有什么,你们自己着手编吧。难道我们要等莫斯科给我们派一位诗人来吗?”
“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我们自己也会努力的。我们想得出来。司令员同志,我们一定会写出来的!”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一个体格强壮、面色红润、头发英武地卷在帽边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在这儿争辩呢,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吧!”
有些人微微一笑。有些人忍不住,哧哧笑出声来。
“你住口吧,尼古拉依……”
“给他堵上嘴……”
“不,”体格强壮的小伙子继续说,“我来说。我认为和司令员,特别是和党的领导人,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商量商量的。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在战斗时……”
一个十九岁上下、穿着铁路员工的长大衣的小伙子跳起身来了,深深地吸了口气,看样子想要讲些什么,但是他的脸胀得通红,委屈地眨着眼睛;他把手一摇,便跑进森林里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费多罗夫同志,您看到了这位游击队员吧?他正就是这位朋友。他在波戈列察作战时,躲在大木头后面,把菜园里的稻草人射击了一刻钟光景。”大伙儿又笑起来了。“的确,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不撒谎。人家都在射击敌人,他却在浪费着子弹。直到子弹把木棍打断,那个稻草人倒在雪地里,他才放了心。”
穿着铁路员工的大衣的小伙子看样子已能自持了,从树林里走了出来,走到体格强壮的小伙子面前,把拳头在他脸前一扬。
“你别以为是了那么大的个子就什么都行了,”他热烈地叫道。“尼古拉依,我永远不会饶你的……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听我解释。现在对我反正一样了……我是个近视眼……但我在机车库是做钳工的,能够干得了。”
体格强壮的小伙子笑得噎住了,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说:“问题就在这里,你在那里是戴着眼睛工作的。老实说,你是用欺骗手段来当游击队员的。军队里不收留你,你本来应该撤退到后方去。你在那里才适宜。要不,他一定看过许多关于游击队的书。真是‘马蹄到哪里,虾螯也到哪里!’②”
【 ②俄罗斯成语,意即“太不自量”】
“别扯了,问题不在书上。如果您想要知道……费多罗夫同志,我父亲在前线牺牲了,妹妹在轰炸时成了残废……费多罗夫同志,这一切他全都知道,他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现在倒嘲笑起我来了。我认为,这种行为不是共青团员的行为!”
“那么你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我问钳工道。“你要是戴着眼镜,大概会射击得好一些吧?”
“我在学骑马的时候把眼镜打碎了。您以为,免役的人只有我一个吗?您认识乐器工厂里的那个小个子丹尼尔吗?他从小就有结核病,在一年前才停止打空气针。他在波戈列察打死了一个德国上等兵,可能还打伤了两个。您问问他看,他现在在森林里比在城市里觉得好些了。还有一个,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共青团员,而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生着胃溃疡,也是个免役的人。我们都是志愿申请参加的,没有被收留……但是我能打仗,老实话。”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在大家的嘻笑之下掏出了三副眼镜。“这是我昨天从德寇头上卸下来的,但是都不合用。我是八级。”
“不要紧,”我安慰着小伙子,“你早晚会捡到需要的号头的。尼古拉依,你帮帮他的忙,在下一次的战斗中,你一定要打死一个戴着合式的眼镜的德寇。在这种条件下让我来把你们说和了吧。也许会好一些……你叫什么名字?……阿历克山达尔·贝契科夫。那么,萨沙,也许你撤退到后方去要好一些,但是现在谈这件事已经晚了。战斗吧!”
比沙拉勃走到跟前来了。看样子,他听到了谈话的尾声。
“我们,啊哼,有个老头儿,一下子戴了两副眼镜。”他说。
贝契科夫把德寇的一副眼镜加在另一副眼镜上。这时他活象一只虾。连我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贝契科夫再也不生气了。他和大家一起大笑,并且高兴地说:“能看啦!看得很清楚!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一定要成为神枪手!”
比沙拉勃挽着我的手引到一边去。
“老乡们,啊哼--呃,情绪好极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比沙拉勃若有所思地捻着胡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认为这个现象应该用我们团结和共同努力来打击敌人这一情况来解释……”
“这么说,我们团结是没有错吧?”
但是比沙拉勃还不见风使舵,就此结束。他是个极端自负的人。在现阶段上,他认为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他想要把这个承认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我。
“劳动能使人振奋起来。现在我们劳动过了。我认为,这就是战士们的情绪到了水平以上的原因。”
“这就是说,我们团结是对的喽?”
“时机选得正确。在这个时候本来应当,啊哼,用共同的力量来活动的。明白吗?”
我和比沙拉勃的谈话到这里便停止了。他直到现在心里依然固执地抱定以前自己的见解。但是事实如此明显,成绩这样惊人,比沙拉勃暂时退却了。
波戈列察战役以后,我们立刻认为主要的成就是士气的普遍提高。游击队员们开始尊重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了。现在我们不时听人谈起更勇敢、更大规模的袭击的必要性。但我们的成就比预料的广泛得多,重大的多。
我们是从自己的森林游击队的立场来估计这个战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