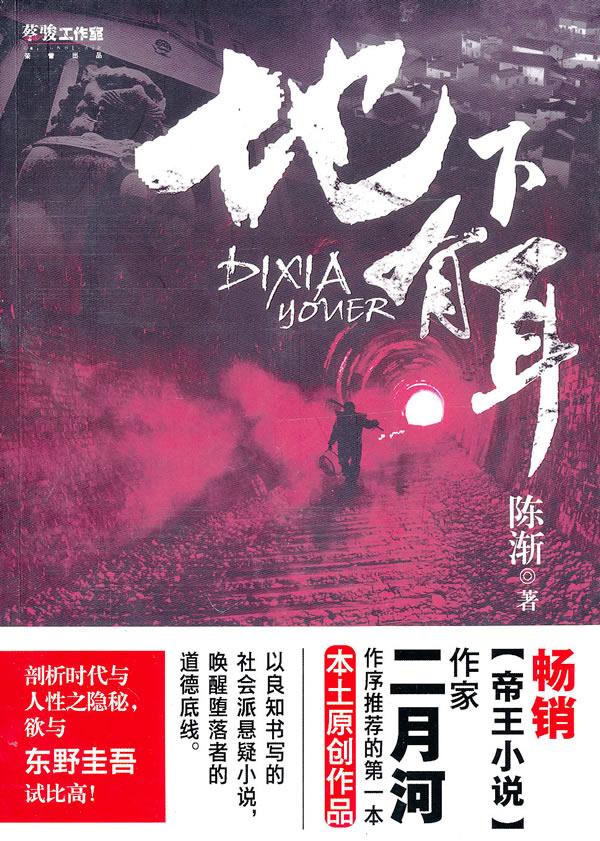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当作是乌克兰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你所谓‘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什么。”他支吾地回答,并且掩着嘴假装打呵欠。
“不,请您说下去。既然你开了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来说吧。”
这时,那个曾经问提美国问题的外貌阴郁的农民,看来年龄跟这个人相仿,转过身去恶狠狠地叫道:“说呀,说呀,你坦白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干么掩饰?”
老家伙没有不好意思。他眯着眼时而瞅瞅我,时而瞅瞅那个同年人,时而又转向全体到会的人,慢吞吞地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看法。整个乌克兰落到德国人手里没有?全丢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想起党呢?你们放弃了乌克兰,就继续逃跑吧。我们自己来对付德国人,否则……”
“……就妥协!”老汉接着喊了一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高兴妥协。瞧,好一个爱国分子。他在替整个乌克兰说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犹大血统的东西:你想的不是乌克兰而是钱。你打从年青时起就想做富农。现在还是想做。你需要的是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和十几个雇农。但是你却谈乌克兰……”他突然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你别老是触我的腰眼,我不怕他。要是他来反对集体农庄,投到德寇那边去,那我们就赶快把他吊死在树枝上。”
“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掉了……因为有月亮,地上很亮,我们看到在德寇中间……好象有个支队里的小伙子和他们在一起……”
“谁,你照直说!”
“你们是怎样想?”
“你别做迷语啦!”
尤尔琴科说得转弯抹角并不是为了玩儿。正象我们一样,他也希望看错了才好。在过去所信托的人们中,竟会有人投靠敌人,听到这种消息实在令人厌恶。
但是尤尔琴科说出这个人的姓时,我们已经不怀疑了。知道了这个姓我也可以对他指出那个人是谁了。
那是夏德林诺村的小学教员伊萨先科。
尤尔琴科解说,弟兄们注意到一条围巾,看出这条围巾是伊萨先科从前围过的,他围的样子有些特别。
“去吧,”我命令道。“你去吧,可是不要声张。对谁都一字不提。”
早在几天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战士伊萨先科时常到夏德林诺去看他父亲。当然他请假的理由是说他父亲有病,需要照料,但是后来我们接到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说这位小学教员的父亲享受德寇和伪警的小恩小惠:伪村长把充公来的集体农庄的家畜给了他一头公牛和两头绵羊。
我当时就把这个儿子给叫来了。我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有罪。他是个年约三十的瘦子,嗓音动听,行动迟疑;但是应不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断定一个人呢。他夸大其词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老实话……我现在向您解说,假如有谁不谅解我,我相信您大概一定会谅解我的。您要知道,司令员同志,我爸爸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说,他是个互相残杀的反对者……他对任何人都是软弱到蠢头蠢脑。他简直是客气地接待德国人,可能客气得过分了。您了解的,军官们就喜欢这一套。他们给他酬劳,爸爸不敢拒绝。他现在竭力想把那头公牛转交给您,那就是说,对咱们、对游击队有利……”
“听着,您毕竟是小学教员,应该了解您‘爸爸’的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你不利。放手吧。停止吧!”
“请允许我说,司令员同志,说实话,我一切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是想促使爸爸参加地下工作。他是个爱国者,我可以发誓。您不是不知道,有些神甫也……我甚至相信,他外表的低首下心应该被运用来做情报工作,您以为怎样?”
伊萨先科的话是说得通的。他在支队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怎么办呢?噢,他引不起我的同情,他的声音、面貌也不使我喜欢。这究竟不是犯罪的证据。但我还是警告他说:“注意,你一定得停止时常离开营地。别去打扰你信教的‘爸爸’。我们不需要他效劳。”
伊萨先科被我们监视了,一连好几天,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瞧,他又犯老毛病了……
现在我们全都断定他不会回到营地里来了。但一小时以后有人报告说:伊萨先科出现了,甚至还是围着那条围巾。想来,他也许以为人家不认得自己吧。但是最可能还是德寇强派他来的:德寇不需要食客。当然,他立刻被带到司令部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得知父亲快死了,跑去看他……”
很适当的谎话。这也可以说明自己的焦虑不安。伊萨先科已经脸色发白。
“那么你有无线电联络还是怎么的?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你胡诌下去吧。”
“我的小妹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所以……我在父亲的床边耽搁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不守纪律,应该事先得到指挥员的准许。不过那次跟您谈过话之后,我怕他们不放我去。我应当受处分,我懂得这一点,向您说老实话,我……亲情是不适宜的,当……”
“你是单身回来的吗?”
“什么?”伊萨先科刹那间打量了一下地下室。
窗口是很小的,门口站着波布特连科和诺维科夫。
“你这个混蛋,有人看见你和一群德寇在一起。”波布特连科沉不住气了。“你把他们带到营地来是不是,你说,带了没有?”
“不,老实话,我……”
“有八个人认出是你……坦白说吧!”
“我说,当然,我说……是一些德国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带路,而是他们在给我们带路……请相信我。我决不撒谎……在我回来时,他们把我捉住了……”
“那么您后来设法脱逃了吗?”我问。
“是的,接着我便逃跑了,”他赶快符合着说。“我乘混乱的机会溜走了……”
诺维科夫突然抓住他鼓起的口袋,从那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那么这个玩意儿是德寇留给你做纪念的吗?嘿,你……快把一切真情实话说出来!马上就说!”
伊萨先科啪地跪了下来。
半小时以后,我下了一道命令:把伊萨先科在队伍面前枪决。这是我头一次枪决奸细的命令。
诺维科夫开始劝我:“干么在队伍勉强执行呢?这会使人们产生沉痛的印象。”
“照您说,就象巴拉贝那样做吗?”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三天,彼列柳勃支队里也揭发了一个和敌人有联系的新队员,也同样被判处了枪决;但是他们没有敢公开执行。当这个叛徒在地下室里睡着时,他们对着他耳朵开了一枪把他结果了。不待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彼列柳勃支队里就有了很多荒谬绝伦的谈话。他们向人们宣布的是:某某人由于叛变行为而被枪决了。但是人们要求公开宣判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