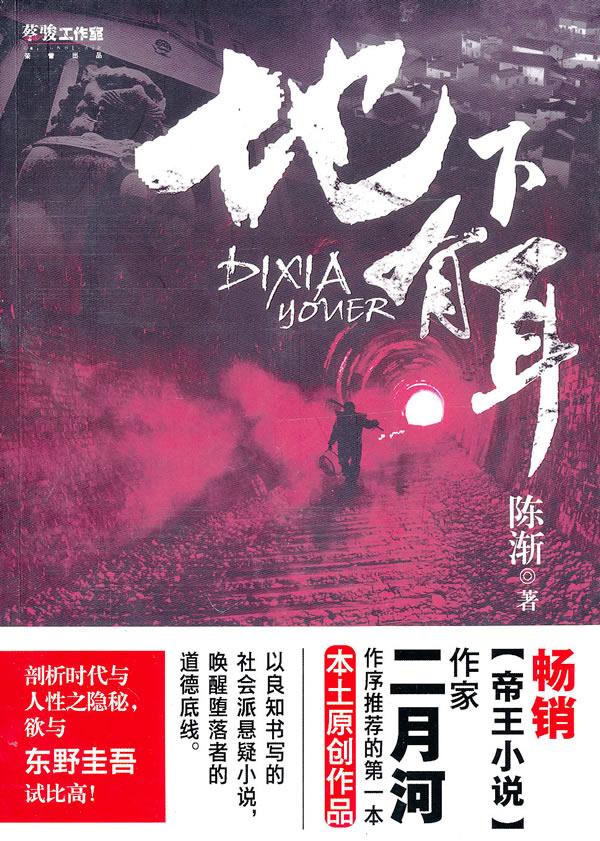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0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铁道附近到处出现了严厉的告白:“禁地!违者枪决!”士兵们因为在禁区里抓到人,开始获得奖金和休假。
护路队每隔五公里建立了由这一条铁路到另一条铁路的转辙器。在路基旁边建了一个个土木碉堡,挖了一条条堑壕。占领者们开始在附近的村庄里收集狗,把它们拴在钉在路基上的木栓上。当军车驶近时,从未见过机车的乡下狗,都挣断了锁链,嚇得发狂了。有时侯,狼在夜里来袭击拴着的狗。这些狗几乎不断地在哀吠尖叫。
当铁路上出现了受过嗅炸药的训练的军用犬时,游击队员们就开始在通埋设地雷的进路上撒下一些鼻烟——揉碎了的黄花烟。但是黄花烟我们自己也不够抽的,不久我们找到了另一种方法来和这些军用犬作斗争:开始在远离埋设地雷的地方撒下和埋上极小的炸药块。军用犬从这边跑到那边,用爪子扒着什么也没有埋的路基。狂怒的士兵拿皮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良种狗。他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炸药是黄色的,它的小块儿在沙子里肉眼是看不见的。
德国的铁道工作人员在机车前面挂上一辆或者几辆装着石头或沙子的敞车。可是地雷不在敞车下面而在机车底下爆炸。为了这个成果,我们的同志们实行计算钢轨的弯曲度。敌人看到运送石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就把这个计谋放弃了,开始放出一列特别的压道车:机车或轨行摩托车和一节车厢,它后面拖着一些链条,在路基的沙土上留下了一条条小槽。这是为了使巡逻队在这种小槽上发现了中断以后就采取措施。但是,一则,这些链条的痕迹只能在干燥的、没有风的天气留下来(雨水把这种小槽冲掉了,风把它刮平了),再则,这种‘发明’给护路队带来了很多麻烦,游击队员们从左右两边把小槽挖开和填平了大约二十多处——试试在这儿分辨一下吧,地雷在哪里!
德寇又尝试用白粉染在铁路道渣的上层,但是这也无济于事:游击队员们储备了调好了染料的小桶子。
在靠近特罗扬诺夫卡车站的科维里-萨尔尼铁道线上,护路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黑夜开始时,在每三百公尺的路线上派定一个由当地居民中征用来的人。每一个人发给一根小铁棍,命令他们每十分钟敲一次路轨。如果这种敲轨人发现任何形迹可疑的人,就应该敲两下。其余的人也敲两下,于是这种加倍的敲轨声就会传到附近的护路队的确岗棚上。从那里立刻开出铁甲车,并且一起开来了警卫队。这时我们的爆破队指挥员奉命同时在四、五个地方悄悄地拿下几个敲轨人,又在两个解放了的区段里埋设地雷,在其他的区段里挖掘几个假坑,给敌人的巡逻队一些意外的礼品。
在我们拿下了四十个敲轨人,并且有几个巡逻队员在意外礼品上被炸死以后,敌人就放弃了这种护路的方法了。
在布列斯特-平斯克和布列斯特-科维里的铁道线上,护路队企图偷偷地顺着路基打埋伏。从前护路的连队顺着枕木徒步走来,在每一区段上分出一小队。口令喊得很响,我们照例知道所有的‘据点’。现在黄昏一到,就用火车分送着兵士,迫使他们在火车行进时成群结队地跳下。这样的小队,通常是十一、二个人,从几节车厢里一下子跳下,立刻就埋伏在灌木从里。但是侵略者没有估计到,士兵跳下火车就惊呆了,况且是在黑暗里,可能轻易地变成游击队的俘获物。我们的埋伏对跳车的德寇的埋伏给予有利的措施到这种地步,使有些爆破队给它吸引到有损于敷雷工作。事实上,抓住和解除几个护路队队员的武装完全是有利可图的事:每个人都有一支冲锋枪,至少也有步枪、手榴弹和子弹。我们的司令部已经准备下令防止过分迷惑于这样的行猎。但是德寇自己也懂得停止给我们运送大批的‘舌头’和武器。
我们的爆破手们的工作毕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我们的科维里战役的第二个月里,顺着铁道路基已经乱抛着大批翻倒的车厢和机车。正是在这些军车的残骸里,侵略者开始藏匿了一队队反游击队的护路队。
我们不容易在那里发现他们,就是发现了,把他们从那里打出来也不是简单事,特别是此后侵略者把铁道沿线的森林都砍倒,把灌木丛烧掉,并且建了许多炮楼:中间放着砂子的双层木板墙的高高的建筑物。在这种炮楼里装置了强有力的、光线能达几百公尺的探照灯,还装备着机枪和迫击炮……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最新的地雷技术,而且很少人会施用炸药,那些去从事爆破工作的人,大家都认为是一些不顾死活的小伙子。在那个时候,我们专用导火线和撞针的地雷来爆炸列车。敷雷手在已经看到火车时才埋设地雷,并且把地雷埋设得愈晚,胜利就越有保证。因为火车司机看到有人在轨道上,立刻就可以刹车。为了使刹车也无效,不得不让火车开得近些。
我们的爆破手们以得到不顾死活的小伙子的称号而自豪,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和毫发无损而志得意满。他们表示着独树一帜。那时我们这里的爆破手们都被派定在一个特别分队里。领导爆破战的人,都是些特别勇敢的人,就象巴利茨基、克拉夫琴科、阿尔托泽耶夫这些人。
我不知道现在的苏联英雄乔治·阿尔托泽耶夫哪怕在战争末期,有没有稍稍节制自己的鲁莽轻率,避免过分消耗炸药。他在小桥脚下一面放上一箱炸药,总共跑过去十来公尺就躺下,说是这样更安全。
“铁梁、栏杆、木板都从我上面飞过,甚至连沙子都落在我的那边。”
“卓拉,”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仰面躺下呢?按照指示应该伏着的呀。要是有什么东西偶然落在眼睛里,或是烫了你怎么办呢!”
“写在指示里的东西多着呢!可是我有兴趣瞧瞧。反正我的工作是这样!只有胆小鬼才不冒险!”
老实说,起初指挥部,连我也在内,对这样的鲁莽轻率都是视若无睹的。而且许多爆破手开始不仅在战斗的环境中拿鲁莽轻率来出风头。
在沃雷尼河上,我们绝对禁止在河里用爆炸筒摧残鱼类,违反者有受严厉处分的危险。但是在乌博尔齐河上,还是有游击队员常常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打鱼。他们用带着短短导火线的爆炸筒来摧残鱼类,大家还认为是最漂亮体面的。导火线很短,短得爆炸筒还没到水底就发生爆炸,而更出色是在水面上爆炸。
这种事情往往因爆炸筒在一个鲁莽轻率冒失鬼的手里爆炸,使他受了重伤而收场。
爆破手们还有其他方式的鲁莽轻率的事件。
有个男高音而且很讨人喜欢的分队指挥员斯列普科夫在追求年青的女炊事员波利亚。他用自己的嗓子引诱了她好多时候,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在好朋友中间自夸说,这天夜里他要钻进波利亚的帐篷里去了。那时,富有发明能力而机警灵巧的爆破手米沙·格拉佐克,便决定教训一下这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半夜两点钟光景,整个营地上的人都被距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发生的爆炸声所惊醒了。人们都跑上了林中空地。斯列普科夫在草地上东奔西窜,晃着拳头,嘴里不知道在叫喊些什么。嚇得胆战心惊的波利亚就站在那里。而米沙·格拉佐克和同志们却笑破了肚皮。
原来,米沙在松树顶上挂了一个七十五公分的钻孔用的爆炸筒,从它上面拉一根铁丝到树根上,随后拉到波利亚的帐篷的出口。小队长正想钻进波利亚那里去,一只脚挂住了铁丝,把它一拉,炸药就爆炸了。
在耶戈罗夫来到联队以前,我们的爆破手们对待炸药是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地存放它,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纵队行进时切开、分配、包装进箱子。雷管是装在口袋里的。如果爆破手坐在装着炸药的马车上,而他口袋里卡嗒卡嗒地响——一只口袋里是雷管,而另一只口袋里是弹筒帽,从来也没有人觉得惊奇。这种情形也被看成了潇洒。
当耶戈罗夫开始同输送爆炸物条例的破坏和违反者进行斗争时,他曾听到了不少意见:
“别怕,官长,我们的人都习惯了!”
“嗳,耶戈罗夫同志,你无缘无故地大叫大嚷干什么呀?你要是和我们一样打过那么久的仗,就会更平静地对待这件事了!”
有一次,耶戈罗夫向我控告帕伏罗夫。
帕伏罗夫当时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爆破手,他奉令去接收空运辎重——炸药和信管,我们还派了两名爆破手——穆斯塔菲和古勃金——去帮助它。当时掷给我们的重要是装在一些麻袋里的。在炸药块中间塞了大量的皱纸。而在装雷管的袋里塞得尤其多。于是帕伏罗夫和他的助手们把装着炸药的袋子都拖集在一个地方,挖了个坑,把所有的炸药都堆在那里。那次送来给他的炸药不少,有好几百公斤;他们把雷管和引信带到一边,然后把所有的纸集成一堆来付之一炬。干完了吃重的工作以后,他们站在那里休息,在篝火边取暖。耶戈罗夫朝火光奔来了:“你们在干什么?马上熄火,堆着炸药的弹抗敞开着呢。”
“别担心,我们知道!这又不是第一次,”帕伏罗夫神气十足地答道。“会出什么事故呢?”
“能出的事故多着呢。雷管突然爆炸了怎么办!”
“雷管怎能到这里来呀!”
帕伏罗夫刚说完这句话,篝火里有什么东西放了炮。后来一个接着一个地炸开了。这时小伙子们着了慌,急忙动手泥土盖灭了篝火。这才没有出事!不然,这里会闹出骇人听闻的灾祸哩:因为离开这几个坑不远还有两个放着炸药的坑,总共有五吨来重。要是一个坑里炸开了,其他的一些坑里也会由于雷管爆发而爆炸的。
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来根除鲁莽轻率和漠不关心。应该承认,我们直到末了也没有能够克服得了这种严重的罪过。
有一次,我听克拉夫琴科给新补充的爆破手们上课。
“你们瞧,这根患燃导火线是这样来接起雷管体的!”克拉夫琴科用平时一样平和的声音对自己的学员们解释。“插进了导火线,然后夹紧……”说着这句话,他就用牙齿咬了咬铝制的雷管壳,然后给年青的游击队员们看。“往下传过去。同志们,仔细地看一看。但要注意:如果你们再压缩半公分,或者是过分使劲,那末雷管就会爆炸的。在这种情况下,下鄂骨会炸掉……”
我提醒了克拉夫琴科,有专门夹雷管的工具,式样象平口钳。
“将军同志,我们整个支队只有一把呀。”
“真的吗!我要告诉耶戈罗夫,要他找一下,给每人都发一把。”
“别费心了,将军同志,所有的钳子都已一扫而空了,我早已问过……”
“可以给莫斯科打个电报,头一架飞机就会送来。”
“当然可以,不过……”
“噢,说吧,你为什么不说完呢?”
“他们用不着这些钳子,将军同志。过去小伙子们有的早已给扔掉了。不方便,放在口袋里太重了。并且,您要知道,这是传统。一开始就是用牙齿来咬紧的……”
“但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冒险吗?”
“费多罗夫同志,您可别这么说。爆破手们从头一天起就应该学习克服恐惧心。我是这样看法的。”
我终究给莫斯科打了个无线电报,请求给我们寄一些夹钳来,他们给送来了;但是我们的爆破手们只有在冬季严寒开始时才使用这些钳子,因为这时金属管含在嘴里挺不舒服:要冻上嘴……
我们跟任何形式的鲁莽轻率进行斗争,即使它是由于高尚的动机而激起的。
克拉夫琴科的老朋友和助手邦达连科,是不久以前同他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已经有不少的敷雷经验。
克拉夫琴科委托他进行训练年青的爆破手。在训练的过程中,本来应该把新型的定时地雷介绍给他们。但是邦达连科虽然在飞往莫斯科去以前炸毁过几列军车,这种地雷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他同巴利茨基一起去进行破坏工作时,关于这种地雷我们还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由于进行爆破工作而受过奖的游击队员,要在青年们面前承认自己不懂得这种地雷,邦达连科是办不到的。
他借口病体恶化,对大家说,为了使神经镇定起见,他必须单独地过几天。
邦达连科把自己的帐篷安设在离营地半公里的枞树林里。他真的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四天。
而回来以后,向克拉夫琴科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