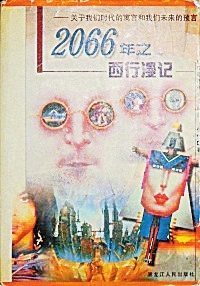66计算中的上帝 作者:[加] 罗伯特·j·索耶-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太奇妙了。”我说,“一个完全的外星生态系统。”
“我刚来地球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见识过其他生态系统,但是,没有比接触一类全新的生命形式并了解它们如何互动更令人兴奋的事了。”他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的世界在七千万地球年以前的样子。当下一次物种灭绝发生时,整个五肢类动物都消失了。”
我看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五肢类正在攻击一个体形稍小的八肢类。它流出的每滴血都像地球动物身上的一样红。垂死的生物惨叫着,虽然惨叫声是从两张嘴里交替发出的立体声,但是听上去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不愿死去看起来是另一个宇宙常数。
《计算中的上帝》作者:罗伯特·J·索耶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七章
我还记得去年十月从纳古奇医生那儿得知初诊结果后我怎样回的家。我把汽车停在车道边。苏珊已经到家了。在我为数不多开车去上班的日子,我俩中先回到家的会把门廊的灯打开,以此告诉对方已经有一辆车停在车库里了。为了去远在费曲滩的纳古奇医生的办公室拿检查结果,我今天开车上班了。
我下了车。风刮着落叶飞过我们的车道和草坪。我打开前门走进屋子。我能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Faith Hill的《这个吻》。我比平常到家要晚,苏珊正在厨房里忙着——我能听到锅碗瓢盆的轻碰声。我仿佛脚踩着棉花,走过铺着硬木的门厅,来到客厅。我通常会在小书房停一下,看看我的邮件——如果苏珊比我先到家,她会把我的邮件放在小书房门内矮柜的顶上——但今天我脑子里已经装了太多东西了。
苏珊从厨房出来给我一个吻。
她太了解我了——过了这么多年,她怎么会不呢?
“出了什么事吗?”她说。
“里奇在哪儿?”我问。我必须也得告诉他,但先跟苏珊说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些。
“在胡家。”胡家是我们隔着两个门的邻居,他们的儿子鲍比和里奇一样大。“出了什么事?”
我扶着楼梯的栏杆,感到自己仍处于初诊后的震惊中。我示意她和我一块儿坐到沙发上。“苏,”坐下来之后我说,“我今天去见了纳古奇医生。”
她看着我的眼睛,试图从里面读到点信息。“为什么?”
“我的咳嗽。我上星期去过一次,他做了些检查。他让我今天去拿结果。”我在沙发上向她靠了靠,“我什么也没问就去了,看起来不过是常规检查——没什么好问的。”
她扬起了眉毛,一脸关切。“然后?”
我寻找着她的手.抓住了它。她的手在颤抖。我吸了口气,充满我的烂肺。“我长癌了,”我说,“肺癌。”
她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我的上帝,”她说,全身不停哆嗦着,“现在……现在该怎么办?”
我微耸了一下肩。“更多的检查。现在的诊断是根据我的痰得出的,但他们要做切片和其他一些检查来确定……确定癌细胞扩散的程度。”
“怎么会这样?”她颤抖地说。
“我怎么得的?”我耸了一下肩,“纳古奇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吸入矿物粉尘。”
“上帝,”苏珊喃喃着,全身晃个不停,“我的上帝。”
唐纳德·陈在麦克拉夫林天文馆关闭前已经在那儿工作十年了,但和他的同事不同,他没有被解雇。他被内部调整到博物馆的教育项目部,但由于博物馆缺乏天文学方面的永久设备,所以唐整天都没什么事干——尽管每次流星出现,电视台都会采访这位中国裔加拿大人,让他的笑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博物馆所有的职员都称陈为“活死人”,因为一:他可怕的苍白的肤色——天文学家的职业病;二:看起来迟早他也会被博物馆辞退。
虽然博物馆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对霍勒斯感兴趣,但唐纳德·陈的兴趣显得尤其大。事实上,他对一个外星人不去找天文学家而去见什么古生物学家有一肚子怨气。陈原来的办公室在天文馆,他的新办公室在医药中心,也就比竖着的棺材稍大一点——但他总能找到理由与我和霍勒斯套近乎,我己经习惯听到他的敲门声了。
这次霍勒斯替我打开了门。他现在对付门很在行,还学会了用一只脚去拧门把手,这样他就不必每次都转动身体了。就在门外的椅子上坐着的是拳击手——那是埃尔·布鲁斯特的绰号。自从霍勒斯来了之后,这位笨重的保安现在全天供职于古生物学部。在他旁边站着的是唐纳德·陈。
“Nihaoma?”霍勒斯对陈说。我曾幸运地在二十年前参与了一个加拿大—中国的联合恐龙项目,因而我的普通话的水平还可以,所以我不反对霍勒斯说中文。
“Hao。”陈说。他溜进我的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没忘了冲拳击手点了一下头。他换成了英语说:“你好,杀手。”
“杀手?”霍勒斯说,他看了看陈,又看了看我。
我咳嗽了一阵。“我的绰号。”
陈转向霍勒斯。“汤姆一直在领导着我们与本届博物馆管理层之间的斗争。《多伦多星报》称他为吸血鬼杀手。”
“潜在的吸血鬼杀手。”我更正了他,“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多罗迪取胜。”陈带着本古书。从它金黄色封面上的字来看,它应该是用中文写成的。虽然我能说这种语言,但要想读懂稍微深点的东西却很难。“那是什么?”我问。
“中国历史。”陈说,“我一直在和康争论。”康是近东和亚洲文明馆的路易斯·赫利·斯通名誉馆长,这个馆又是个在哈里斯削减预算之后产生的合成物。“这就是我要见霍勒斯的原因。”
弗林纳人把眼睛搭在一起,准备帮忙。
陈把这本厚书放在了我桌子上。“在1988年,一群工作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空间物理研究院的天文学家宣布发现了超新星爆炸的残余物——也就是一颗巨大的恒星爆炸后剩余的东西。”
“我知道超新星爆炸。”霍勒斯说,“实际上杰瑞克博士和我最近讨论过这个问题。”
“很好。”陈说,“那些家伙发现的残余物离这儿很近,大约有650光年,位于船帆座。他们叫它RXJ0852。0—4622。”
“很好记。”
陈没什么幽默感。他继续着,“公元1320年左右,在地球上应该可以观察到产生那些残余物的超新星爆炸。它应该比月亮更亮,而且白天也可以看到。”他停了下来,等着看我们中的一位会不会驳斥他。见我们没有反驳,他又继续下去。“但是世上没有关于它的历史记录,从来就没发现过相关的记录。”
霍勒斯的眼柄挥动着,“你说它是在船帆座?对你我两个世界来说,那是南星空。但我记得地球的南半球上当时没什么人口。”
“是这样。”陈说,“事实上,在地球上我们仅有的关于这次超新星大爆炸的证据来自于北极积雪中的硝酸钾峰值变化。同样的峰值伴随着其他超新星爆炸。但是我祖先的土地上可以看到船帆座,你可以从中国南部清晰地看到它。我想如果有人记录了它的话,那他一定是中国人。”他合上了书。“但什么都没有。当然,公元1320年中国正处于元朝中期。”
“哦,”我卖弄地说,“元朝。”
陈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元朝是由忽必烈汗在北京建立的。”他说,“中国政府通常对天文学研究很大方,但在那时候,蒙古人统治一切,科学也倒退了。”他喘了口气,“跟现在在安大略发生的差不多。”
“至少不是更惨,不是吗?”我说。
陈耸了耸肩。“那是我惟一能想到的为什么我的祖先没有记录这次超新星爆炸的原因。”他转向霍勒斯,“从长蛇星座第二上看这次爆炸应该和从我们这儿看没什么分别。你们有什么目击记录?”
“让我查一下。”霍勒斯说。幻影停止了移动,甚至他的躯干也不再一起一伏。我们等了大约一分钟,随后大蜘蛛又活了过来,霍勒斯又重新操控了他的幻影。“没有。”他说。
“没有650年前的超新星爆炸记录?”
“不在船帆座。”
“你该知道,这些是地球年。”
霍勒斯似乎被他可能弄错了这一暗示冒犯了。“当然。弗林纳人和吕特人观察到的最近一次肉眼可见的超新星爆炸发生在50年前,在大麦哲伦星云。在此之前,我们两族还在你们的十七世纪早期看到过一次,在你们称之为巨蛇的星座中。”
陈点点头。“开普勒超新星爆炸。”他看着我,“我们这儿在1604年之后就能看到。它应该比木星亮,但在白天只能勉强看得见。”
他咬着嘴唇,思索着。“这很奇妙。开普勒超新星爆炸离地球,或是长蛇星座第二,或是孔雀星座第四都很远,但三个世界都看到了并做了记录。1987A超新星爆炸,甚至不在银河系里,我们也都记录了。但船帆座的这一次却非常近,我一直认为会有人看到。”
“有可能当时被星际尘埃挡住了?”
“从现在来看我们之间并没有尘埃。”陈说,“而且要有的话,这片尘埃要么离爆炸的恒星很近,要么大得足以挡住地球、长蛇星座第二以及孔雀星座第四的视线。应该会有人看得到这东西。”
“真是个谜。”霍勒斯道。
陈点了点头,“一点没错。”
“我乐意向你提供我们的人收集到的超新星爆炸的信息。”霍勒斯说,“或许能给你的研究带来些许光明。”
“那太好了。”陈说。
“我会从母舰上送些东西下来。”霍勒斯说,眼柄来回摇摆着。
我十四岁时,博物馆为对恐龙感兴趣的孩子举办了个竞赛。得胜者可以领到各种和古生物有关的奖品。
如果是个恐龙琐事竞赛,或是考察你的恐龙科普知识,或者要求你辨认化石,我应该可以赢,我很有把握。
但它不是。它是个最佳木偶恐龙比赛。
我知道什么龙最合适:似棘龙,博物馆的标志性化石。
我打算用橡皮泥、泡沫塑料和木头销钉做一个。那是一场灾难。顶着根长棘的头常常会掉下来。我一直都没能完成。一个胖小孩赢得了比赛。他领奖时我就在下面坐着。奖品中有一头蜥脚龙,他却说:“真棒,雷龙。”我感到恶心:甚至在2O世纪6O年代,任何稍具恐龙知识的人都不会把它俩搞混。
但我的确学到了东西。
我知道了你无法选择你被测试的方式。
唐纳德·陈和霍勒斯可能痴情于超新星大爆炸,但我还是对我和霍勒斯以前谈论的话题更感兴趣。唐刚刚离开,我就开口了:“霍勒斯,你们这帮家伙好像很懂DNA。”
“可以这么说。”外星人说。
“你们——”我结巴了一下,我咽了口唾沫,试着继续说,“你们对DNA出现的问题有研究吗?比如复制过程中的错误?”
“你知道那不是我的研究范围。”霍勒斯说,“但我们船上的医生,莱布鲁克,应该是这一行的专家。”
“这、这位莱布鲁克……”我咽了口唾沫,“……这位莱布鲁克对疾病有没有研究,比如说癌?”
“癌的治疗在我的星球上是一项专门的学科。”霍勒斯说,“当然莱布鲁克也懂一些,不过——”
“你们能治愈癌症吗?”
“我们用放射和化疗。”霍勒斯说,“有时有用,但经常没用。”他听上去很悲伤。
“噢。”我说,“地球上也和你们差不多。”我安静了一阵子,显然我期待的是一种不同的答案。哎,管他呢。“说到DNA,”最后我终于开口了,“我在想你是否能给我点你自己的样本,如果我的要求不算过分‘我想对它做些研究。”
霍勒斯伸出一只胳膊。“请便。”
我几乎忍不住想去摸它。“你不在这儿,这只不过是个投影。”
霍勒斯放下了胳膊,眼柄做着S形运动。“请原谅我的幽默感。当然,如果你想要DNA样本的话,随时欢迎。我会让飞船送点下来的。”
“谢谢。”
“我可以告诉你将会看到些什么。你会发现我的存在和你一样是极小概率事件。一个高等生命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随机产生的。”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不想和外星人争论,但该死的是,他是个科学家。他的头脑本该更清醒些。我转动椅子使我面对计算机。计算机放在我以前刚上班时放打字机的地方。我有一个漂亮的微软垂直分体式键盘。在雇员委员会开始抱怨应增加腕部职业病保险金后,博物馆不得不把它们发给每一个开口要的人。
我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