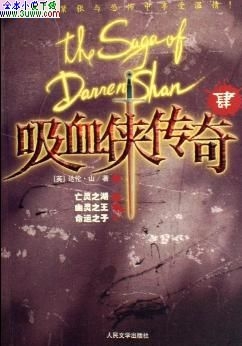家妇·山泉·有点田-第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应松
一
以下的故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并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都是我哥哥梦中告诉我的——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与我哥哥有某种灵犀,仿佛是一个人似的,谁叫我们是孪生兄弟呢。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
三年前,母亲死了。母亲在田里干活,一块石头砸下来,死了。当时还请了山下很好的老中医来看过,喝了大粪和童子尿,母亲还睁开了一下眼看了我们哥俩,后来就死了。母亲死后,爹疯了一阵子,把田里的庄稼全拔了。我跟哥哥商量着就准备出去打工。我们山谷有不少人在河南挖煤,我们也准备加入那个队伍。给爹说了,爹那时候吃了些药,病情控制住了,点点头算是表示同意和给我们送行。我们从羊家村出发,沿着落羊溪河岸,跟在一群光屁股的纤夫后头,一直走到十堰,再坐火车到了河南挖煤的地方。
走的时候,鲍家姊妹一人给我们绣了一条汗巾,说是擦汗的,上面绣了些喜鹊梅花的图案。当然也像是樱桃。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哥哥就拿出那汗巾说樱桃开了。因为鲍家门口有一棵山樱桃树。樱桃开花早,花事很盛。每当樱桃开花时,一定是春雷滚滚的三月,细雨润物的三月,哥哥就使劲地抽着鼻子说:樱桃的花好香。他一定会丢下手中的农活去看鲍家的大女儿鲍早霞。
哥哥拿着汗巾说了三年,三年没回去。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然而事实如此。甚至三年没有和自己的意中人通书信来往。但是有一次,爹来鬼鬼祟祟地看过我们,后面还跟着一个派出所长的老婆。那个女人是我们出了五服的三表姑,我们叫秀三姑。爹见了我们,劈头一句话:“还活着啊!”——这是什么话!爹说是随秀三姑来河南办什么事的,要我们给几个钱。爹的疯病好了,这是我们高兴的。还带来了鲍家早霞晚霞的口信,说是希望与我们哥俩尽快把“会头过了”(就是办喜事)。哥哥很高兴,说总得把房子修修,两张新床总得打吧,就给了爹五百块钱。爹拿着钱就与秀三姑一起走了。
回去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爹跑了。爹扔下奶奶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跑了。哥哥走进自家房子里的时候,房子歪歪欲倒,就像全家人都去城里打工去了一样——凡是全家去城里打工的人家,房子都是这么一副七歪八倒的破相,门前荒草丛生,草中小兽扒出的浮土成堆。还不止这么,哥进村的时候人们一副难看的眼光看着他,说:“大双还是小?”当证实是大双之后,又说:“活着呀?你究竟是人是鬼?”热气腾腾走得大汗直冒的哥哥惊诧得不行,我不是个活人么?他就说:“我不是个活人么?”那些人说:“唔。真还活着哪。”他们握他的手,手上是热的,还一股子狐臭味,这是大双小双。他们说:“唉。”哥哥万分不解。可一想也是,山谷里有几个死了。到煤矿活着回来也不易。就给他们说:“我跟小双下矿井,是分开班次的——他下我不下,我下他不下,万一有事,总有一个可以回来。”可他们说:“说是你们两个都死球了咧。”
咒人死的人不得好死。哥哥心情极坏地走进屋子里,从黑暗中伸出一双死尸般的手,还有个死尸一样的声音说:“大双,是大双么?大双真回来了?……”这就是奶奶。奶奶已经没有了人形,花白的头发一团一团的,没有牙齿支撑的嘴巴和腮部,已经变成了泄气的皮球。奶奶说:“给我口水喝。”奶奶说,她有三天没吃没喝了。没人给她吃喝。她摔了一跤,爬不起来了。奶奶说,她经常挨饿,经常病,起不了床,就这么饿着,连家里的狗也饿死了。可人是顽强的,奶奶虽然三天没吃没喝,却吐字清晰,看人准确。如果不是哥哥回家,她不会三十天没吃没喝么?就算三十天没吃没喝,奶奶还会活着。这就是咱山里的人,跟石头一样坚强的人。
爹不见了,修理过的房子呢?新打的床呢?没有。哥哥就说:“奶奶,我是给爹五百块钱了的啊!”奶奶说:“鬼的钱,连一头猪都被你该死的爹背走了,这个奎友贱鬼呀!”
“我跟您去找您的贱鬼儿子奎友回来!”哥哥说。
他就去村里问,看爹奎友是到哪儿去了。走出门去,狗都咬他,都是些新狗,不识人。有一家人家正在放鞭,听说是生了娃儿,请客坐流水席,派出所长也来了,就要我哥大双去喝一杯。大双盛情难却,上了二十块钱的人情,正准备进屋,派出所长出来了,姓艾,大家私下叫他艾滋哥,脸上长着许多疱疹,鼻子发紫,牙齿发黑,常年吞云吐雾,连舌头都是黑的。这个长我们一辈的派出所长见到我哥哥,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咧得开开的,牙缝里夹着绿莹莹的蔬菜,说:
“鬼啵?”
我哥哥吃得很难受,艾所长又拿很难听的话取笑他,主人看派出所长的面子,赔着笑。派出所长说的很恶毒,大意是说那么多人死在窑里了,你为何活着回来了;还说,说死的没死,没说死的死了。
我哥哥当时还是蒙在鼓里,直到他去了自家的田里,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走到自家地头,有两亩多上好的阳坡地,一挂流泉从石上逶迤下来,田土被泡得松松的,苞谷苗比别人早出半个月。田里果然出了苗,迎风摇曳,绿得让人直想流泪,想都没想究竟是谁种的,爹或者奶奶。可有人从山石背后钻出来了,竟是邻家的梁毛子。
“大双小双呀?”
那梁毛子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眼睛直了,好半天吐出一口气来,摇摇晃晃站起来,拿上锄头,说了声:“我中了圈套了!”就飞也似的跑下坡去,眨眼就跑得没影了。
我哥哥甚为吃惊,恰好上来个打柴的人,就问刚才梁毛子为何躲着他,说什么中了圈套?那人想了想说:“可能是他见你回来了,这田又要回归你名下。”我哥说:“这田给了梁毛子?”那人说:“可不是,都说你们死在河南了咧,你爹疯了也不见了,田就给了毛子种了,这可是一亩顶十亩的好地啊,哪能闲着。”
我哥望着碧绿的苞谷苗,这地成了他人的地。我哥哥前思后想,不是个滋味,地旁有妈的坟,坟塌了,青草黄草杂乱,我哥哥就跪在妈的坟前好一阵痛哭。哭过之后又用泉水洗了一把脸,决定去野羊尖鲍家。
二
应该是第二天。
应该是第二天吧。这天夜里,雷声轰鸣,好像世界要翻覆过来一样。我哥哥是送走了梁毛子,雷才开始打的。梁毛子是个可怜虫,爹死得早,娘又再嫁了。娘想管他,后爹打他,从小在外乱蹿,与我们年龄相仿;后来是被他的舅舅找回来的,村里二轮承包已经分完了地,村长就说等谁死了划地给你,就要他吃百家饭,像个小康工作队队员一样,吃派饭,到了吃饭的时间,只消拿个碗去别人家就行了,点着吃,有腊肉吃腊肉,有活鸡吃活鸡,你若不干,就找村长来,大家恨死他,巴不得他得急症死了,或吃鸡让鸡骨头卡了喉咙。奇怪的是,那几年村里没死一个人。可如今回来,我们哥俩成了死人,田给了梁毛子。梁毛子怕我们哥俩,那时因他偷吃我家一只鸭子,揍过他,揍服了。梁毛子就来给我哥哥说:地我退了,损失我找村长算去,还给我哥拎来了一块麂肉。后来雷就打起来了。
这个晚上的雷声是我哥哥听到的最不安的雷声。在我们落羊山谷,是个雷暴多发区,只要打雷,那一定是惊心动魄,电光闪闪,火球滚滚,树啊,人啊,畜啊,谁沾上谁亡。雷本来是最好的,漫长的冬天过去后,雷会把阴暗潮毒的秽物彻底打跑,让阳光春光回到这遥远的山谷,让河水解冻,土地酥松,墒情爆发,万物昂扬。听着这山谷的雷声,还夹杂着雨的欢歌,躺在暖和的被窝里,重回故乡的感觉应是无比安逸的,就像一首歌所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可我哥哥听到那尖锐严厉残忍的雷声,就像是自己的心肝放在磨刀石上来回揉搓撕刮一样。风在狂烈地吹着,下起了冰雹。雷还不走,在村子上空无耻流连,像个无赖,寻找着下手的目标。
我哥哥认为这雷是冲着他来的——有一忽他这么想,可我哥哥没有找到他被雷打的理由。我哥哥跟我一样,都是个善良的人,三年暗无天日的煤矿生活,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念着“农妇/山泉/有点田”互相鼓励,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赚点钱,回家娶个媳妇,养儿、种地、过日子去。
第二天,是雷暴过后的寻常日子,天晴了,田野和山谷清亮过人,云彩像洗晒过的棉花,远处的山峰历历在目。而且植物的气味会更重,开花的花蕾只要晾干了水珠,就会绽放出来,碧绿的叶子会更清纯,像少女的羞涩。猪在烂泥里叫得欢,牛铃的声音亮晶晶的,村庄像天堂一样干净美丽。哥哥向野羊尖走去时,在路边看到一棵被雷劈断的巴山冷杉,烧得黑糊糊的。他的心情本已经被早晨弄好了的,看到那树,又惴惴不安起来,并且心跳突然紊乱,这时,就看到了鲍早霞,我未来的嫂嫂。
我未来的嫂嫂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未来的嫂嫂烫了发,还染了,染得黄不拉叽,嘴巴上亮晃晃的,好像拔过胡子一样,一看就是个妇人。最要命的她是从山下来的,敞着怀,两个松松垮垮的乳房在毛衣里乱蹿。我哥哥怎么想呢?我哥哥想过一千次,看到的早霞应该是像初升的早霞一样出现在樱桃树下,眼波如泉水,微露尖细的米牙,可能会对着山下唱两句晃晃悠悠的山歌,一定要带着让人心痒的神秘和调皮,当然了,还会有一丝他所理会的放荡。一个女人不放荡,就简直不是女人。
哥哥说:“早霞!”
那早霞正埋头爬坡,听到一声熟悉的唤她名字的声音,就站住了,抬起头,看到逆光里的我哥哥,大双。
“你……你!……”
早霞盯着哥哥,上前来,抽了他三个耳光,说:“是真的?”
早霞的手打麻了,一下子抱住我哥,悲也似的大哭起来,还找他的嘴,要亲吻他,安慰他。
我哥哥被她的动作搞得连连后退,差一步就要退到悬崖边摔下去了。我哥哥推开她,远远地打量她,带着愤怒和遗憾打量她,说:
“你从哪儿来的啊?”
“我问你从哪儿来的?”
“家里。”
“我也是家里。”
“下面?”
“下面,你还活着呀大双,我已经死了,我嫁了个老公叫艾滋!……”
这时一个晴天霹雳,一个晴天霹雳就是早霞的话。
他们互相搀扶着上了野羊尖,野羊尖的樱桃蔫了,野羊尖的鲍家老屋,弥漫着一股腐臭,他的未来的弟媳——晚霞双腿溃烂,眼睛已经瞎了。
“……我每天早晨都要上山来,取下在树上接的露水,为晚霞洗眼睛和双腿的。”
早霞从那要死不活的樱桃树上,拿下一个大盘子,那里面存积着晚上收集的露水,来给晚霞洗眼睛。可是晚霞在号叫着,捂着她的腹部。她萎缩的双腿流着奇怪的黄水。
我哥哥越来越感觉不到真实生活的刺激,他像在噩梦中迷路穿行一样,听着一个年轻女子的怪号。另一个花枝招展如女妖的女子手拿着从山上承接的露水,为这号叫的女子擦洗着眼眸和身子——而这女子已经病入膏肓。
“哥哥,大双哥哥……”这个女子喊他,声音带着痛感。
“你会好起来的。”
这时她们的父亲,一个瘸腿的老男人蹲在门槛上悲声大哭起来,手捧着干瘪的脸腮。他这一哭,把我哥哥弄得更加惶惶不安,心里尤其难受。
“啊呀!……哇呀!……”
狗也汪汪叫起来。
“没有用了,怎么都治了,没有用了,家产都败完了……”早霞伤心地说。
后来,因为那个老男人的哭声止不住,早霞也被勾引了,哭声从喉咙里冲了出来,同时捶打我哥哥的肩膀:
“你呀,你呀!砍脑壳的,都怪你们两兄弟呀!……”
事情是:在我们去河南打工的第二年春天,樱桃花开之后,早霞就想去找我们。于是姐妹俩就去了河南。可找不到具体的地方,只好坐火车回到宜昌,在宜昌碰到一个神农架的熟人,那熟人就神说鬼吹要姐妹俩去福建上班,说是一个月吃了喝了一千块钱,还不加班。早霞不为所动,晚霞动了心,就与几个兴山、秭归的女孩子一起跟那人去了福建。在一个小鞋厂里上班。没想到半年以后就开始头晕、呕吐、肌肉发颤、萎缩、视力下降。没撑到年底就回来了,回来眼就看不见了,不能正常走路了。后来找对方赔了三万多块钱。这钱治病也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