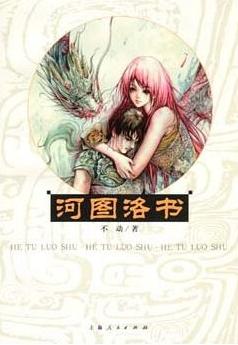洛书·胭脂碎-第5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杀戮重重(六)
元昊三年,腊月十七,明日便是十八,皇上出宫拜太庙祭祀之日。
流苏已经走了好几日,仍无音讯,我心底有一点儿的着急了,不过仍依旧如常浅笑,怕先乱了皇甫轩及其他人的心。流苏未回,也无法得知哥那边做了何等安排,是否可以瞒过洛谦的耳目?
“柳姨,菜叶上的水都洒到脸上,大顺这就给柳姨擦擦。”大顺举起袖子,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污水。大顺跟他爹李柱子一样,都是个憨厚的直傻性子。
“大顺真乖。”我和煦笑道,继续与碧衫准备过年的腌菜。
掰开刚摘下的大白菜,我问道:“碧衫,和李大哥说清楚我们的事没有?”在留宿碧衫家的第二日就跟她道明白了我们的危险状况,并嘱咐要她向李柱子解释清楚,免得让李柱子不明所以的受了牵连。
“没有。”碧衫心虚地低下头:“我还没有和他说过我曾经是大将军府的丫鬟,他还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普通商家的丫鬟。”
“糊涂!”不知怎么的,心里就是有一股不安升起:“今天午饭过后,带李大哥到我房里,我亲自说明一切。”
午饭后,在我暂住的简陋瓦房中,李柱子坐立不安,终于嗫嗫问道:“扶柳妹子,碧衫说你有天大的事要告诉我,是什么事啊?我还要赶着进城送菜呢。”
我端坐在坑上,面色严肃,摊掌指向对面:“李大哥请坐。”
“我代碧衫先给李大哥道歉,碧衫刻意隐瞒了我的身份,我怕这样会给李大哥带来许多麻烦。”
李柱子疑惑道:“扶柳妹子不是碧衫的小姐吗?”
“我的确是碧衫的小姐,可你知道我是哪家的小姐吗?”我反问道。
李柱子抓头想了一会儿,才猛地摇头:“碧衫没有和我提过啊!”
“我是上官大将军府的小姐。”我字字郑重:“天朔八年,嫁于当朝丞相洛谦。现在卷入皇宫纷争,随时都有性命之虞。”
李柱子瞪大眼睛:“将军和丞相都不是很大的官吗?妹子是贵人,怎么会死呢?”
“其中曲折怕是很难让李大哥明白。”我言简意赅说道:“李大哥现在和我们在一起有生命危险,李大哥还愿意留宿我们吗?”
“当然,说好了一起过年。”李柱子呵呵一笑,披起旧棉袄:“我还要赶着送菜呢。”说着匆匆离去。
无奈摇头,像李柱子一样的憨直农民怕是一辈子也无法理解皇宫中的不可思议,明明是亲兄弟,却必须你死我活的战斗;明明是一家人,却必须勾心斗角的算计;明明是可口的点心,却怕是别人的毒药;明明是……这样平静的生活,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呢?
单纯而直率的想法,热忱地对待每一天,石头村的人无权无财却更加懂得生活!
想着想着便累了,身子一歪,顺着躺在坑上,静静的睡了一个下午。
晚饭间,李柱子对我笑道:“妹子,我今儿回来的时候向村头的王老二打听了。原来丞相的权利很大的,将来妹子回家了,能不能请丞相妹夫帮一个忙啊?”
“就是村里的李员外老是喜欢提高租收,听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在城里当官,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嗯。”我心不在焉地点头,心里惦念着流苏。皇甫轩倒是心细:“你怎能在村头酒铺当众问及丞相呢?”
李柱子连摆手道:“只问了一点点。”随后指着门口笑道:“冷面姑娘回来了。”
流苏肩后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袱,沉甸甸的也不知装了多少东西。
“不用追究了,明天我们就要离开石头村。”我起身走向流苏,然后又不放心回头嘱咐李柱子一句:“李大哥以后不要再提有关于我们的任何事,否则会引得官府人员前来的。”
李柱子惊骇道:“官大爷,是要抓我进大牢吗?”
“是啊,看你还多不多嘴!”碧衫从旁训斥一句,便领着我与流苏进了卧室。
杀戮重重(七)
卧室中,如豆昏灯,一时静谧,皇甫轩悄然进入,碧衫无声退出。
一股压力在室内纠结。
流苏脸上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竟露有喜色。她手指轻快打开沉甸包袱,顿时流离光彩映满了狭小卧室。
不由得,我与皇甫轩的呼吸渐渐沉浊。
精致的锦缎代表了太多的含义,至少它显示了主人光鲜的地位。
凤栖梧桐,龙啸九天,繁复绝伦的锦绣。
“是长公主与皇子的礼服。”皇甫轩说道,淡淡的笑意扬上了他的唇角。
“少爷要我将这些交给小姐。”流苏道:“少爷已经策划好一切。”
我面沉如水,淡道:“说吧。”
“少爷说,非太庙祭祀之机不可。但丞相定会阻杀,所以必然会有牺牲。”流苏思路清晰,剖开层层复杂情势:“为今之计只有调虎离山,将丞相重兵吸引到一个点上,削减其他点的防备实力,趁着此时进入太庙,对文武百官宣读圣旨。”
皇甫轩轻轻摇首:“要他中声东击西之计,谈何容易?”
“有饵便好,只要是重饵,就有机会成功。”我无力再笑,只是在平淡说话:“敲打东西两侧并不够,最好是兵分三路。”
流苏讶异:“老爷与少爷足足商讨了十日,原来小姐早已想到这个法子。”
我轻叹:“我也辗转几夜,掂量许久,才想或许这是唯一可搏的路了。”
“兵分三路,我们本就微薄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分散,洛谦不是更容易一一歼灭?”皇甫轩乍见礼服的欣喜已经凝固,浓眉渐渐拢起。
“第一路的人是哥,为了迷惑洛谦;第二路的人是可以吸引洛谦出手的人;第三路才是我们,洛谦想要阻止的人。”说话时,我知道我有多么的苍凉乏力,只能靠着墙汲取一点支持。洛谦我开始算计你了,而你现在呢,是否也在和墨斋算计我?
“哥带着流苏与辕儿,打着骠骑将军的名号大方地进太庙,同时流苏与辕儿不经意间露出模样,让洛谦知道你们的存在,与哥在同一辆马车上。这样可以很容易地让人联想到,我与轩儿也藏在骠骑将军的马车里。”
“另外一路是找一个与我形态相似女子假借某位官员之名,拣隐蔽小路通向太庙。当然这些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却反而能让人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设局,将众人目光引到骠骑将军马车中,然后趁着空隙挤入太庙。”
“而我们真正要上的马车是西华大将军的专车,正大光明的驶入太庙,不遮不掩。”
皇甫轩眉拧极而舒,忽而放声笑起:“好计谋!”
笑声朗朗,却不悦耳,皇甫轩墨瞳闪有诡异光芒,将原本冷硬的嗓音刻意说得柔缓:“父皇在世言,能够打败洛谦的人世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将他看透之人,另一种是他弱点之人。三姨,你是哪种?”
我是哪种?我也不知道我是哪种!
我的身子在颤颤发抖,皇甫轩,非要将我逼上绝境,才肯相信我会辅你登上晋王位吗?
你们,上官家,皇甫家,一个一个的人,都在寸寸分裂我与洛谦,是否真的我与洛谦决绝对立,甚至再见便为仇人眼红,你们才会甘心吗?
杀戮重重(七)
心底的怒火在遍地蔓延。
院外的喧闹及时的止住了我与皇甫轩的对峙。
粗暴的砸门声,乱吠的犬叫声,喝斥的怒吼声,一切都在显示着不安气氛。
卧室门被慌乱的打开,碧衫冲了进来,神色惊慌:“小姐,都跟着我到地窖躲一下,快点啊!”
“什么人?”我问道。
碧衫抓着我,一个劲地跑向柴房,还喘着气解释道:“我刚才从门缝里瞟了一眼。外面全是凶脸的官差,手里还拿着亮晃晃的刀,我想一定是来找小姐的。”很快进了柴房,皇甫轩抱着辕儿,流苏背着包袱,齐齐地盯着碧衫。碧衫也不含糊,快速地掰开柴房角落的草堆,揭开一面木板:“小姐,这是储藏粮食的地窖,赶快先进去避一避。”
“你们呢?”我怒道。
碧衫求助地望了一眼流苏,随即流苏就拖我进了地窖。碧衫盖住木板,地窖内顿时黑暗无光。碧衫的声音从上方遥遥传来:“小姐,我与柱子哥没敢什么坏事,他们没有理由抓人的。”
砰地大响,像是大门被踹开,接着就是骂声一片:“想造反了,居然不给官差开门。”
“我们庄稼人睡得早,所以开门迟了,官大爷们息怒。”是李柱子的赔笑声。
官差一哼:“妈的,你小子是不是叫李柱子啊?”
“嗯,正是小的。”
“抓起来,关进衙门!”
一阵骚动,铁链叮铃作响。
李柱子大喊不断:“官爷,我冤枉啊!”
“是啊,我家柱子哥犯了什么事?”碧衫抗议道。
官差嘿嘿笑起:“什么事?自己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你这贱民竟敢打听丞相大人的事。”
“民女相公只是恭敬相爷,所以才想知道相爷的英雄事迹。”碧衫在紧急时刻终于学会如何说话了。
“少耍花枪了。”官差并不理会:“你们收留的人呢?藏到哪里去了?”
果然还是冲着我们来的!在死一般黑暗的地窖中,皇甫辕最为安静,因为他被点住了睡穴,避免看到将要发生的残酷画面。皇甫轩与流苏面色凝重,都在静静的聆听着。而我习惯性地抱紧了沉甸的乌木圆筒,三年了,我从未将它离开我一丈之外,每当遇到危险时我总是抓着它不放,因为我知道里面的圣旨是支撑我的力量源泉。
“官爷弄错了,小民家中没有外人啊!”李柱子辩解道。
四下翻箱倒柜,锅碗瓢盆的破碎声叠叠响起。
莫约那群官差们在屋子里搜了一刻钟,没有发现我们的踪影,便又骂骂咧咧道:“他妈的,还真的没有。”
“如何交差啊?上面又催得紧,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沾点边的,就这样摆手了?”大抵是为首的官差说的。
立即便有一个媚谄道:“定是这个刁民隐瞒,爷何不带回牢中细细审问?”
“好主意,回去时我会禀告老爷你抓贼有功!”为首的语气十分愉悦。“李家三口窝藏逃犯,立即押回衙门送审。”
顿时,李柱子大声叫屈。其中还夹杂着大顺的哭啼声。
竟然连稚龄小孩也不放过,我感觉自己气血上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伸手便要推开木板。
蓦然手腕一凉,已被一只铁掌紧紧抓牢,皇甫轩的脸近在咫尺:“你要做些什么?毁了三年的努力吗?”
冷冷的一句喝斥,冻结了我身上的沸血,颓废地垂下手了。
“最近洛谦急于寻人,弄得每个衙门胆战心惊,每日都要上交可疑人等。”皇甫轩松开了我的手腕,徐徐解释道:“所以各衙门乱抓人,以充数也是常有之事。他们一家抓入衙门,并无性命之忧,待明日大事成功再放他们出来也不迟。”
时间稍滞,官差们便已带着碧衫一家离去了。
渐渐,农家小院又归于黑夜的宁静。
杀戮重重(八)
再次伸起胳膊,我轻叹道:“这次可以出去了吧!”
同样的快速抓住我的手,然后扯下,皇甫轩淡道:“外面可能还有危险,你不会武功,我先上去瞧一瞧。”说罢,推开木板,跃然一跳,出了地窖。
一盏茶后,我才得见院里院外的狼狈场景。
原本温馨的小家再无一处完好,破裂的木块,粉碎的瓷片,掀翻的桌椅,拆下的门板,充斥了整个视野,甚至还有淡淡的血迹。
夜风吹起,将血腥之气弥漫院落。
“流苏,现在就开始准备吧!”我将乌木圆筒抱得更紧,直勒得胸口一阵阵的痛。
“是。”流苏应道,随即跟我进了门窗俱已砸破的卧室。
瞥了一眼院里的皇甫轩,他随意坐在草垛上,仰面遥望星空,水晕月光洒在他洗旧了的淡青袍子上,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
明日,他就要踏上孤寂的帝王路了。
“流苏,点根蜡烛。”我收回视线,吩咐流苏道。
流苏在狼籍中翻出一根折半的蜡烛,从腰间取出火折子,点燃半截蜡烛。
我深深吸气,捧出乌木圆筒,将圆筒前端置于烛火之上,然后目不转睛盯着圆筒。一会儿,封住圆筒盖子的蜡开始慢慢融化,小心地转动圆筒,一圈下来,已流淌了一滩白蜡。
将圆筒移开烛火,手有些发抖,覆上了圆筒木盖,我无意识地叫了一声:“流苏。”
流苏虽然表面如以往沉静,但呼吸早已乱,声音也颤:“小姐,老爷的马车一个时辰后,便抵达这里,接小姐与大皇子去太庙。”
流苏的话语似在鼓励,我还有上官家作为后盾。
轻旋开木盖,耀眼明黄倾泄而出。
这是皇甫朔的最后一道遗旨。
就在微弱的烛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