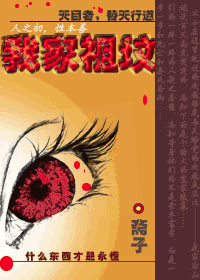祖坟-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青青,感到舜铨的离去对她们是早了,这也是这对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无可挽回的一步。
拆去隔扇的房屋连成一片,显得衰旧空旷,一座即将被拆的旧屋,正如一个趋向死亡的老人,使人觉得它已名存实亡,昔日那无处不在的灵气,那给人以依赖的坦实,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我说还是把七哥送医院去吧,丽英无言,大舅爷说,已是不治之症,现在也没有安乐死,将来青青母女还要过日子……我明白了大舅爷话中再清楚不过的意思,这使我盘在心头许久的辛酸热热地升起来,泪水充盈了鼻腔,我屏住气息,将那苦涩之水咽了下去。想舜铨一生,辛勤作画,与世无争,也曾有过艺术的辉煌,也曾有过人生的佳境,如今谁识京华倦客,回首悲凉,都成梦幻,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舅爷见我无言,无指桌上当年我由祖坟抱回的绿釉罐说,姑老爷骨灰,将来可否置此。我一惊,没想到连骨灰盒的开销也算计到了,思考如此周到精细非头脑冷静之人而不可为,看来家内并非人人都悲伤到昏天黑地的份儿上。骨灰盒的价格想来不过百元之事,我与舜铨穷是穷,终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父棺前掘出,内装残羹剩饭,霉烂不堪,后虽返家,又被充作沤花肥泡马掌之物,污秽难闻,舜铨清爽洁白一生,终了怎会委屈此物之中。青青说古色古香的,菊花一样的造型,挺可爱的呢,我用洗碗液浸泡了好几天,不脏。父亲前几天跟我说好几回,让我把这个罐子擦洗出来,说最近可能有用,我想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我说,你父亲若真有这想法,自然会明确提出,若未言明,骨灰盒所用之资连同火化费用和住院费用全由我承担。大舅爷立即跟上说,有了姑爸爸这句话我们心里多少有了底,都说姑爸爸一次的稿费抵得上阿英数月的工资,姑爸爸与姑老爷手足情深,这种至爱亲情我们当好好学习呢。当然,一切也不能全依赖姑爸爸,众亲戚也会齐心协力的。我明白自己是钻入了另一个家族的圈套了,我将在舜铨这件事上被大大地敲上一笔,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我们这个家庭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工于心计,察见渊鱼的人物,到我这辈,却怎变得如此木讷呆傻,不谙世事,小家小户出身的丽英姐弟,自有着小家小户兄弟姐妹间的提携与关照,有着小家小户的精明与狡黠,这一点无论我与舜铨,都不是对手。就是从这个家门走出的,在政治上能翻云覆雨,左右大清帝国命运的人物与舅爷们相对,怕也多会败下阵来。我开始怀疑舜铨所留大批藏画的真实下落……
为了证实舜铨是否有将自己装入绿罐的意向,我决定将罐子抱到小屋去,摆在他的窗台上,让他日日可见,不会没有说法。我抱起罐子踏着积水,穿过荒凉冷落的小屋,怀中的绿罐在细雨中似乎发出一声凄异的叹息。
舜铨正在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噢,你把它拿来了。说着接过去,细细地抹拭。我想说骨灰的事,却终张不开口。舜铨说,这个罐啊,从你拿回来那天,我就知道它不是寻常东西,故意冷落着它,为的是让它悄没声儿地,完好地保存下来,八百多年的岁月,如今该派用场了。我问他可派什么用场,他笑而不答。我说那就卖了它,八百年的东西能值不少钱。他说以钱而计便玷污了国宝,怎能俗到如此地步。此绿菊铁足凤罐产于宋建炎二年官窑,因泥胎配制特殊,罐底露胎部分呈赤铁色,质硬似钢,击之发金属音,其色与绿菊色相近,来自天然,与哥窑的豆绿和清代雍正御厂仿烧的豆青又不同,绿中暗含水气,流光溢彩,变化无穷,极为罕见,是宋瓷绿水釉中仅存精品。一窑百件,成者有二,一大一小,大曰龙罐,小曰凤罐,官窑所制,大都专为皇室,物以稀为贵。仅此两件作为传世,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惶逃到杭州,扬州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罐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流入北国。后因长期辗转,下落不明,瓷史虽有记载,终未见龙凤罐实物,作为研究南宋官窑的重要实物资料短缺,实为遗憾。不想启祖父之坟,使凤罐重见天日,这实为中国陶瓷界一大幸事。可惜,以后运动连接不断,瓷罐虽在,总无机会献出。今我来日无多,想必大限之日便是凤罐曝光之时。他说已给有关文物部门写了信,希望不日派人来家取罐。舜铨说1930年中国有个叫朱鸿达的人曾依据宋《咸淳临安志》所指官窑地址搜集瓷片编印成书,于1937年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所集众多瓷片中,独缺铁胎绿菊釉,今所献绿菊铁足凤罐,当补此空白。我问凤罐何以会到祖父之手,舜铨说他也说不清楚,祖父一死,再无人识货,仓促间抄来作棺前祭物,也算是跟陶瓷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祖父殁于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整个大清王朝一片慌乱。袁世凯放出风来,要将诸皇亲驱进皇宫,关押在北五所的空房里,继绝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样一来,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肃王避往日本人占的旅顺,恭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有人劝祖母赶紧携家人择地躲避,祖母说贝勒爷际在弥留,要死便死在自己家中,谁见有抬着病人逃难的,老死外面,即便葬于祖坟也寻不回自己家门,何苦?再说,今日之势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了,可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只要京畿不起后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清江山善始善终,共和就共和吧。1912年2月13日,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北京各大家报纸全文发表,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改朝换代了,是共和的天下了!”在皇帝“必为列圣在天之灵暨皇族、宗支、王、公、亲贵等所共谅也”的哀告中祖父逝去。北京东城家中,留守者仅祖母和稀里糊涂的长子,江山已无,家亦难保,在一片忙乱中祖父的丧事办得十分草率,凤罐划名其妙葬入太阳宫墓地自然在所难免。
我为舜铨对身外之物的洒脱而敬重而释然,以他一生之经历,所得与所失,岂可用八百年的罐子所能了断。我想起骨灰存放老山骨灰堂的事,便有意把话往身后之事引。我问舜铨还记不记得看坟的老刘,他说怎会不记得,要活着今年该有一百零七岁,怕是早已作古了。“四清”时他的孙子刘建民来过,为那五亩地划分成分的问题他给刘建民写过一个证明,说五亩地系我家坟地,刘家租种,按时交租,属租佃性质。“文革”时刘建民又来,是来算剥削账,带了一车农民造反队战友,一通摔砸掠抢之后,打断了舜铨两根肋骨。舜铨认为,他以一纸证明,两根肋骨,给刘建民撑足了面子,总算没负刘家百余年看坟辛苦。可是刘家孙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舜铨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抵美丽富饶的淋河平原,雄浑壮丽,坦荡开阔,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源,积得一分阴德才得一分享用。他在“文革”中能大难不死,我在西人河滩能转危为安,皆倚祖宗荫庇、与祖坟所选穴位也大有关连。他说自“文革”后再未去祖坟祭奠过,但祖坟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群山雄峻,旷野凄迷,老树无言,草衰阳西……金凫几经秋叶黄,暮鸟夕阳摧晚风……我明白,舜铨印象中的祖坟景致实则是宋朝无名氏名画《秋山游眺图》的一部,这个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画家,至今仍没有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没有挣脱出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对祖坟的虔诚与对中国文化之美的感动作为情感体验和艺术造诣而互为混淆,达到了迷狂的程度。果然,舜铨最终提出死后回到父母身边的愿望,并希望我和他的女儿青青共同操办完成。他说,青青还年轻,正在上学,然而作为这个家中的唯一传人,黄花山她不可不去……舜铨在说这些话时不像说他自己,而像在谈论别人,语调缓缓,平静坦然。他像窗外一枚即将辞枝的黄叶,离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道别,在沉默的睇视中得到深切的理解,然后轻轻地飘落下去,心满意足地化作土灰。
四
我去医院联系舜铨入院事宜,因考虑是自费,院方给予很大通融,就这亦需先预交押金八千元。医院的人说。这种病到现在程度,本不应收,在护理方面力量牵扯太大,现在护士又奇缺,考虑病人是个德高望重的画家,家属又确有困难,收便也就收了,但钱是需要大量准备的,八千元只是底金,另外还需三日结帐一次,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我一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
出了医院门我就给西北的丈夫打电话,让他速筹三万元,两日内电汇北京。他说三万元岂是两天能凑齐的,就是借他也要跑几家。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啊,他仍表示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颇拮据。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骂他是冷血动物,不谙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嘛这样,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啦……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要哭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使电话哪!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相离是多么的惨情,它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渗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酸楚,更是兔死狐悲的怯怯惶恐。
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风市场北门丰盛公买乳酪,这是舜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公是个院落,绿门脸,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舜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酷,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溜回去,逢在我嘴上沾有糖渣、粥迹,他便会蹲下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似兄妹倒似父女,如今,昔日冷静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来到丰盛公时布帘已经挂起,小吃部关了门挂起了拆迁的版子。我忽然觉得极累,靠在小吃部的墙上,呆愣愣地看着进出市场的男男女女。有步履匆匆的,有悠哉游哉的。有空手的,有携物的,好像大家都很有钱,都活得惬意而自在,唯有我,像被美好生活甩出来的倒霉蛋儿。
回到家里已经亭灯,舜铨的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以为是文物部门来的人,朝他点了点头。孰料那人张口叫了我一声“大表姐”,一下把我推入云里雾中,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称我为表姐者南方口音,面孔白皙,身材微胖,穿戴极普通,眼镜后面是一双俊美有神的眼睛,称呼我的时候那双眼便亲切坦诚地望着我,没有骄矜与张狂,也没有卑琐与不安。我告诉来人,我不是什么大表姐,若真该做谁的表姐也排不到“大”的份儿上,我的上面还有几个姐姐,当然都已不在人世。对方很诚恳地说,因为从未有过往来,许多事他搞不清楚,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把一些该弄清楚的事弄清楚的,冒昧上门,实在是失礼之至,原本他是想写封信来,但三言两语又说不明白。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来了。
我这时才看见舜铨的炕头放了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初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舜铨正在看一本《美文》94年第10期杂志,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散文“太太与姨太太”。来人指着杂志说,他是读了我这篇文章才费尽周折找来的,我问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文中对谁有所冲撞,但我写的全是家事,与外人无干。来人说他姓李,叫李成志,小名福根,祖籍苏州,后移居吴江,又转张家港,现在在南方办着一个公司,从我的文章上来看,他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几辈人都在北方生长,若论婚嫁也都是长江以北,与江南素无指染,怎会有亲戚在南面,我也从来不曾做过谁的表姐。福根说,我料想表姐不明白其中原委,所以才把这本杂志带来,您的文章上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