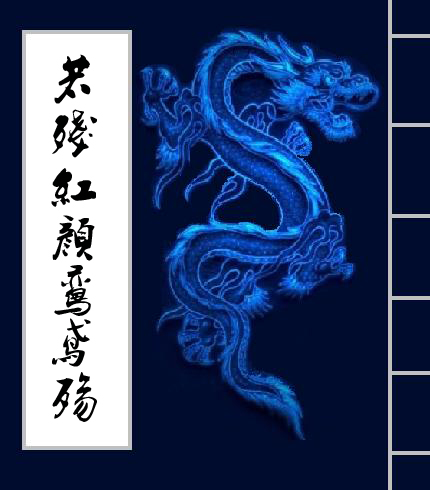花褪残红青杏小(完)-第9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手忙脚乱地按住包袱想堵住,他却跳起来:“翠环——翠环 ——”翠环带着奶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给孩子换了尿布,小家伙不满意,张着小嘴开始哭。
“夫人,这是饿了。”奶妈掀开包袱看了看他扁扁的小肚子。
“哦,你……帮帮我行吗?我想喂喂他。”我低声说着,奶妈见杨骋风没有动静,便上来帮忙,“夫人,你得先撩开衣服,然后再……”她说着,我正要撩起上衣,见杨骋风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便背过身去,“你看什么!”
“看你喂奶啊!”他说得理所当然。
“你看什么?!”
他嘻嘻笑着凑上来,“你是我的娘子,这是我的儿子,我看看不对吗?什么时候也好帮你一下。”
“你走开!”
“害羞了?你和我儿子都生了,还害什么羞!”
我的恶心又上来了,“你走开!”
他有些悻悻地往后面退了几步,嘟哝着:“脸皮真薄。”
我撩开衣服,照奶妈的指点小心地捧着孩子凑过来,小家伙吸了一阵,又哇哇地哭了,没吃着?
“奶妈!”我有些慌。
“不要紧,刚开始都这样,吃一阵儿就好了。常言道‘吃奶的劲儿’,夫人放心,这吃奶的劲儿最大。”
我拍拍他,把他的嘴凑过去,他又吸了一阵儿,我感觉这次他吃着了,小脖子一动一动的,看着真幸福,我满面笑意地看着他。
“小家伙还真能吃。”杨骋风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伸出一个头。
我又背过身去,“你看什么!”
“都孩子他妈了,还害羞。”
我不言语,把他推了出去,放下帐子,他又把头钻了进来,“娘子,那是我儿子呢,你让我看看吧!”
“要看等会儿喂饱了再看。”
他要发作,可又眉开眼笑的,“好好,你喂,我不惹你生气。”
小家伙吃着吃着似要睡着了,我对着他的脚心轻轻一弹,他立刻又开始吮了起来。我抿嘴一乐,小东西!真是神奇,人居然会造人,这小家伙是我生的!我沉浸在奇妙的幸福感之中。
“好了没,他还要吃多久?怎么这么能吃!”杨骋风的头又钻了进来。
我背对着他放下衣服,掀开帐子,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只剩下他和我了,我作势要下床。
“哎——你干吗?”
“下来溜达溜达。”
“坐月子哪有下来的!”
“顺产不能下来?是剖腹产不能吧?”
他歪着头看着我,有点儿傻乎乎地问:“什么是剖腹产?”我转了转眼珠子没说话,又缩了回去。
他凑了过来,“这小东西像我。你看这脸、这嘴、这鼻子都像我。眼睛像你,我觉得你的眼睛最好看,眉毛又黑又有光彩,睫毛长,软软地覆在眼睛上,让人觉得特别安静,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我轻轻地皱起眉头,他什么时候看我看得如此仔细?
“耳朵……”他抬头看了看我,“你的耳朵也好看,又圆又白的,就是不厚,还是我的好,让他像我的吧。”
杨骋风伸出自己的大手,拉起小家伙蜷着的小手,“手得像我吧,像你的话太小了,你的手指也短,不好看,
还是我的好。”他举起自己的大手,与小家伙的小手对比了一下,我扑哧一声笑了。
他也笑了,拍着小家伙,“快长吧,快长吧,小东西,长大了看着你娘,我也不怕她再欺负我了。”
我皱起眉头,谁欺负谁?
“我来抱吧,听说月子里的女人抱孩子容易胳膊疼。”他把孩子接过去小心地抱着。
“你得托着他的头。”
“怎么托?”我一招手,他靠了过来,“这样……”我给他比画了一下,“小孩子脖子软,不托着不行的。”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看看我,我点点头,他咯咯地笑了,“儿子,你爹爹抱着你了。哈哈哈……你是你爹抱着的第二个人,第一个人是你娘。”
我的脸色黯淡下来。
“娘子,咱们儿子的名字取好了。”他兴冲冲地说,“名钦宽,字越己,怎么样?是我撺掇老爷子取的,还不错吧?”
“哪几个字?”
“钦慕的钦,宽阔的宽,越过的越,自己的己。”
我思索着这个名字,不说话。他抱着孩子靠了过来,“王荆文公有一篇名文叫《原过》,娘子知道吧?”
王安石的《原过》,天有过乎,有之。地有过乎,有之。人介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孔子曰勿惮改过。
“人这一辈子,最难越过的,就是自己。”杨骋风悠悠地说,“要想幸福,就得把心放宽,把眼界放宽,越过自己,越过种种……”
我静静地听着,是,人这一辈子,最难越过的就是自己。
“我现在也觉得以前做错了。有了你,有了小越己,我觉得我有了家,觉得……这就是幸福。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的目光越过他,茫然地盯着墙壁——家?幸福?
他靠近我,“原谅我了吧?我们……重新开始?”
我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他一脸的诚意。原谅他?
忽然,我脑中蹿出一个念头,“这……是不是你早就想好的?”
他怔了怔,“娘子,我……”
“我问你是不是?”
他垂下了头。
“你是不是给我下了药,然后你……”我早就觉得奇怪,论日子,这孩子怎么都不像是我尽“娘子的义务”时的产物,我现在明白了到底为什么不对劲儿,“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用这个孩子来拴住我?”我绝望了,这辈子就要和他拴在一块儿了?我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娘子,我……”
“谁是你的娘子!”我吼了起来。
“好好好,不是,不是,你别哭。人说坐月子哭对眼睛不好的,你别生我的气,你心事重,老睡不好,什么人也不能那样熬着,我是让郎中开了点儿药……”
“你能不能别装?敢作敢当你也算个人!”我怎么就遇上了这种人!我希望他马上在我眼前消失,马上!
“你别哭,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了。”他有点儿慌了。
小孩儿哭了,冲淡了屋内紧张的气氛,杨骋风赶快掀开包袱,尿布上有一小团黑色的胎粪。他又要叫翠环,我却扬扬手,“把那块尿布拿来!”在他惊讶的目光中,我拎着孩子的小腿儿往上一提,抽出脏尿布,另一只手换上干净的尿布铺好。
“这……拎不坏?不会脱臼?”
“不会,都这么换的。”前世我家有两个小外甥,我不知换了多少次尿布。
重新包好,小越己不哭了。越己,我也觉得很好听。是的,人这一辈子,最难越过的就是自己,希望他能越过自己吧。
作者有话要说:鸡同鸭讲的日子又开始了,锉锵……
继续聊天啊。现在正值答辩时间,想起那年听来的某位同学和其导师的趣事,贴在这里。
该同学去华宇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售货员突然跑过来,说:你给我签个名吧。
他很纳闷。
售货员:我知道你是明星,你不就是演《天下无贼》的那个吗?
他更纳闷:我不是刘德华啊?
售货员:不是,是那个农民,叫什么强来着?
他巨汗,心里嘀咕原来是傻根。
于是,他便有了名字,“三多”。
三多的导师从香港回来,盯着他看了半天,说:你还不是特别像傻根。
三多心里暗自高兴,终于不像那家伙了。
他导师补充道:你比傻根还丑。
他彻底崩溃。
导师开同门会。强调了他们开题的事。
三多blabla 阐述了自己的论文内容,是关于股指期货跨境监管的。
说完了,导师默不做声。
然后问旁边三多的师弟师妹:你们听懂了吗?
答:没听懂。
导师:我也没听懂。
转头又问三多:你是不是不想毕业了?
三多:想。
导师:那就是想延期了?
三多:老师,我也不想延期毕业。
导师:我也不想。——你再多呆一天我都忍受不了了。
众人大笑。
这个导师很有意思。
第七十章 角斗(一)
越己是个能闹腾的孩子,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喂奶迟了一点儿就要哭,闹得我白天晚上都不能睡。
杨骋风常常半夜被他吵醒,然后皱起眉头捏他的小手,“小家伙,这么能闹腾,像谁?”像你!我心想,一点儿都不省事!
“娘子,小家伙太能闹了,要不要送到奶妈那里去?我看你也瘦了很多。”
还不是你让我吃虾吃的!再说喂孩子哪有不累的。我不语,只静静地抱着越己哄着,他在旁边看着,有时嘿嘿地笑,“娘子,你对越己真是好,你对他好,我就高兴。”越己是我儿子,对他好,不是因为你。
有了孩子的日子过得更快了,虽然很累,但看着小越己一天天地长大,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常常对着他的小鼻子小眼睛,一看就是半天。看多了,甚至觉得大人的脸太大,很丑。
越己要百岁了,头一天晚上两人上了床,杨骋风说:“明天,你去吧,衣服我让人做了。”
“不去。”
“去吧,有很多人,让他们见见你。”
“不去。”
“去吧。我让人接了我爹娘,你去拜个安?”我不吭气,他叹了一声,各自无言。
杨骋风请了很多人,我在屋子里都听得见吵闹声。真不嫌累,反正我不去!杨骋风打发人把孩子抱到前面,大家看了一阵儿,又打发人送了回来。
“娘子,我爹娘给了越己一个项圈,人说这是长命锁,来,给他戴上!”等外面安静了一些,杨骋风一身喜气地进来了。
我见越己正睡着,“等等吧,孩子睡觉金贵,什么时候不能戴。”
他凑上去看看,轻轻地点了点越己的脸,“小家伙,娘疼你,爹也疼你,爹也疼娘,你要快点儿长大。”
我板着脸不说话。
杨骋风凑了过来,“听奶妈说孩子要哭一百天,起初我不信,果然,现在真不哭了。小家伙,可折腾死你娘喽。”他抱起了越己,越己又抓紧时间哭了起来。
“哟哟,刚说你不哭,却又哭了起来,你还真长脸啊。”杨骋风也学我一边拍着孩子一边说,“阿公阿婆来了,你要是会说话,就要你娘给阿公阿婆晨昏定省去。”
我转过身去,别变着法子敲杠子给我听,嫌吵!
他俯下身看了一阵儿越己,又直起腰来,“司杏,爹和娘今天问起你了,他们说,你……”
我冷冷地说:“杨家的所有人和我无关,我只是越己的娘。”
“司杏,别倔了,越己姓杨,你能和他无关吗?”
我被他堵得接不上话来,硬撑着说:“我只和越己有关。”
“司杏,”他走了过来,“你都是越己的娘了,我是越己的爹,再不对,气儿也该消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再说你和我分得这么清楚,但看着越己,你和他分得清吗?只要和他分不清,你和杨家就分不清。都已经是杨家的人了,干吗非要闹别扭!”
我冷冷地说:“我只是越己的娘,其他人和我无关。你杨少爷的光,我也不想沾。杨少爷要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闹别扭,那我就再说一遍——我还没学会和绑架我的人相敬如宾,我没有你所谓的涵养和廉耻!”说完,我抱着越己一转身,便再也不开口了。
越己戴着项圈,胖嘟嘟的,像个童子,我常常一抱着他就是半天。杨家的老主人在这儿住了半个多月,但我始终没去见。杨骋风总是一个人去晨昏定省,我仍旧遵循自己的作息习惯,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己每天由青琏或翠环抱过去看看,然后再抱着送回来。
这天,翠环抱着越己回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事?”
“夫人,奴婢说了您别怪罪。今儿老夫人提起你了,问你天天在做什么,奴婢不敢直说,只好说夫人生产后月子没坐好,老觉得困乏,在屋里歇着。老夫人就说:‘要是这么着,是不是我得去看看她?’”
我不动声色地听着,“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