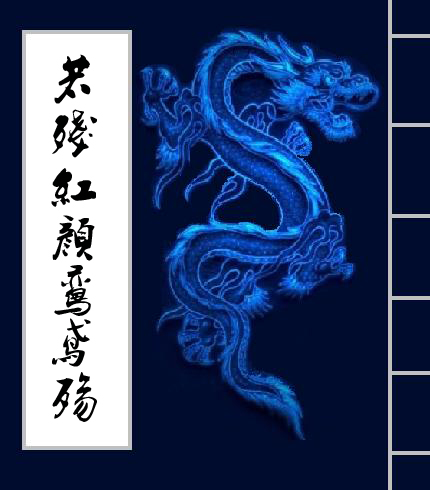花褪残红青杏小(完)-第1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知再说什么,只把银子包好又放回他的面前,“还是你拿着吧,我在府里,吃穿都是人家的,要钱做什么。你拿着,万一家里不方便,也凑凑,不至于受了窘。”
萧靖江又推了回来,“不用,我一个男儿,以在外面,不行了总还有别的办法可想,你一个在府里的丫环,真到难了,叫天都难应。”
小包在我们之间推来推去,我急了,“你快拿着,再等二娘就回来了,看着我们这样,还以为怎么了呢。你若真有心,以后来看看我,真发了迹,帮我赎个身,也算是你做件彻底的善事了。”
萧靖江愣了愣,默默把小包放回怀里,两眼望着我,我突然有一个念头,“萧公子,你那里可寄得书信否?”
“书信?寄得呀,你忘了,我爹爹还是衙役呢。只是你怎么寄?”
“好,你快把驿站名告诉我,只要有可能,我就想办法给你写信。”萧靖江报了,我一遍一遍的在心里默念着,唯恐忘了,这时李二娘进来了,我们又扯了几句闲话,萧靖江便起身告辞,李二娘千不舍万不舍的送了他,我跟在后面,悄悄的对着萧靖江做笑脸,做了个写字的动作,他也向我眨眨眼睛,我和二娘站在风里,一直看着他走得没有了,才回转。
“唉,走了。”二娘伤感的说,“我进府这么多年,还没人来看过我呢,头一回。”我心里的滋味并不比二娘好受,难为他还记得我,萧靖江怕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还在关心我的人吧。我在心里悄悄的默念着他的邮驿地址回到了琅声苑。
君闻书并没有问我去做什么了,也许他认为我既是二娘的下手,便也不用问了吧。我一回书库就把萧靖江的地址抄了下来,压在我工作台上那堆纸的最下面,我能给萧靖江写信了!
要写信,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我怎么寄,二是我如何收,三是毛笔字。前两个问题我一筹莫展,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机缘既不凑巧,也只好罢了。但第三个问题,我还是很努力的进行——糊弄君闻书,差不多就行了,但给萧靖江写信,我不希望他会笑我,我也想用毛笔好好写个字,给他留个好印象呢,于是,我放弃了看书,抓紧时间练字。宋朝的印刷术虽已很发达,但手抄本的书还是不少,尤其是名家的集子,各自的字体还是保留的,我也不用找什么字贴了,直接拿一个我看着对眼的练了起来。
我每天除了做事,就是头也不抬的练字,以至于君闻书进来我都未曾发觉。但给君闻书抄书,我仍然还是用幸笔,并且尽量快速抄完,有几次还因过于潦草而挨了他的说。私下里,我瞅着机会问侍槐有没有办法帮我寄信收信,侍槐想了想说:“办法倒也不是没有,但你要寄一封可,若长期寄,恐怕就会被少爷知觉”。原来他是想混在君府要寄的信中,偷偷的帮我寄。至于收信,侍槐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信有时是府里的仆役直接送来的,万一直接落入君闻书手中就完了。宋代不似现代邮政那么发达,要寄信,不是派专人送,就是走驿站,只是官员走驿邮,而商人走驿驴。萧靖江他爹只是个衙役,收信当不成问题,但要寄信,也不能太频繁,君家寄信走的是商人用的驿驴,数量不成问题, 但只能送到君家,不能送到我手里。我没有办法了,但我还是加紧练字,也许会有转机呢。
我对工作越来越熟悉了,并把书架按格编号,将所收之已编上目录,君闻书也逐渐熟悉了我放书的规律,有时我不在,他自己便去翻目录,按图所骥,估计没遇到什么问题,至少从来没因此训我什么。我的闲时间越来越多,无事的时候,我便跟锄桑他们几个乱扯,三个小毛头很快就对我臣服,尊称我为老大。对此侍槐很不服,可他有事无事都要跟着君闻书,平日又一副军事秘密不可泄露的样子,府里的事也不和我们说,于是,在三个小毛头的心里,我老大的地位越发稳固起来。有一天,我实在无聊,便动员他们三个打马球。马球我只在小时候见到人家打过,跟我们现在的高尔夫差不多,只是不似高尔夫需高低不平的地势,而只要平地,地上设又矮很窄的门,球杆也与高尔夫球杆类似,将球射入球门者为胜。我选择马球也是有原因的:马球和现代的高尔夫一样,比较静,不像别的活动容易忘情的大叫,只要避开君闻书的眼睛,再不出声,我们就是安全的。起初锄桑他们不肯打,怕起了喧哗被君闻书发现,几经我动员,并施之以老大的威风,终于少年心性压倒了对君闻书的恐惧,决定先试试。琅声苑地方大,平地多,我们在正房的后面插了几个木棍钉的门,便装模作样的打了起来。我们这些土包子,谁都没有打过马球,纯粹瞎打一气,谁要瞎猫碰着死耗子的射个球进去,都要跳着高庆幸老半天,根本谈不上什么球技,但在这死气沉沉的君府,我们能自由的跑动,自由的压低噪子笑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忘掉我们为奴的身份,好像我们只是人,一群少年人,生活在明媚的蓝天下。
侍槐起先对我们的活动很不屑一顾,我断定他中君家的毒太深,我老觉得君家有一种衰腐之气,人在里面压抑的很,不敢说话,不敢笑,我所见的每个主人都阴沉沉的,就连那十岁出头的君闻书也整日如老头子,我讨厌这样的日子。经不住我们的劝诱,侍槐打了几杆,便成了我们的同僚,只是他得空的时候不多,不似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事,应应卯,便可以打一阵儿,每日总有些可以觉得快乐的时光,日子过的终于有些滋味了,在我来到君家将要第三个年头的时候。
就这样,日子尽了,我一直没能给萧靖江写成信,冬天眨眼就要到了,真快呢,我依然没找到能给萧靖江寄信的办法,想想,我和引兰、特别是听荷也有两年没见了,不知她们都可好?我问过侍槐,他说君府大,三个园子隔的远,又分了炊,无事君闻书也不让他去停霞、澧歌,君闻书又整天窝在书房,他对府里的事也隔膜的很,只是听说二小姐的婚期就在明年春天,至于引兰和听荷,他也没什么消息。
冬意迟迟中,有时我坐在斗室中胡思乱想,君府就像一个大死潭,而君闻书,更是在这个死潭闭上门过日子,这家人,真看不透,难道我就要在这如死潭的地方生活一辈子?又要过年了,我又要长一岁了,我的将来又是如何呢? 有时我笑我自己,上一世觉得路难行,为了逃避而梦想喝孟婆汤重新来过,真到了这一世,困难如当前,依然觉得坏,觉得没有出路,那么,怎么样才是我所谓的“好”呢?环视周遭,胜我的人当然有很多,但似我的也不少,大家都能好好的活下去,为什么独独我,总觉得对生活不满呢?
冬月初十,一场大雪,整个琅声苑都是白的,瘦削的竹叶上盈满了雪,倒显的胖了,太湖石也圆乎乎的,落光叶子的槭树仍然直挺着,在澈骨的风中,迎着湛蓝的天。活着真好啊,我一脸笑容的进了书房。
君闻书今天着了一件湖青色的毛领缎面背心,里头是淡青色云纹的丝棉袍,乌发上只别着白玉簪,他的小乌龟依然忠实的趴在他下摆的右侧,猛的一看,嗬,还真有几分公子的样子,也是,这孩子,过了年就十五了,按照宋朝的习俗,该准备论亲了。
“少爷早”,我行了一礼。
“唔,”他抬眼望了我一下,“你今天笑的格外开心,甚事这么高兴?”
切,你这木头,哪里懂得本姑娘的彻悟,又哪里能领略到这世间的大好风光。我一摆头,“没有,只是天气好,心情就好罢了。”
“哦?”他又注意的看了一我眼,“今天林先生来,莫要忘了多准备些干果,还有林先生喜欢的白毫。”
我应了一声,便去做了准备。
林老头儿来了,他们又在书房里低谈阔论,我无聊,便坐在窗前看锄桑他们扫雪。雪很厚,年纪最小的栽桐面前的那一堆垒得都快有他高了,嘻嘻,我有主意了。瞅了个空儿,我过去,“少爷,外面雪大,不早点扫恐怕化了院子里泥泞,我去帮帮锄桑他们吧。”
君闻书转过头来,静静的说,“院子里的事有锄桑几个小厮就行了,你一个丫环,去做什么?还是在屋里吧。”
我瘪了瘪嘴,死板板的君闻书,男啊女啊,就知道这个,你哪儿知道外面有多么好玩,你非要去,于是我眼珠儿一转,立刻又说:“少爷说的是,前几天刚下过雪,这次雪下的大,倒是干净的,不如去把竹叶儿上的雪拂下来,留着化水也好泡茶喝。”
林先生是个茶迷,听了我的话便说:“竹子本来就清,雪水泡茶,倒合着茶的意思了。”大约我从来没这么勤快,也从来没做过这等细事,君闻书狐疑的看了看我,碍了林先生的话,也就同意了,只让我小心,别摔着。
我一个高儿蹿出了正房,哈哈,上当了吧君闻书。我得意的抱着瓮出现在看榆的面前,跟他咬了阵耳朵,看榆点头。锄桑一边干活,一边往这边儿看,我扫了几把雪,慢慢的又溜达向他,向他咬了阵耳朵,锄桑也笑了,提着扫把往栽桐那边去,不一会儿,栽桐先胆怯的看了看正房,然后露出小白牙。
院里逐渐又露出地面,我三下五除二的往翁里扫满了雪,送到厢房。勒了勒束腰布,紧了紧鞋子,几步就到了正房的后面,三个小毛头早已集合完毕,眼前一个大雪堆。我一甩头,四个人不约而同的开始扒雪、滚雪,做起了雪人。看榆非要给雪人的身上贴满竹叶子,说是当衣服,锄桑鬼头多,折了几棵扫帚枝插在雪人的鼻下当胡子,栽桐傻乎乎的笑着,一会儿却在雪人的下面抠出两只胖乎乎的脚来。晴朗的雪、滑稽的雪人使我们的心情大好,我兜了看榆一头雪,锄桑却跟上来塞了我一脖子,四个人似衔了枚的士兵,裂着嘴却不出笑声的打起来了雪仗,雪地里全是我们踏的印子,每个人都挨了个无数个雪球,摔了无数跤,一身的雪泥还乐哈哈的不觉疲倦。
正玩的起劲,忽听侍槐高声叫道:“司杏,司杏,你在哪里,少爷叫你。”我一惊,该死的君闻书,非要在我玩的最起劲的时候找事儿,我忿忿不平应了声,小跑着回到书房。
“少爷,”君闻书正和林先生说话,闻声便转过头来,张嘴欲语却愣在那里不出声。“少爷,”我又叫了一声。
“你怎么这幅样子?”他皱着眉头。
“怎么了?”我低头看看,呀,我的胸前因“中弹”太多,已经全湿了,前襟、袖口和膝盖因为匍匐频繁,也早就沾满了泥,最妙的是我的鞋子,已经辨不出颜色了,鞋底还沾满了厚厚的泥,往那儿一站,两个大泥印子向四周泅了开来。
“呃,少爷,这个,刚才没站稳,摔了几跤。”
“翁可破?”
“没有,”我赶紧说,“已经装满了雪,放到厢房了。”
“唔,你摔了这多跤翁尚未破,是这翁太结实了还是你太会摔了呢?”君闻书盯着我。
死乌龟,我愤愤的骂了句,却不知怎么回答。“这个……”。
“今儿你这么勤快的去拂雪,我便觉得奇怪。你到底做什么了?”君闻书愈加逼问过来。
“这个……。”
“侍槐,把锄桑几个给我叫来。”君闻书冷冷的吩咐道。
“哎哎,少爷,您别怪他们几个,我们只是玩了一会儿。”我是老大,主意是我出的,怎么好让他们受连累?
“玩了一会儿?”他又倚向后面,“玩的什么?”
“没有什么,”我嗫嚅着,盘算着这顿训肯定是挨不过去了,“我们只是见雪好,一时兴起,在后面推了个雪人。”
“还有呢?”
“玩了会儿雪仗。”
“哦,还玩雪仗呢,一个女孩儿家和几个小厮,疯疯癫癫的成何体统?”君闻书厉声道。
呸,乌龟,你自己不玩,还不准人家玩?还什么体统,老古板!我心里想着,脸上却不敢露出来。
我正寻思着如何对答,另一个老古板林先生在一旁发话了,“少爷,今日雪景正好,他们几人少年心性,玩玩倒也不失大道。老朽以为,少爷也不要太在意。少爷与我座谈时间太久,不妨出房门看看天地。”哟,这林先生为我说话?我极为诧异,感激的望了他一眼,没想到,他正在拈须微笑看着我,他在笑,他居然会笑?!
“也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