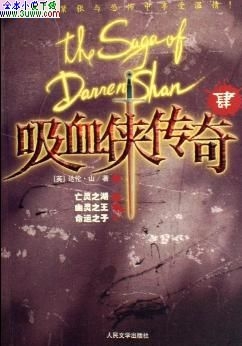阎锡山传-第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逢源”的游戏。形势的发展,不断给阎锡山桌面上的表演以沉重的打击,却又使心怀叵测的阎锡山窃喜不已。反袁气势日益高涨,宣布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北方省份也纷纷宣布独立,到陕西也宣告独立之时,袁世凯大势崩溃,手中已经没有了可用之兵。帝制被迫取消,但袁世凯仍想霸占总统的位子,又指使段琪瑞在南京召开各省督军联席会议,以寻找苟延残喘的办法。阎锡山指使他的代表,赞同以袁世凯退居总统的办法,由袁继续把持国政。众叛亲离的形势之下,阎锡山的这种态度,深得袁世凯的赞赏。于是,在走投无路、捉襟见肘之际,他要阎锡山派兵到郑州,防备陕西的军队向河南进攻,还想用这个部下的忠诚抵挡一时。阎锡山接到出师郑州的电令,立即表示服从。但又说山西贫瘠,筹措军费困难,求袁世凯接济。袁信以为真,一口承诺,并随即拨发军费80万元,作为开拨所需。阎锡山也迅速行动,在娘子关集结兵力,派员领到粮饷之后,就以兵力一部进驻石家庄。袁世凯越发相信阎锡山此时是真心真意在拥戴自己,因而对拨付军资军械的要求满口答应。阎锡山的部队得到堆积如山的物资,从容装备,并不急于南下郑州。频频以军资尚缺请求拨付为由,继续拖延时日。军资军品堆积如山,又缺车装载,就请京津拨车备用。直到无法再拖延了,装载重兵的列车于深夜开行,但车并未开往郑州,却是向着北边背道而驰。车离郑州越来越远之时,阎锡山给袁世凯发电报称:“我军北驶,已抵保定。”袁世凯接到这封电报,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这个“脑后没有反骨”的部下戏弄了一场。措手不及而悔恨已晚,从此病沉难起。有人说阎锡山的这场戏和这封电报是袁世凯的催命符,也许并不夸张。阎锡山自己,在对袁世凯作了这一番嘲弄式的报复后,心满意足地微微而笑。这个曾让他坐立不安的袁世凯,终于也有被他玩弄的一天。最后这一着,不仅吐了一口多年来沉重郁闷的恶气,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大批军资物资。
对于阎锡山媚袁的这一段经历,国民党内始终有一部分人耿耿于怀,斥之为“叛变革命”。阎锡山本人恐怕也感到不甚光彩。在他的回忆录中,极力予以粉饰辩解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示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攻之者认为事实铁定,辩之者苦心编织言词。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自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历史的事实是:阎锡山确实是对袁世凯一身媚相;阎锡山的地盘和力量也确实是保存下来了。不过,从中倒是可以看出,能够在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眼前瞒天过海,显示阎锡山善于韬光养晦的手段此时已经相当成熟,而他那“存在第一”的哲学想必也经历了一次成功的喜悦。
拥段倒黎,反对护法,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阎锡山以他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才能,早在竭力奉迎袁世凯的同时,就已经将投靠段琪瑞作为通向袁世凯的一条捷径。段琪瑞好为人师,阎锡山就投其所好,在1912年,到北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首先具了门生帖子,拜见段琪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从此自称为段的学生。在段的面前,表现得谦逊稳重,颇得段的好感。段琪瑞确实也在袁世凯的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现在段琪瑞在中央政府掌了大权,阎锡山自然更是趋炎附势,同时,自己的腰杆子也就硬了起来。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他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对于山西的军政大事,不闻不问,以示没有野心。袁世凯一死,他就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处境了。他先是赶走了袁世凯派到山西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接着就准备收回先前放弃的军权,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时任山西军政司司长、督军府参谋长、混成旅旅长的黄国梁。
这时,也有人想要利用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这个变化来对付他。这就是投靠山西的吴禄贞的部下孔庚。孔庚投靠山西后,也曾为阎锡山出过大力,长期坐镇包头,治理地方有方,名震塞北。袁世凯曾当面嘉奖过他,而他与副总统黎元洪又是老乡,来往密切,并将不少同乡旧部,安插在部队中,因此引起阎锡山的莫大疑忌。阎曾暗中操纵孔的部下发动“兵变”,企图将孔杀害,但孔因此时不在自己办公室而侥幸躲过。后来,在袁世凯称帝时,孔庚秘密进行过反袁活动,更为阎锡山所不容。阎曾一度撤掉孔的职务,将其软禁在太原。孔庚这时就和黄国梁勾结起来,密谋将阎锡山取而代之。由于袁世凯时代强行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只剩下黄国梁所部的一个旅。袁死后,黄国梁就着手扩军。他大批训练军队的基层干部,又挪用军费修建营盘。他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一个旅扩充为一个师。计划拟得非常周密详尽,只剩下将师长的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在黄国梁看来,与阎锡山的关系非同寻常。既是早年的拜把子弟兄,又从太原起义以来一直亲密共事,还在袁世凯的监视下替阎锡山担惊受怕地顶了几年门户。艰险过去,现在得到发展的机会了,军队扩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个师长还有什么过分之处吗?却不料,计划送到阎锡山处,阎看过后勃然大怒,将计划扔在地上,拍着桌子大骂:“绍斋也太不把蒙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蒙作傀儡?一点小事,他都不听蒙的,难道蒙就那么听话!”素日积累的矛盾找着了爆发的导火索,早已成竹在胸的图谋得到了实现的时机。阎锡山逮着了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他既不看拜把子弟兄的面子,也不理采长期共事的交情,表现出一副震怒的模样,立刻把秘书长召来,拟了一份电报,拍发给北京黎元洪总统和段琪瑞国务总理。电文声称“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请北京政府撤销黄的职务。当然,不用等北京政府的批复,他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狠下毒手的行动。他怒气冲冲地把宪兵司令找来,亲手写了一道手谕:“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当面命令宪兵司令派兵包围黄的住所,禁止黄与外界任何人见面,监视黄于次日早晨离开太原。宪兵司令虽然曾是黄的好友,此时也不得不绝情相逼。黄国梁被迫郁郁寡欢地离去,临行感慨良多:因为原来的山西军政司长、阎锡山的另一位好同学,太原起义后曾任副都督的温寿泉,是黄国梁在阎锡山的授意下逼走的。性格爽直的黄国梁,虽然是阎锡山患难与共的把兄弟,却难与阎锡山同行一路。
对于时任晋北镇守使的孔庚,阎锡山也毫不客气,让亲信张树帜趁孔进京不在大同期间,带兵闯入镇守使署监印室,将镇守使关防抢走。孔庚知道是阎指使所为,只得忍气吞声,乖乖地将镇守使职务交与张树帜,离开了山西。
这年7月,阎锡山应邀进京面见黎元洪,回到住处,哈哈大笑着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他看不起黎元洪,这一次却差点遭了黎元洪暗算。次日晚,段琪瑞派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去密谈了很久。原来,孔庚、黄国梁被迫离开太原后,并不死心,再三鼓动黎元洪采取“调虎离山计”,把阎锡山调到北京,而后孔庚、黄国梁秘密回到太原,由黎元洪出面明令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北京,措手不及,鞭长莫及,到时候也只能认命,他的这个老窝就给端掉了。段琪瑞得到了这个消息,为拉拢地方实力派,以念师生之谊为由,迅速把消息透露给了阎锡山,并面授机宜:即日化装离开北京,间道转回太原。只要能先他们一步回到太原,控制局势,黎元洪就不敢动手。老谋深算的段琪瑞替阎锡山筹划一番,想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京汉路车离开北京,为避开耳目,不要在石家庄转车。南下直到河南新乡,换坐车到清化,翻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回太原。
这消息,对阎锡山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轻而易举地挤走了黄国梁和孔庚,却又差点被他俩暗算。看不起黎元洪,却险入黎的陷阱。在对段琪瑞感激涕零的同时,也对黎元洪他们恼恨不已。阎锡山经历过几次突如其来的风险了,这一次就老练得多。经过考虑,他不肯照段琪瑞的计划,绕个大弯子,那样既费时间又多变数,决定还是坐京汉线的车到石家庄转太原。为了保密,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对部下交代说:“蒙想还是坐京汉车从石家庄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不过,蒙不能从车站上车,免得引起他们注意。”他吩咐部下用400块大洋买通火车司机和扬旗手,将火车开离站台到扬旗地方时,尽量开慢些,让他能够从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上车。而后又说:“只要蒙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蒙走了以后,你们几个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就推说蒙病了。他们要是派人来看望,你们就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是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接到蒙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就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次日,阎锡山浑身商人打扮,穿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沿压到眉头,再戴上一副大墨晶眼镜,未经车站站台而从车站扬旗处神神密密地离开了北京。与当年仓皇逃离太原时相比,阎锡山此时已经镇定得多了。这一方面是他人生阅历的增长,对意外和惊险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和对应力;另一方面,他在山西的基础已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任意动摇的。他敢于胸有成竹地与黎元洪玩这个乔装潜行的游戏,也显示出他的自信。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阎锡山格外感激段琪瑞,也更重视与段琪瑞的“师生”关系。从此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北洋军阀各派系混战中,他总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段琪瑞。他还多次向段琪瑞表示,愿以山西的武力作段的后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琪瑞为首的国务院,受其各自的后台的怂恿,围绕所谓“参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段琪瑞以对德参战为名,准备向日本大量借款,扩充武力,以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图谋;美国为了与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则支持黎元洪联合直系军阀进行抵制,人称“府院之争”。在这场争权夺利的争斗中,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琪瑞一边。阎锡山拥护段的“参战案”,在其案未获国会通过后,阎锡山马上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当段琪瑞被免去国务院总理之职,出走天津时,阎锡山又宣布山西“独立”,脱离北京中央政府。黎以总统身分下令将段免职后,段则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准备用武力将黎推翻。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就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进京,与康有为等人密谋后,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段琪瑞利用全国上下反复辟的情绪,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阎锡山立即响应,通电反对复辟,并派兵北上,声援和支持段琪瑞。段琪瑞再次控制中央大权之后,大力支持阎锡山扩编军队,壮大势力。山西的军队由原来的一个混成旅,扩充为四个。一下子增长了好几倍。
段琪瑞重掌中央大权之后,拒不恢复张勋复辟时废弃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并以参加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借巨款出卖国家利权。孙中山先生视《临时约法》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不能容忍段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