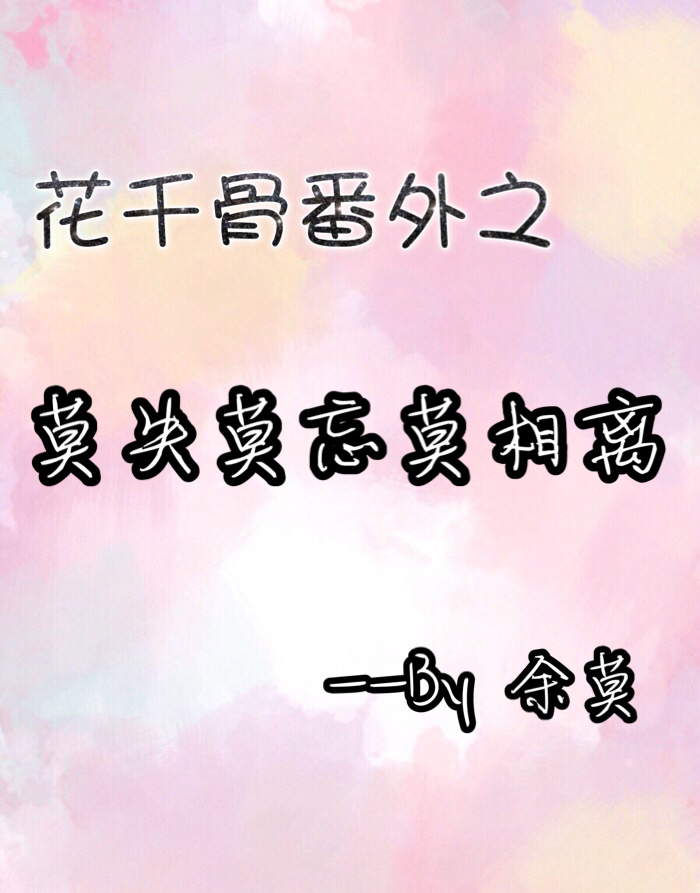莫失莫忘-第1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起来发生了什么事了,我送流川回森林,已经到了森林边,刹车忽然失灵,车子冲出路基,然后我就失去知觉。
病房内温度适中,可冷汗浸湿我的了衣衫。
一个月前,才在车行全面检修保养过汽车,现在刹车却完全崩断。
不,我不相信这是意外事件。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银都,Scully说他们除有上层路线外,尚有黑社会背景。这不是一个意外,根本就是他们想置我于死地!
我以为我只是在依循一个建筑设计师应有的职业道德,最多不过让银都集团少赚一些而已,并不会让他们动摇根本。始终还是太天真,如果没有这样费尽心机的敛财,又怎会在短短时间内扩张如此迅速?又或者根本每个财团都是如此起家。
早就该想到,敢在地质断裂带上建一座地下商场,仙道彰一条小命又何足道哉!
是我自己估计错误,还自以为宽大为怀,妄想给别人七天时间,岂知别人连生路都不愿给我,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怨不得别人,还好命硬,车子从路基上冲出去居然没事。
等等,脑海中铮的一声响裂石穿云。我猛然从病床上翻身坐起。
流川!
我没事,但是流川呢?小狐狸呢?
出事时他和我一起在车上!
雪白墙壁无辜地包围我,世界没有一点色彩,令人窒息。
病房门开了,进来一位护士,我跳起来捉住她。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手指不停发抖,不,全身都在不停颤抖,流川流川流川呢?我压不住心里的恐惧,一条胳脯抬不起来,我只能用一只手紧紧捉住她的衣袖。
我牢牢望住她,满眼的话,却组不成语言。
流川流川流川,流川他现在怎么样?
“好了好了没事了,别紧张,已经没事了,快躺下,别回血了。”
护士职业性地安抚着我试图让我镇静重新回到病床躺下,她以为我尚在为发生的事后怕。
我是怕,怕得混身僵硬,捉住她衣袖的手指指节痉挛。声带仿佛被冻结般不能出声。我对自己说,镇静,镇静,仙道彰,你要镇静。
“和我同车的人在哪儿?”我用尽全身力气开口。
冲出医院,我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一定狼狈极了,但我顾不上。
护士说,她不知道和我同车的是谁,但是昨天送我进医院的是我学弟。
护士说,据说是我学弟把我从车中救出来,然后步行许久挡到运砂石的车送我进医院。
并且,她还说:“送你进手术室他就先走了,仙道先生,最好让你学弟也来医院检查一下,我看他脸色很不好呢。”
大街上没有遮挡的阳光直射下来,刺得我眼睛痛,痛得快要流下泪。
是小狐狸。
流川没有对医院说去哪儿,但我知道,都市里只有一个地方可容他栖身。
天气很好,人群来来往往。这个城市没有战争的威胁,没有什么天灾人祸,超市里挤满了疯狂购物的人群,也有旅人提着行李东张西望,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歌舞升平,一派祥和。
可是流川,世界这么大,却容不下我和你。
终究是我连累了你。
出租车司机在我的驱使下,着了魔一样疯狂行驶。
恐惧如同潮水,越涨越高,快要将我整个人淹没。
如果我受了伤,流川不会一点事也没有;如果流川没有受伤,他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医院;如果银都决心置我于死地,不会就这么轻易罢手;如果被人发现他真身是一只狐狸……
我不敢想下去,每一个如果都让我心惊胆颤。
以前越野喝得酩酊大醉后曾经对我说,“仙道,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原来那是个不能相信的谎言。”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越野流泪,他哭得象个孩子似的不能自抑。当时他们警局才破了一起大案。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也无须问。
是,遍体鳞伤的不只我一个,我所需要的是尽快谙熟所有规则,学会不再相信谎言,学会让心脏变得麻木并且失去痛感。
我以为已经成功了,然而这一刻我知道差得太远。
流川倒在客厅里,分开虚披在身上的外衣,衬衣上已半干涸的暗红色刀般割入眼帘。
“流川!流川!”
我拍打他的脸,试图抱起他,但是木疼的胳膊使不上一点力气。不只胳膊,全身都没力气,甚至无法直起腰来。
微弱急促的气息喷在我手上,如火焰灼伤着我的肌肤,一寸寸将它烧裂。
“流川醒醒,……,流川你醒醒,小狐狸……”
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揽住他让他半靠在我怀里,一遍遍叫。
怎么办,应当怎么办?
千百个念头在我脑海刮着暴风,它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可最终没有一个能被我清晰捕捉。
送他去医院?可他是一只狐狸,如果被人发现他是一只会幻成人形的狐狸……,我闭上眼,绝望地想,不行,绝对不行,如果被发现真相,他们不会放过他,他们会研究他,用尽一切手段与仪器。
对于冷静理智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流川枫,一只狐狸怎么可能需要这样的名字,准确叫法,代码01号,或者011号711号等等。
那么送他回森林?可是,我试着抬了抬胳膊,根本动不了。
慢慢镇定下来。对了,伤口,不论如何,要先处理流川的伤口。
我咬咬牙,放下流川,努力站起,摇摇晃晃往书房走,以前的女朋友里,曾有过做护士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个简易药箱并未扔掉,我的运气一向好,这回也不应当太差。
小心揭开流川衣服,俯下身,我面无表情仔细看他的伤口。
一道血痕从右肩向后背斜斜划下,很明显的外伤,大概是被撞碎的车玻璃划伤的,但明显的血迹并不多。判断不出是否还有内伤,即使有,此刻我也无能为力。
流川的手心与脚底也有很多伤痕,有的地方已变得血糊糊一片,分别被很粗糙的砂石地磨砺过。护士告诉我,是我的学弟把我从车中救出来,然后步行了将近五公里,终于挡到运砂石的车送我进医院。
车翻下去的那一带是高速公路通车后不再使用的废旧路,路况极差,并且,我冷静推测,流川要想用最快速度找到车辆,最好办法恢复原形奔跑。
轻轻撩开他额前刘海,左侧头部有个宽而深的伤口,头发被血粘住,结成一大片褐色。
我返身从茶几上拿起镊子夹住药棉,酒精跟伤口接触时,流川痛得猛一缩,我停下手,屏住呼吸,长长的眼睫似乎略略颤动,流川睁开了眼,开始迷茫,但很快清醒过来。
看清是我后,他迅速打量我,全身安然无恙,他的眼睛亮起来,寒冷漆黑晚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流川……”我笑,努力放松面部表情温柔微笑,“别怕别怕,有点伤口要处理一下。”我微笑着说,“可能会有些痛,但是你一定会忍住是吧?要哭了我可是会笑话你一辈子。”
光亮暗下来,他看我,盯着我看。
我掉开眼睛,保持微笑,继续专心关注那个伤口。
流川,我知道我笑的很难看,可是不要这样看着我。
(十四)
没有力气把流川抱进房间,只好让他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我跪在他身边,药棉蘸着酒精一下下往他伤口上拭去,流川安静合住眼,不动也不说话。
胳膊垂在身侧,两只手握得很紧,十指牢牢攫在掌心。清洁伤口时,全身会很细微的紧绷,不易察觉的细微的发抖。额上有细密冷汗一层层渗出。
终于,额头的伤口全部清理干净。我站起来,试着活动一下,全身肌肉与骨节都是僵硬的,生了锈的机器人,稍动一下便会咯喇喇响,神经仿佛也失了灵,到处都有迟钝的痛,但我说不清到底痛在哪里。
怀疑很快就会象我那辆车一般,不送去大修次指不定哪天什么重要部门猛然失灵。不过不要紧,哪怕太阳升起后阳光下它就要融化,可只要它今夜还能用就不要紧,只要现在我还能抱得住流川就不要紧。
我柔声对流川说,“小狐狸,现在抱你上沙发趴着,背上还有伤口要处理。”
他迷迷糊糊睁眼,眼睛不再明亮,狭长乌黑的眼里没有焦点,全是疲惫和疼痛。
我看着他的眼睛,还有额上细密的汗珠,忽然再也不能忍受,再也不能微笑,我扯开他双手,近乎粗鲁地掰开他手指,一把甩到背后示意他抱紧我,迅速站起带动他安稳落上沙发俯在我怀里,我听到自己声音,郁闷嘶哑如同困兽,“手上明明有伤还要这样握住?伤口会更糟这你都不懂吗?!”
“嘶啦”一声彻底撕开他背上衣服,准备好的毛巾敷上去,湿热毛巾迅速染红,触目惊心,他一声不出,在我怀里发抖。
胸膛里有隆隆闷响声,我闭上眼,怒气消失了,我轻声说,“疼的厉害,就抓住我好了。不行用牙咬也可以。你不是狐狸吗?那就咬我好了。”
第一块玻璃碎片顺利找到,挑出,流川整个身体一挺,放在背上的手用力握住我。我抿住唇,不去管,继续寻找其他碎片。
“嗳……”好象听到流川的声音,但恐怕是我幻听,这个不爱说话沉默不但是金还是钻石甚至恐怕是森林里新鲜浆果的小狐狸。
气流明显不对,流川是狐狸,可他现在没有用原形,两个大男人挤在一张沙发上,他还趴在我怀里,嘴唇正好在我耳边,就算幻听可耳朵边痒痒的气息不会错,流川想说话。
我小心换个姿势,这样能看到他的脸。
“仙道……”清澈见底的眼睛,小狐狸挑着眉,认真看我,青天大老爷缉拿住真凶般对着我的黑脸宣判,“真难看。”
我停下手上动作,没心去理会我根本无心控制的脸部表情,我知道这般平底锅似面孔倘若拍照留念,足以叫越野等一干人吓倒。但是流川不应当介意,我笑不出来,小狐狸说过,不想笑时就不要笑。
空间太小挨得太近,甚至能看到点漆般眼里那两个小小的,板着脸面无表情的我。
玻璃碴已经差不多捡完了,我耐心等,果然还有下文,低弱吵哑的嗓声,“白痴”,灼热急促的呼吸一下下喷上脸颊,“我才不会吃生肉。”慧黠笑意从狭长黑亮眼里闪现再消失。
我凝目看他,看进他眼底最深处,看他清清亮眼底那两个小小的我。
小小的我,正在慢慢、慢慢绽开微笑的我。
这样的微笑,不够快活轻狂惬意,轻轻浅浅淡淡,却温暖如春光晴朗如碧空。这样笑着的我,不再长袖善舞精英干炼,却自在如云舒云卷闲淡任花开花落。这样的我,在神奈川的海风中笑容明朗尽情奔跑十七岁的我。
世界上所有的我里,最完整、最纯粹、无人再能捕捉的我。
扔掉手里毛巾,换一条新的小心擦试伤口旁的污血,我柔声说,“要擦酒精了,那可是很疼的。”我微笑,“这回我可是亏大了,胸膛借给你靠肩膀借给你咬你还不要,小狐狸啊…”假模假式叹口气我说,“这样的好事你再修五百年也遇不到啦,错过了不要后悔哦。”
酒精棉探上伤口,一阵火辣辣地痛,流川狠狠咬上我肩膀,我挺直背,小心搂住他,安静等他熬过那阵剧烈疼痛。
所有受伤的地方全部清理完毕,我扶住流川小心翼翼让他俯在沙发上,重新坐回地毯,解开衣服处理我肩膀,若有所觉侧过头,黑亮眼睛正在看我伤口。
我举起被血沾红的酒精棉恶狠狠笑,“流川,这件衬衣花我半月薪水,被你咬坏了,看你拿什么赔!”
流川很不屑白我一眼,毫无一丝歉疚。
在我衣柜里住那么久,不叫耳濡目染叫全身心接触,跟鞋的品味有天壞之别。
虽说给他买时一点不挑,可他对我哪件衣服好哪件衣服不好简直天份的不得了,往往随手抓出就是价钱最高的那件。想当初第一件看中的就是阿曼尼。
现在身上这件衬衣,准备去旅游特意找出开车时穿的,普通再普通大众再大众,这件衣服要能花我半月薪水,唯一原因我的薪水实在太低。
清理掉各式沾上血的毛巾、棉花,顺道洗了脸,换件清爽衣服。我重新回到沙发,流川已经睡去,但显然睡得不安稳,虽然一声不出却不时蹙起眉,分明伤口仍在不时痛。
我探手过去,呼吸明显均匀许多,而且不再有那种迫人的热度,慢慢放下一些心,我想我的救护处理还算成功,而且我的运气可能好到不得了,流川多半受内伤。
不,不是可能而是肯定,流川一定不会有什么内伤,我不介意所有的运气这一次全部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