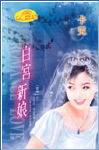白宫突围-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来行刺,而且凶手竟然那样轻松地就混过了警戒线。这使他对泰伯森吹嘘的“立
体警戒网”不得不产生怀疑。尽管此后美方在邓小平的公开活动场所采取了更加严
密的防御措施,但他浑身的神经仍同拧紧弦的钟表一样分分秒秒都绷得紧紧的,惟
恐稍有不慎再发生什么意外,而这种“意外”现在几乎随时都会发生。这时无线电
对讲机中传来泰伯森低沉的声音:“丹尼尔,命令四、六小组马上进入A 区。”
一直守候在监控器前的局长帮办丹尼尔。约翰轻声应道:“明白。”他随即摁
动了几下键钮,对着话筒呼道:“劳伦斯注意,‘老狼’命令你们马上进入A 区。”
罗新华知道,所谓A 区是指宴会厅便门外的长廊通道,国宴结束后卡特将陪同
邓小平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艺演出。原计划从正门穿过前厅走出白宫,现在泰
伯森决定改走便门外的长廊。罗新华很赞成他的这一改动,因为他已在显示器上看
见数百名记者已将前厅挤得水泄不通。他奇怪美国怎么有这么多记者,而且都能随
便出入白宫。罗新华又扫了一眼泰伯森,见他仍然站在那个位置上,目光警觉地环
视着整座宴会厅。他不太喜欢这个高大、傲慢的美国人,特别是他那饱满的前额和
自负的微笑,总令他想起朝鲜战场上的仇敌和耻辱,心中总涌起一丝不快,甚至厌
恶之感。但作为美方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组长,罗新华在短短的接触中又很佩服他
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凡邓小平经过的路线和停留的场所,他事先总要亲自反复
勘察,布置警戒,细致得连一个窗口、一棵小树也不放过,而且总要亲临现场观察
指挥,即使负了伤仍坚持如此。别看泰伯森表面上坦然自信,若无其事,但他这种
不辞辛劳、忠于职守的行为已表明他内心的紧张和压力。尽管在双方互通情况时他
只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讲了几句应酬话,但罗新华断定他一定掌握着别的“险情”
和“线索”,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讲明罢了。就像他不愿说出李。乔治和王东升
的关系一样。对此罗新华虽不甚满意,却也理解。
丹尼尔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递给罗新华一杯,感激地说:“罗先生,谢谢你
的灵丹妙药。”
罗新华关切地问:“怎么样?好点了吗?”
丹尼尔转了几下脑袋:“呶,完全好了。”
今天上午,罗新华见丹尼尔讲话时总歪着头,一问才知他昨夜值班在沙发上睡
觉把脖子睡扭了。罗新华患有关节炎,每次外出总爱带几帖“虎骨舒筋膏”,于是
便给丹尼尔脖梗处贴了一块,没想到还真见效了。
丹尼尔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夸奖道:“中国药,伟大!”
罗新华笑了笑,没说什么,两眼仍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器。
丹尼尔指了指显示器的泰伯森,轻声宽慰道:“罗先生放心,有泰伯森在,什
么事也不会发生。”
罗新华呷口滚热醇香的咖啡,随口赞叹道:“泰伯森的确是一名出色的特工。”
丹尼尔却郑重地竖起一根手指:“不,他是一头老狼,一头真正的阿拉加斯加
雪原上的老狼。”
罗新华不明白他这话是褒还是贬,只好随之一笑,没再吭声。
从两天的接触中,他对这位局长帮办的印象还算不错。也许是多年干特工养成
的习惯,他很少讲话,无论是举行会谈还是私下交谈,他总是默默地听别人讲,干
瘦的脸上总是泛着和善的微笑。不像泰伯森那样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虽然他年长
资深,虽然他即将离任退休,但对泰伯森却很敬重,甚至有些惟命是从。每当泰伯
森指手画脚下达命令、分配任务时,尽管他是特别执行小组的副组长却很少提出异
议。罗新华出于尊重,曾主动询问他对泰伯森的安排有什么不同想法。他很郑重地
摇摇头:“不,我没有想法,在特别执行小组必须一切听泰伯森的指挥。这就像一
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统一样。”他还笑着反问道:“你
们不是也主张‘一切行动听指挥’吗?听他的没错。”
罗新华略显窘迫地笑笑,觉得自己的“同情”很有些“小人之心”。对丹尼尔
这种不计得失,顾全大局的“君子之腹”越发多了几分敬意。
从几次简短的交谈中,罗新华得知丹尼尔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二战时曾在大西
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上任中尉雷达员。珍珠港大战中巡洋舰被日军的炸弹击沉,他
却只受了点轻伤死里逃生。退役后经海军情报处推荐到财政部秘密勤务局也就是后
来的联邦安全局任特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是安全局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他有
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妻子是圣保罗急救中心的护士,现在已退休。一儿一女也均
已成家。他说他们一家人都很喜爱中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也是最
伟大的国家。他还不无自豪地告诉罗新华:目前他正在学习汉语,打算退休后和妻
子一同到中国去旅游,亲眼看一看黄河、长城、兵马俑。有时他还在罗新华面前有
意说几句结结巴巴的汉语,那水平如同学舌的鹦鹉差不多。罗新华虽不敢恭维,但
对他的友好之情却很感动。彼此熟悉一些后,谈话也就随便了。一次闲谈中,罗新
华问他对邓小平访美的看法。丹尼尔不假思索地用汉语连声赞叹道:“伟大!伟大!”
他说邓小平敢来美国确实了不起,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
并称这是跨世纪的访问。他也直言不讳地问罗新华,他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只
让邓小平当副总理?“他应该是总理,是国家元首。”他有些忿忿不平地说。
罗新华笑道,这是上头的事,他不清楚。
丹尼尔又问副总理在国家领导人中排第几位?
罗新华想了想说,第三位吧。
丹尼尔就递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时代周刊》画报,指着封面上邓小平的大幅彩
色照片得意地说:“可他在世界排第一。”那神态好像邓小平是美国的副总理。
罗新华看过才知道,原来《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世界第一位伟大人
物。
丹尼尔介绍说,这不是刊物评的,是几十万读者选出来的。他还说,亚洲领导
人被评为世界伟人,这在《时代周刊》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罗新华倒被他的情绪感染了,凝视着画报颇有些动情地说:“谢谢你,谢谢美
国人民。”
几分钟后,丹尼尔便接到报告:被调往A 区的两支行动小组已全部到达指定位
置。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泰伯森作了报告。从显示器中可以看出,宴会已进入尾声。
两名中方贴身警卫也已站到侧门边等候护送邓小平退席。就在这时,连接外线的电
话铃响了。丹尼尔抓起话筒听了一下,又递给罗新华:“找你的。”
罗新华颇感奇怪,接过话筒一听才知是刘秘书打来的。对方言语很简单:“‘
长城’请你立即返回住地。”
“长城”是王枫的代号。
罗新华心头一紧,不知王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找自己,忙应了一声:“好,我
马上回去。”
第十五章 《朝日新闻》的首席记者
我们在肯尼迪中心观看了一场很轻松的演出。
后来我和邓、邓的夫人卓琳、罗琳莎以及艾米一起登台与演员们见面。当邓拥
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
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地流泪了。参议员拉克泽尔特是极
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
童唱中国歌曲(孩子们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诚地喜
欢人民,他确实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也许因为邓的精力充沛和个子矮小的缘故,那天晚上艾米和其他孩子们都非常
喜欢挨着他,同他在一起,其实双方似乎都有这种感情……
摘自卡特1979年1 月29日日记一1979年1 月29日晚8 时。华盛顿。肯尼迪艺术
中心。
他随潮水般的人群从白宫新闻大厅又涌到了肯尼迪艺术中心。他和所有的记者
一样,神情急切,脚步匆匆,机敏的目光四下寻觅着。他确实很焦虑,因为按计划
中部署他必须在今天晚上想办法接近目标,完成他的“采访”任务。
五颜六色的彩灯将艺术中心大厦装饰得金碧辉煌,灿烂绚丽。停车场、入口处、
长廊中、阳台上,到处是身穿制服的警察,便衣特工和各种监控仪器。那些手持请
柬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虽然都是华盛顿的名流和要人,却也均受到警卫的严密盘查,
甚至连女人携带化妆品的小皮包也不允许带入场内。他已从报纸上获悉:为了保护
邓小平的安全,卡特命令安全部门仅在华盛顿就调集了一万多名警力和各种先进的
监控防暴设施,真称得上全力以赴,警戒森严。他冷笑一声,这又有什么用呢?再
多的警察,再尖端的设备也休想阻止他的行动,也休想阻止他的计划。通过一天多
的观察,他对“目标”的活动范围和规律已基本掌握,这更增添了他走向成功的信
心。每想到那即将完成的伟大使命,他便禁不住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心中充满了
复仇的喜悦和快感。
由于没有请柬和特别采访证,他和大部分记者仍被挡在入口处前的休息厅内,
只能通过电视屏幕了解场内的情景。邓小平由卡特夫妇陪同已走进二楼的包厢。两
千多名特邀观众起立欢迎,掌声雷动。
他却把目光一直盯在前厅的入口处。他真有点纳闷:这些美国政客为什么会对
邓小平表现出这样强烈的热情?狡猾的卡特为什么要用这样破天荒的隆重仪式欢迎
邓小平?据白宫新闻处透露,卡特还破例批准美国的四大电视台对今晚的演出进行
全球性的卫星直播。乔尼说得对,这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
不过,他现在对卡特和这场“史无前例”的晚会却一点不感兴趣,他关注的只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已经盯了他很久,可以说从邓小平的专机一到华盛顿
他就盯上了这个人。他决定今天晚上就要采取行动。但万万没想到,在白宫的宴会
结束后,这个“小人物”竟从他的视线中失踪了。这令他大为疑惑,他没敢在白宫
久留,随记者群匆忙赶到第二个采访地点肯尼迪艺术中心,继续寻找失踪的“目标”。
按他掌握的规律这个时候此人应该早已进入艺术中心,应该出现在那些现场直
播的电视记者的摄像机内。然而他看遍了所有的直播屏幕,也没发现这个人的身影。
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惊异和不安。他思索了一番,断定此人还没有进入演出大厅,也
断定他一定会进入演出大厅,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记者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
的采访机遇。
可他为什么没来呢?他能去哪里呢?
二杜立彬非常恼火,恼火得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他没想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候
镁光灯的电池竟出了故障。平素他总喜欢把手中的照相器材称为“武器”,精心照
料,他的这种细心很受同事和上司的称道。而偏偏在这场一生难得、举世瞩目的
“战斗中”,他的“武器”却突然打不响了。这对一名肩负重任的老记者来说无疑
是失职和耻辱。他真后悔今晚出来前没多带一块备用的电池本来他是要带上的,并
已装入采访包。但他又想多带一架备用照相机,而进入宴会厅采访检查的非常严格,
对记者携带的器材限制也非常严格。思忖再三,他还是觉得后者更重要,便舍前留
后了。可老天偏偏与他作对,结果偏偏是电池出了问题。正当他举着照相机在宴会
厅为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镜头频频摁动快门时,镁光灯竟怎么也打不亮了。这种情
况在他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似乎还没遇到过。他急了一身汗也没抢修好,只得半途
退出宴会厅匆匆赶回下榻的肯塔基旅馆。王东升长年在这里租了一间客房,杜立彬
到华盛顿后便住了进来。等他换好电池心急火燎地返回白宫宴会厅时,晚宴已经结
束。邓小平已被卡特请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艺演出。杜立彬未敢喘息,又急匆
匆赶到距白宫数百米的肯尼迪艺术中心。
应邀出席晚会的宾客们都已入场完毕。艺术大厦前厅内拥满了保安人员和被挡
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