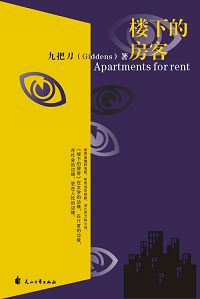相似的房间-鲇川哲也-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有人证明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而且证人是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所以没有理由不相倍他的证词。”
“是什么证词?”
“那还是你直接去调查比较好,如果有了先入为主之见就不太好了。”
律师讲完,好象该歇一口气似地把杯子里已经变温了的水吗干,接着又急忙擦冒出来的汗。
五
简单地说,报告文学作家有好的,也有差的。她是属于好的,还是差的,我判断不出来。我要求会见她,她以事情忙为理由让我得等三天,从这一点来看,她也许是个红人。但也可能是故意装作红人而让我等着,而实际上非常空闲。
她住在杉井区善福寺的公寓大楼七层,房间非常豪华,衣着打扮也是最高级的。可见,她的收入似乎相当之高;看来她还是个红人吧。她的身高和我相仿,身材苗条,满可以做一个时装模特儿。年龄三十一、二岁;小巧玲珑的面庞轮廓鲜明。
我被让进一间象电视台布景似的过分装饰的房间。用她喜欢的字眼说,叫做“起居室”。如果说我那终年不叠被褥的公寓也算是起居室(因为只有一间),那么两者好象有天和地、麒麟与猪锣之间的差别,实在无法相比,我这饱经沧桑的人不由得坐立不安。她以冷漠的跟神注视着。她微微张开唇膏已褪的朱唇,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那副微笑的容貌真是漂亮极了,但是她的跟睛却非常严肃。
“这件事刑警已经询问过我了,但马上他就理解了。”
她抽着在长烟嘴中装着的妇女用的细长纸烟,好象很乐意与我交谈,语调很轻松。
“那么,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首先是动机问题,我说真是胡说。我这个人,这五年完全成长起来了。五年前,我天真幼稚,简直象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所以才对中山那样的人发生了兴趣。可是,现在不同了,对他那样的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了。你读过他最近写的东西吗?”
我摇了摇头。中山和她的书我都没有读过,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读小说之类的东西。
“身为推理小说作家,净写黄色东西。一个人关在工作室里拼命写些黄色小说,你想一想看,这个人太脏了!”
……我也不打算瞪起眼睛来攻击中山毅,在这种场合,只能随和她了。
“确实如此,关于黄色小说作家给读者的影响怎样,我丕知道,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好象成了一亿人都是色情狂的国家了。”
“所以嘛,我不承认那种人算什么作家。我的理想还远远地高着哪。”
她猛然举起一只手来,那姿势很象耸立在纽约一角的自由女神像,虽然我没见过那尊像。
“我这么一说,刑警还施计套我说,你回忆起过去被抛弃的往事很伤心吧,我理解你的心情。这并不是笑话,他这么问本身,就说明刑警水平之低。”
“不错。”
我表示了同意。而且声音大得超过了必耍的程度。
“但在社会上,水平低的人还挺多呢。我的老牌律师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胡猜乱疑地说,你一定是在为那件事夜不成眠地悔恨吧!他就是这种不高明的胡猜乱想的人!”
我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个房间的空调很好,所以,出汗也肯定是冷汗。
“我想再问一下,重冈被杀是什么时候?”她稍微改变了一下口气问。
“是这个月一日晚上十点钟左右。”
“重冈勤的家在什么地方?”
“在王子飞鸟山附近。”
“那么说,我是完全清白的啦。那时我正在这个房间里。”
的确,如果她说的是事实,就足以证明当时不在现场了。
“那么,您的证人是谁?”
耍让刑警确认无罪,当然需耍拿出可靠的证明。
“那天晚上我正在招待客人。我到北陆去旅行时,经一位古家具店老板介绍,购得了古九谷①(石川县九谷地方出产的磁器。从明历到元禄初期(l665…1690)烧制的作品最名贵,陶磁史上称之为“古九谷”,此后的作品称之为“九谷”。两者均为珍品。)茶具,有的朋友说我上了当,全是假货,他们说决不是嘲笑我。但我相信是真货,因此想请个懂行的人鉴定一下。”
“那天晚上的客人是鉴定家?”
“是的,是佐藤文吉先生。”
“是学者吗?”
学肴和艺术家是不太好对付的。前者惯于装模作样,叫人难受;后者则进入角色就忘掉了一切。
“不是学者,是茶道大师。”
“是不是那个叫傀儡坊的……?”
“那是搞花遣的,我说的是茶道大师。”这位美人对于我的无知表示出可怜的神情,并且以严厉的口吻责怪我。
我从公寓大楼出来以后,乘电车来到大田区北马区的佐藤文吉家造访。门旁的围墙上有一块奈良风恪的招脾。可能是因为茶道大师使用文吉这样普通的名字不足以表示自己身分的高贵,所以自称为“不岑”。
方才我打电话问时,说他到附近的女子业余大学讲课去了。下午四点才能回家。所以我就准时来拜访。
不岑大师的确象个茶道先生,整齐地穿着白色的越后出产的上等麻布和服,外罩黑纱短褂接待我。这是一间六铺席子的日式房间,屋里装饰的匾额上,写着我连认都不认得的漂亮字。我在夏季用的坐垫上面端正地坐下来,不到两分钟,我的腿就麻了,但仍然一声不吭。
“那些问题,刑警也都问过了。”
这位大师与报告文学作家的回答一模一样。他眉清目秀,但有些神经质,四十岁左在,脸色白净,这可能是因为常年在家饮茶的结果吧。他好象为人慎重。对我的询问,总是先仔细地付度一番,然后才开口。对于我这一行的人来说。真是个理想的对手。如果是无关紧耍的事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是最使人头疼了,但社会上这种轻率的人往往很多。
“我们是过去通过一件小事认识的。前几天突然来了电话,请我去鉴定一套茶具。因为我是个一说到茶具就格外感兴趣的人,所以就同意了。白天有弟子来,比较忙,晚上还是有空余时间的。”
“您去了善福寺的公寓大楼?”
“不,我们先在新宿的茶室会齐,然后用车把我接去。”
“时间大概是几点钟?”
“时间嘛,在茶室里见面大概是八点半左右,路上用三十分左右,那么到公寓大楼大概是九点钟吧。此后,我在那里打搅了两小时,她又用车送我回家。”
既然从九点到十一点她一直在公寓大楼,那就不能不承认她均时确实不在犯罪现场,我决定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追问下去。
“鉴定需要两个小时吗?”
“不,有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只耍看看题字就可以定了。虽然对泽村和子来说太遗憾,那并不是古九谷的茶具。不过。如果我简单地说那是赝品,显得有点草率,于是我稍微仔细地进行了一番鉴定,花费了一段时间。”
总之,是装模作样吧!
“请你鉴定时她自己出去过没有呢?”
“没有!……哦,等一等,有那么一次。她说威士忌喝光了,于是到附近的酒店里去了。拿回来一小瓶威士忌。”
他一说外出过一次,我觉得有门儿。于是颇为紧张,但去处晃附近的酒店,就不值得一提了。
“那么晚,酒店还营业吗?”
“当时已经十点了,酒店当然关门了。可能是在自动售货机那里买的吧?”
“她说是附近的洒店吧?”
“我们等了最多只有五分钟左右,可能就是附近的酒店吧。出乎意料那威士忌很好喝。她劝我就那么喝,兑上自来水,味不好,难喝……漂白粉的味很浓。”
我也颇有同感。咸士忌香味不管多么浓郁,由于兑了水,
味不正,把味儿都破坏了。
“她也喝酒了吗?”
“不,因为她要驾驶汽车,喝的是果子汁。”
我和他的问答到此结束。如果这样就足以证明她不在犯案现场的话,其它就没什么可问的了。
六
律师听了我的汇报,显然吃了一惊。他那肥胖的身躯好象泄了气似地萎缩下来。当然,实际上是不会萎缩的。可是从他并没有说些引以为得意的挖苦话和责骂话来看,好象他由于某种原因身体突然萎缩下来了。
“我还以为她是最有嫌疑的人呢。因为再没有怀疑的人了。”
他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微弱了,使我也感到好象很难过。
“好,你再努一把力吧!”
虽说努力,可是她并不在犯案现场的证明业已成立,我还有什么办法呢?话虽这么说,既然取得人家的报酬,也不能呆在办公室里睡午觉。无可奈何,我只好开着即将报废的“国民牌”摩托车往来于王子的现场和善福寺的公寓大楼之间查看,或是在善福寺公寓大楼附近的酒店和她的房间之间徒步来回转转。
这样,偶然间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同时,使我想起了日本纸牌上写的一句谚语。“常在外面走,也有好运气。”那时,我的车正是油快用完的时候,来到公寓大楼附近的加油站停下。我趁加油的时间洗了冼手,顾便拧开水龙头喝口水。当时梅雨季节已过,在烈日之下行车,嗓子很干渴。路旁的冷食亭里放着很多冷食品,好象在频送秋波似地引诱着我。可是,在真正感到渴的时候,即使有点漂白粉味,冷水还是好喝的。
满满的一玻璃杯水,我一饮而尽。溢出来的水从嘴角流向下颈,湿了衬衣。对于汗渍渍的身体,这种清凉劲儿使人感到很舒服。我又一口气喝下了第二杯,全身才感觉舒畅。
“啊,真好喝!”
正在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灵感。对我来说,这是很少有的事,但在故事中,那些著名的侦探都曾闪现过这种灵感。
昨夭,那位茶道大师说过,水里有漂白粉味不能喝。的确,东京市自来水的味道很差,这是早有定评的。喝了那样的水,不但金鱼受不了,我们人也受不了。只是人们害怕饮用未经消毒的不干净的水可能生病,所以只好喝有怪味的水,吃有怪味的水烧的饭。可是我刚才喝的水,不但没有漂白粉味,而且非常好喝。
也许是这个加油站特地自己打了井使用井水吧!
“不,不是井水,是自来水。不过,在杉并区内只有善福寺一带的水是由杉并自来水厂处理的,这水最好喝了。有的顾客专为喝这里的水,特地到这里来加油呢!”
穿工作服的职员好象为这里的水而自豪得了不得,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着。
“在同一个杉并区里,东村山一带和朝霞一带的水味就差得多了。有这种高级酒似的水,除这里的杉并区自来水厂外,还有世田谷区的泊江自来水厂呢。”
“是吗。不但让我喝到了甜水,而且还给我上了一课,真是太感谢了,真叫我开了窍呢!”
我拍了拍穿工作服人的肩膀,递过去刚买来的香烟。因为我感到这可能成为破案的开端,起码是个好预兆。
然而,当我一面驾驶着已加足汽油的车,一面考虑把这个新发现同什么联系起来,怎样使它发展下去才好的时候,我又感到前途渺茫。我喜欢跑跑跳跳,用得意的招数一脚把对方踢倒,这也是我拿手戏中的拿手戏。但我下生以来最不愿意动脑筋思考问题。只要稍微思考点问题,脑袋就开始痛起来了。
反正,再和茶道先生会一次面,对他谈话中的矛盾之处进行反复追问,这是我想出的唯一办法。我把车停下,先打了个公用电话,回答说,今天他去养老院讲课没在家,要过两个小时才能回来。因为还要等两个公时,于是我把车停在途中一个小学校的门前,走进校庭,躺在桐树荫下的靠背椅上,准备睡个午觉。
虽然后背略得有些发痛,但凉风却使人觉得很舒服。在绿树围绕中睡上一觉,觉得好象耍做个绿色的梦。我轻轻地闭上眼睛。从体育场那边的教室里传来了我童年时代学过的令人怀念的歌声。……唱的是什么歌曲啊!“在河里可以抓到兔子……”什么什么?河里兔子在游泳,真是闻所末闻的事情啊!……
有人在使劲地捅我,我睁开了眼睛。不知是校工还是管理员,一个穿着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子的人毫不客气地把我摇醒,说与学校无关系的人员严禁入内,不出去就是非法侵入,以此为由驱逐我。
“啊,我错了,对不起,大叔,怎么都行就是别找警察,请原谅!”
我和和气气地作了答复。虽然我叫他大叔,但年龄比我还小四、五岁。我所以没跟他吵架,是因为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