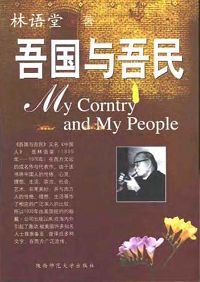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作者:胡辛-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纯儿岂敢不从命?扮个鬼脸,不情愿地跟着公公进了后天井旁的西厢房,那是公公的书房养心斋。
周妈已拢好了一陶盆炭火搁置厅堂,又利索地将厚绒毯铺上八仙桌;懋宿静静地提出麻将盒,三姐没归家,得他这个生手凑数。
奶妈会香逗着维儿,时观战,时到门口张望。
西厢房中,传出修纯结结巴巴的背诵声。
周锦华烦躁不安起来:“老三……怎么还不回呢?”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四 与众不同的“蒋太子”
四 与众不同的“蒋太子”
章家三小姐在古城作幽幽神游。
德胜路、中山路、环湖路、沿江路,她步履匆匆、顾盼生情,将那流逝岁月的踪迹来寻觅。
如果没有变迁的时代没有开明的家庭,她原来只属于烹饪与女红。章家大女上了京都女师大,让二女读毕小学,亦要钟爱的三女进了省城教会学校——宝苓女中。西化的教育,数理化体音美的濡染,给她年轻的心田拓宽了一扇明窗。而北伐战争隆隆的炮声、举着标语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万众一心的游行又燃烧起少女原来恬静的血液……
夜中的百花洲迷离虚幻,苏云卿的菜圃和蒋介石的行营混沌难辨。
她鬼使神差般进到湖畔的心远中学。这葬着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校园,眼下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到处是南腔北调扶老携幼的人们,到处是布满尘垢和恐惧的面孔,到处是饥饿的哭泣和病痛的呻吟,到处是对故土的思念和喃喃的述说……
她窒息了。她逃也似地来到篮球场的冬青树旁,哦,球场上也东倒西歪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样呻吟啜泣。老(亻表)……给我……
泪水蒙住了她的双眼,老(亻表)……
明灿灿的天高云淡的秋日。明灿灿的洒满金色阳光的篮球场。明灿灿的生龙活虎的操着南腔北调的健儿们。
江西省青年服务团设在心远中学,从东北、平津、宁沪流亡而来的大学生们,有伤感颓丧,但更多的是勃勃朝气和乐观奋发的劲头,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其时,她在省抗战后援会帮忙,有事来服务团,一进大门就感受到热烈明朗的气氛,她的脚步不由得轻松起来,手也情不自禁抚着矮矮的碧绿的冬青树叶。
一只篮球飞过冬青树丛,在鹅卵石的小径上跳腾几下后,就要擦过她的身旁,一时兴起,她一个跳跃,接住球,小径上已奔来一男子:“喂——老(表)!给我!”
热切、开朗、随和。她有点尴尬,旋即将球很潇洒地轻掷过去。
男子接住,很赞赏地对她一笑:“谢谢,老(亻表)。”又奔向球场。
她在这一瞬间看清了这男子,白布衬衫,两根吊带的西装裤,头上戴顶鸭舌帽,帽檐下的眼睛似很有神,笑起来弯成月芽,有点眯缝。这,跟她自己笑起来很相似。
她的脸倏地赤红:胡思乱想。
她静静地立在冬青树旁观看这场球赛,直到球赛结束。她看见那男子挎着夹克衫,在一群大学生们的簇拥下,边走边聊。看见他逢人就打招呼:“喂—老(亻表)!”
他一点也不尴尬,或举手致意,或握手言好;时驻足观看宣传栏,时与人争辩得激昂慷慨。他将原本明朗活跃的氛围鼓动感召得如火如荼,让人感受到平等民主的祥和。
他就是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的“蒋太子”!
他第一次来到南昌,然而刚到就如鱼得水般融洽,刚到就鹤立鸡群般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特殊的身分?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风采?
总之,他烙刻进了她的心田……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五 “亚若,你娘……就托付于你了!”
五 “亚若,你娘……就托付于你了!”
亚若居住的小阁楼,收拾得绣房一般典雅,只是嫌寡淡了些,什么都是海青色的。壁上斜挂着一支箫和一把月琴,写字桌的玻璃台板下压着自抄的蔡琰的《悲愤诗》,蝇头小楷,娟秀极了。章老太太正在收拾细软首饰,亚若便起身继续收捡父亲的行袋,一边宽慰着母亲:“妈,船租好了,东西收捡好了,该交代的事都交代了,等明早把爸送上船,我们后天就走了。”
“唉,这兵荒马乱的,人家都怕天各一方,我们家是天各几方呵。”
“妈,收拾熨贴了,早点睡吧,我送你下去。”
下到楼梯口,却见西厢章家主人还在擎烛夜读。母女俩便推开虚掩的门靡,将收捡好的大包袱拎了进去。一时间,章家老太太竟哽咽不能语。
抬眼看她们的章先生就呵呵笑了:“怎么啦怎么啦?不过是小别前夜嘛。”
章老太太就抽抽搭搭:“懋兰他爷,这兵荒马乱,你也不是年轻的辰光了,全靠自己保养呢。庐山寒气重潮气重,这传代的狐皮袍子还是你带上……”
听着内子的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章先生的鼻头就有些酸酸,眼塘子就有些潮湿湿的……
章老先生也算阅尽人间沧桑。前清末叶,吴城镇的少年章甫,县试、府试、省试连连中魁,轰动乡镇。十八岁那年娶了同镇名门周家之女周(女先)为妻。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章甫自是得意。婚后虽连生三女,但民国了,时风不同了,何况章甫还曾在北京政法大学进修过,亦算新潮派,不仅不难为娇妻,还调皮地哄着妻子一同对付刁横的老母呢。去京都求学也罢,奉派到遂川当知事也罢,在佑营街挂牌做执业律师也罢,风风雨雨近三十年,说雅点,琴瑟和弦;说俗点,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眼下即要一北一南,何况近年来夫妻间还生出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章甫的心就被搅得不能平静了。
三女却站到西壁一溜长排的书柜前浏览。笨重的老式书柜几乎挨着天花板。
三女最钟爱书柜,而他最钟爱三女。
大女太沉静,二女太懦善,四女懋梅自小给奶娘带,十来岁才归家,满女幽兰,一生下来就给新建的远亲当了养女,唯有这三女,活泼伶俐,聪颖可爱。三岁背得下唐诗一百首。七岁那年,章甫让儿女围着炭炉,给他们讲了曹植七步诗的故事。这个才七岁的三女,竟跳了起来,嚷道:“我也能作七步诗!”好呗,看她挪着小步,七步到了,就吟:“春兰桃李竞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这还了得!满座皆惊。她将姊妹五人的名字全嵌进去了。他章甫能不疼爱这白净玲珑的小精灵嘛?
到得抗战前夕,她竟然自作主张,将懋李改名叫亚若,底下的弟妹也就一哄而起,大弟懋萱改名叫浩若,小弟懋宿改名叫瀚若,懋梅也吵着要改,章老先生就说,你是大雪纷飞时生的呀,这“梅”字我舍不得。懋梅就改名叫亚梅。怎么说,三女早早就是弟妹们心目中的主心骨了。起初章老太太是不允许这么瞎改名字的,有宗有谱按辈分叫的,一个毛丫头敢擅作主张?章老先生却很开心,率先在家喊新名字。想当年,他到京都求学,不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章贡涛吗?章贡合流为(章贡)(赣),赣江之水浪涛涛,有气势有抱负。他还将发妻周(女先)更名为周锦华,锦绣中华,女儿家的名字也要不凡嘛。看来三女像她呵,这就叫有种像种吧。章老太太却不改口,那原先的名字就委屈地做了小名。
此刻,章老先生望着凄凄怨怨的妻和手不释卷的三女,便说:
“亚若,一大家人可就托付给你了。”
话很重,亚若便有点愕然,扬起弯弯柳叶眉,旋即又甜甜地笑了:“爸,我是那份料吗?爸还是改变主意吧,全家一起南迁好了。”
章老太太更是声泪俱下:“一家人家扯做几块,怎是得了呵。”
章老先生摆摆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已与友人约好,就不要改了。再说浩若的部队说是也调到了庐山,父子团聚亦是幸事嘛。你们呀,终归眼光浅一点,中国是亡不了的!
老式挂钟当当当当响起,十二下,正是子夜。
忽听有枪声和凄厉的呼喊远远近近撕碎子夜的寂静,三人面面相觑,动弹不得。
这枪声喊声似从不远处的省府传出!
他们当然不晓得,成群的伤病军人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着涌进省府请愿,冲破卫兵的封锁、闯入府门,登上大堂,喊叫着要见“熊主席”!其时跛着一条腿的省主席熊式辉惊慌失措,逃进后花园的防空洞内,他的侄儿熊滨出来阻挡,手一挥:“格杀勿论”!枪声大作,曾在张公渡抵御日军的伤病员便倒在大堂的血泊中!
好一阵,夜又归于死一般的沉闷寂静。
亚若刚想启齿,又听有喧嚣声浪响在街外巷里裹挟着叫人毛骨竦然的恐怖。
“快跑啊!日本鬼子打来啦!”
“快起来!快起来!全体疏散撤退!”
啪啪啪!
蓬蓬蓬!
白手套、警棍焦灼地拍打着、砸着一扇扇沉睡的门扉。门一扇扇吱吱呀呀开了,探出惊愕的披头散发的睡眼朦胧的人们。
“快跑!快跑!快跑!”
大街小巷!人拉人人挤人人推人人踩人。
二姑妈章金秀一家八、九口,扛箱挑笼,好不容易挤到县前街汇合成一路,个个脸上冷汗热汗交流,可又禁不住打着冷颤,牙齿格格作响。
章贡涛先生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撕碎了他的幻想,就转化成满腔的愤怒,反剪双手在厅堂里急促徘徊,骂着鬼子,吐出文天祥的《正气歌》。
亚若望望这二十几口的大家庭,将一绺秀发捋到右耳后,沉稳地说:“大家莫慌。船我已租赁好,米和咸菜也上了船,船老板是英葵哥哥介绍的,守信义。从这里上码头,大家一路要相互关照,各人管好各人携带的行李,会香你们几位奶妈,只管抱住细伢子。若万一冲散了,就到章江码头汇合,我会在埠头等的。就这样,大表弟和瀚若打头,我压阵……”
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这才把混乱可怕的情绪略略调整。一大家子人望着这幢虽不阔绰但井然有序的老屋,就不禁泪流满面。
章老先生也不禁抹了把老泪,与骨肉至亲点头举手道别。亚若硬咽着:“爸……大衍细衍……还有婆……就拜托您老了……”
“放心……放心……我会找入送他们随后跟去的……亚若……你娘你弟弟侄儿……就都托付于你了……”
“爸——”亚若一头扑在父亲胸前,生离死别般悲恸欲绝。她毕竟还年轻。
章老太太就也大放悲声。亚若这才赶紧止住哭声,搀着母亲离了家门……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六 天涯同命鸟
六 天涯同命鸟
省政府已迁到泰和县城,但泰和终究太小,不少省级机关就迁到了赣州。于是泰和与赣州的往来极其频繁,这条负重的简易公路便越发泥泞难行、满目疮痍。
一辆烧木炭的货车喘息着由泰和往赣州颠簸而行,那帆布车篷将车厢覆盖得蛮严实。连车厢后方也遮着两块大帆布,像装载着保密军需品或是怕风怕雨的精贵物资似的。
过了遂川,临近黄昏时,车厢后方两块帆布交接处被一只丰腴的女人的手撩开,无名指上有颗红宝石戒指——正是章家三小姐亚若。她探头看看车外,又转身扶着一头缠老蓝土布的女人,那女人伏在后档板上哇哇吐个不停,直到吐出青绿色的胃夜。亚若用一方湿手巾轻轻地替她揩拭,那女人方缓缓抬起脸庞,虽像涂抹了黄泥似地蜡黄,但即便在幕色中也掩饰不住这张鹅蛋脸的年轻的光彩:一双丹凤眼睛秀向鬓边娇俏地吊起,眼中似有流光溢彩;嘴巴十分小巧,却肉嘟嘟的厚实滋润!亚若不禁一怔,眼光垂到那扶住后挡板的那双手上——竟是十指尖尖削似葱!古典美女的纤手。
亚若回过神,扶那女子车过身,又将帆布盖了个严实。昏暗中,就听章老太太发话:“懋李,我这还有瓶仁丹,给她们娘俩含着,也是作孽呵,晕车这么厉害。”
亚若答应着,将仁丹接过,又有一京腔京韵的女老太哼唧着:“哟,您老呀……真是地道……您家小姐……也真是贤德……咱两家……也真叫缘分……”
亚若心头一跳,却不露声色将仁丹分给这陌生的母女俩含服;又掏出万金油,给这母女俩太阳穴旁抹抹,方柔声说:“都出门在外的,别客气了。”战时,药物是金贵的。
昏暗中,亚若又摸索着从包袱里抽出夹袄,给章老太太怀中抱着的纯儿盖上,章老太太就又轻声说:“你也迷糊一阵吧,一路上都你抱着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