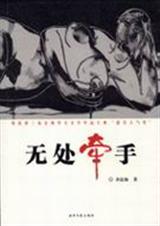无处告别-第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活动,又由于这种联想,那个男人也被拉了进来,这使得黛二
感到无比丑恶。
黛二给缪一买去了很多营养品。这举动本来完全是出于她
们以往真挚的友情。缪一却忽然像一个习惯了受礼办事的太太
那样,理所当然地欣然接受,然后是一番关于黛二工作问题的
真诚的客套,以及关于自身婚姻生活的真诚的假话,黛二立刻
敏锐地感到一股强大的隔膜与疏远向她压迫而来,她静静听着,
不想再说什么。这时,她才感到自己长时间以来对于友谊的信
仰是完全地被愚弄了。黛二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神思活跃,她
想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用,男人可以利用他的肉
体和激情,女人可以利用她的头脑与真诚。她想,如果她拥有
大权和大钱,被利用的方面还会更多。她还想,她在被利用的
时候肯定也利用了别人,这个世界就是在利用和被利用的平衡
中运转,这是多么的正常啊,自己就是这佯生存的,所有人都
是这样生存的,尽管许多人自己不承认。一时间这些思绪搅得
黛二心事重重,心乱如麻。想着人的前景,黛二心里一片空茫。
黛二本想起身走掉,但已经跟缪一的公公约好,就硬撑着
坐下来,神清冷冷地不再说什么。
傍晚,黛二在缪一的陪同下去了“谁谁”家。黛二问是否
要给“谁谁”买些礼物。缪一说,“你给他买什么都不算什么,
干脆什么都先别买,以后再说吧。”于是黛二就先不买什么,
等着以后再说。
黛二扶着缪一走进“谁谁”家的时候,正有个气功师刚刚
给“谁谁”看完病。他新近得了一种小便失禁的毛病,像退回
幼儿时期一般,早晨醒来总是一床冰凉的尿湿;甚至在白天精
神稍有紧张的时候,或在大会发言时的几声咳嗽,也会使他的
裤裆洇湿一片。为此,“谁谁”吃过很多中医偏方,连西医也
试过了,尽管“谁谁”对西医深恶痛绝。但都没有疗效。
缪一从一进“谁谁”的房间立刻换了容颜,父亲长父亲短,
问寒问暖,殷勤备至。看到缪一如此苦心经营,黛二心里有说
不出的滋味,她深深吸了几口气,使自己可以坐在沙发里面不
至于起身走掉。
那气功师却在一眼之间给黛二小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身材颀长但不干巴,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体态中散发一种底
蕴十足的温情与魅力,他那镇定自若的神情给人一种宗教般的
超然的悟性。他的手很大,那手在空中划来到去的时候,黛二
在心里遥遥感到一股博大温热的神力。
这时,一声嘶哑的老鸦般的声音从黛二小姐的头顶和脚尖
钻入她的身体,她一时没有搞清那是什么声音。待她敏觉地从
那声音传出的方向追寻到发出声音的初始点时,她望见“谁谁”
的嘴唇在吃力的地翕动。她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并判断一下“谁
谁”说了什么,她已被“谁谁”的秘书很礼貌地引领到另一个
房间。那秘书的毛笔字非常漂亮,他悬腕运笔,几分钟时间,
黛二所需要的推荐信已经写好,那秘书又回到“谁谁”的房间
签了字,事情顺利得有些令黛二意想不到。
办完事,黛二就起身告辞。她不想再与缪一打招呼,她知
道自己除了对缪一还拥有一份怜悯,再也没有其他。于是,黛
二就悄悄地走掉了。
走出“谁谁”家住宅的时候,户外夜晚的天空橡梦境一样
安详,黛二小姐独自站在“谁谁”家门外梦境一般的空旷里,她
想起了那个忽然变得陌生了的女友的隆起的肚子以及世界上千
千万万通过不同的黑暗渠道钻入女人们日益隆起的肚子里去的
事情。她的神思滑向远方。她知道自己在梦幻里活得太久了。她
站在那里,望着幽静如荒漠的苍穹,重温起自己在夜梦中最常
出现的几个景象:第一个场面,就是她独自一人在四际荒凉的
沙漠里无尽地跋涉,秋风掀起她的衣服,裤管里也爬满幽幽的
风声,她永远在走,却永远也无法抵达目的地;第二个场面,就
是她在拥挤不堪、嘈杂纷乱的楼群之间被许多人追赶,她刚刚
甩掉一个,就又冒出一个,无数个埋伏四周的追赶者永远会从
意想不到的方位向她袭来;第三个场面,就是一两只颜色凄艳、
阴暗的母猫永远不住地绊她的脚,它们的目光散发出一股狂热、
病态而绝望的光芒。黛二小姐冥冥中感悟到,那无尽的沙漠正
是她的人生;那拥挤的楼群正是纷乱的情场;那凄厉的艳猫正
是危险的友情。
一阵夜风裹在黛二小姐的身上,把她从邈远幽深的天空拉
了回来。她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她知道自己把世界上的一切
都看得过于认真和严重了,把天空和大地当成了真正的悲剧舞
台,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悲剧演员,并且过于真诚执著地恪守
自己的演员职业了。
这会儿,黛二小姐开始判断自己的位置,她的空间方位感
从来都很差,她一边费劲地明确回家的归途,一边为自己茫然
混乱的思绪与情感寻找一条出路。
这时,那气功师从“谁谁”家告辞出来了,他向黛二小姐
这边走过来。于是,很偶然地他们同行了几步。气功师的目光
在黛二身上停留了一瞬间,然后说:“你经常头疼是不是?如果
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黛二抬头望望他的眼睛,它散发出一
种征服者般无可抵御的温情,那神情就是一声无声的军令。
“我有个诊所,自己干。主要是搞气功。”
“花费很高吗?”
“一般是收费的。我最近正在搞中枢神经系统以及一些穴位
的研究。对你可以免费。”
黛二望着他,默默地在心里叫了声:“老天爷,就是他。”她
稀里糊涂点了点头,说:“愿意。”
他们分手的时候,悠闲的月亮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远
处运送货物的火车汽笛声遥远地传过来,把夜晚衬托得格外宁
静,黛二小姐望着气功师那超然之躯和温和的背影产生了某种
想象,她的内心忽然生出一股柔情。
第二天是星期一,黛二特地早早起床,按照气功师指定的
时间和地点来到他的私人诊所。
那诊所就设在他家里,开门的正是气功师本人。他身上雪
白的大褂透出一般职业医师的冷峻而和蔼的气质,提醒来者他
来看的只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医生而不是为了叙忆某种旧情的朋
友,他不会对你的任何私人问题有所侵犯。黛二在进去的一瞬
间,环视了这里的格局,这里明显地拥有家居的特点,同时又
明显地弥漫着一般淡淡的悦人腑肺草药的清香。她被气功师引
领到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完全是医务诊室的陈设,使黛二看不
出一丝一毫的生活痕迹。
从一进屋,黛二就感到一般涌动的气场在她身前身后身上
身下徐徐滚动。到底是气功师,不是一般的中医或西医师,黛
二一直对气功深感兴趣,就像早年迷恋哲学那样对气功存有很
深的好奇心。气功能否治病她不清楚,但她对此作为一种物质
的存在深信无疑。她以为气功是与巫术、宗教、神话、灵魂、科
学、生命和宇宙都有着某种关联的东西,在其背后拥有着一个
神秘莫测光怪陆离的世界。黛二小姐对于这种虚幻而邈远的力
量的兴趣,完全是出于她的精神世界对于某一种解脱欲望的企
盼,她企盼宇宙间存有一种力量,它使人能够在念灰思焦、郁
悒孤寂、心怀仇恨、盛怒烦躁、悲伤绝望中保持精神的平衡。在
处处碰壁的情景中,在理智的经验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有所解
脱,凭借这种力量终南捷径,逃到超然的领域里去。
黛二小姐被气功师扶上一张很平的窄床,平躺下来。床很
硬,由于头部没有东西可枕,黛二产生一种挺胸抬头之感。也
许是因为这姿势使她僵持,也许是因为她一览无余地仰卧在一
个陌生男人的注视之下,她感到全身绷得很紧,无法放松。
气功师请黛二小姐放松并且闭上眼睛,黛二就动了动身体,
使身体的曲线在这只平展展的窄床上尽量找到几个较为舒眼的
支撑点,然后闭上眼睛。
黛二小姐感到一股热中带麻的气场罩在她的头顶和额头
上,那气场流动着从她的头皮表层深入进去。她的眼睛微合,隐
约可以看到气功师的双手平展着悬在她的头部,那气流随着他
的双手的缓缓移动而流动。黛二小姐只僵持紧张了几分钟,便
感到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那种舒服的柔软感从她的头部逐渐
向身体下沉,顷刻间爬满全身。
这种轻松与柔软之感激起黛二小姐某种潜在的意念,激起
她渴望看到某种奇迹的欲望,她几乎涌起了人类本有神秘力量
的信仰。
这时,黛二小姐感到气功师的手掌发射出来的气场开始从
她的头部向她的身体流动,被气流淌过的部位就感到一股灼热,
她完完全全专注于品味自己的感觉,这感觉先是隐隐的,尔后
那气流便强烈起来,像手指一样真实地触摸在黛二的身上。她
挣扎着从迷朦中猛地睁开眼睛,望见那气功师眼睛微合,立在
床边,双手在距黛二小姐身体两尺开外的空中向下悬举。什么
都没发生。她放心地喘了几口气,重又闭上眼睛。现在,黛二
小姐已明显地感觉到她身体里的某种东西为理智所抵挡不住地
被渐渐调动起来,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触摸、挤压、揉弄,于这
种力量撩拨起她对于约翰·琼斯那双宽大的手掌和怀抱的追忆
与想象。她努力地用意志去和这种欲念抗衡,结果这一欲念却
在她的身体上越来越强烈和集中地呈现出来,她几乎要叫了出
来……
这时,一个声音却从黛二小姐身体上空的一个部位响了起
来:“好了,起来吧。”气功师语调平平地说。这语调使她想起
了她在替缪一做婚前妇科检查时那个冷冰冰刻板板的女医生的
声音。
黛二起身下了床,气功师已远远地坐到一边的黑色转椅里
去,神情里透出一种正直的疏远,黛二为自己没有由来的想象
感到羞愧。气功师不动声色地静静察看了黛二一会儿,问:“有
什么感觉吗?”黛二说:“很有感觉。”气功师说:“你的气感比
较敏感,有的人是刀枪不入呢。”
黛二很想就气功治病的问题询问开去,谈到更深层次的东
西。可是,气功师说:“好了,下星期这个时候欢迎你再来。你
的头疼会好起来。”然后气功师站了起来,做出到此为止的身体
语言。黛二欲言又止,他的冷峻与镇定自若已经使她的内心热
情起来,她觉得自己格外安全。于是,黛二忽然象那种粘人的女
人一样,莫名其妙地想与他畅谈,她想说:“别这么快就分手,
跟我说点什么吧。”然而,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黛二站起身,
告辞了。
旋转下楼的时候,黛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爽。她一级一
级慢慢走下去,仿佛刚刚用生命敲开了一座神秘之门。黛二小
姐浮想联翩,形离神滞地走出于气功师的大楼,走在白得耀眼
的中午的街上。黛二小姐在阳光浓烈的街上走了很久,从一个
路口到另一个路口。每一步她都感到非同往日,尽管街景仍然
是往日那种大同小异的街景,她的心境格外好,满街平淡的烟
囱、楼群,电线杆、断垣、窗棂和废弃物都显得充满奇异。
这些天来,黛二小姐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无论气功师还
是工作问题。是那样一种随时准备投入、应战的高亢。
“谁谁”的信,几天前已由墨非亲自交到报社正社长手里。
墨非说,是在报社门口有个年轻姑娘请他转交社长。黛二很怕
把这么重要的信寄丢;或是明明寄到了,社长就是说没收到。人
心叵测,事情不能一开头就砸了。
缪一来过一次电话,说社长已给“谁谁”回过话了,此事
已转交负责人事的副社长老刘手里了。黛二拿着话筒半天没出
声,她心里很乱,觉得她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交谈了,像以前
那样的充满真诚地交谈。现在,连缪一的声音都变得陌生遥远
起来。她很想隔着电话线说点什么题外话,但黛二忽然一阵时
过境迁的茫然之感。于是,她只说了声:“谢谢!多保重。”
就挂断了电话。这电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永远地挂断了。放下
电话,黛二的神思乱乱的,半天才转了过来,镇定了情绪。
这一个星期,黛二小姐在多重等待与想象中度过。她很清
楚,工作问题是个切身实际的存在,气功师问题是个虚幻缈然
的存在。
星期一上午,她又如约去了气功师的诊所。一进房门,她
就从气功师的脸上感到异样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