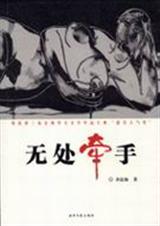无处告别-第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沙面前退而却步了。
黛二小姐蜷缩在浓郁的黑色风夜里,脸上一层无法遮掩的
四处无落、飘零无依的忧虑与茫然。她把自己的眼睛藏在墨镜
后边,天空和大地全变得黯黯淡淡。
黛二先去找缪一。她一身风沙按响了缪一家的门铃。这是
黛二回国后第一次去缪一家。在门外等了半天,终于有个很怯
的老妇人的声音隔门传出:“谁呀?”黛二说是来找缪一,那
老妇人才打开门。毕竟是“谁谁儿子”的家,连保姆都比一般
家庭里的保姆显得高傲。那老妇人请黛二换了拖鞋,抖掉身上
的风尘,才引她走进缪一的卧房。
缪一蓬着头,眼窝深陷,目光凄切松散,面色憔悴靠在床
上。黛二进屋的时候,缪一刚刚吐完一大场,这会儿才平息下
来,黛二没想到缪一变化如此之大,也没想到她的妊娠反应会
这么严重。黛二并不赞同缪一对于生活的选择方式,更不赞同
她要这个孩子,可缪一对自己的决定表现出一种非常理性的坚
定不移。黛二便知趣地不再说什么。缪一的表情显得冷漠,里
边掺杂着自卑与诡秘,这其中自然有非常切身然而又无法告人
的东西。黛二深知人的复杂与矛盾,深知做人之难,并不想多
询问什么,缪一那维护自尊的淡漠,使黛二把刚才一时涌起的
怜惜之情不露声色地藏在表情里边了。黛二很想说,有什么事
需要她,她会尽力。但她终于没有说。
缪一说,她无法一同去看时装表演,她要吐完一个月或两
个月说。
黛二坐在沙发里喘了几口气,就起身走了。她重新回到大
风里,她的长发飘飘扬扬,让那些躲在街两旁的商店,餐馆里
的感不到风的人看到风。街上人流涌动,摩肩接踵,嘈杂喧闹。
黛二望望拥挤在身前身后的人流,觉得自己在中国实际上从来
都是一个人孑然自处。
她凝望着人流,那人流很像冷漠的风,从远古一直流淌至
今,从太平洋东边的纽约城穿越大洋流淌至北京。它带着往昔
人们喜悦哀伤,带着悠悠岁月,从黛二小姐身边漠然滑过,然
后又顺着黛二小姐的一切流向远方和未来。它与她毫无关联,它
无法安慰她的心灵,无论在哪儿。她感到自己像一株被遗弃在
人流之河的堤岸旁的孤树,看着千百年的岁月流淌着的古老的
面孔沉思苦索,她看到每个面孔都是一个城堡,她被夹在无数
城堡之间倦怠不堪,忧伤自怜,像个真正的傻瓜。她再一次感
到某种真诚的东西正与她无可奈何地慢慢远离……
墨非已等候在长城饭店门口多时了,远远地见了黛二独自
一人被大风推拥着裹来,便迎上去拉黛二。
一见面,墨非就欢喜地告诉黛二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黛二问什么绝妙的主意这么兴奋,是不是麦三的美国梦有了门。
墨非就一古脑地把自己几天来的谋划讲出来。
仍然是黛二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工作问题。墨非那个报
社的副社长老刘专管人事,老刘是黛二父亲生前的好友,私交
甚笃,墨非知道这点,若黛二做为亡友之女去请刘伯伯帮忙找
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老刘有些特点全社众所周知,墨非十
分通情达理、善解人意,首先考虑到老刘的难处。老刘这人在
报社几个副社长中是学历最浅、资格最短、著作最少的一个,在
社里站住脚全仗走正直无私、不搞歪门邪道这一条路,这一条
是他唯一安身立命站稳脚跟使之在历次风波中立于不败之地的
法宝。墨非在社里工作多年,深知社里领导层的底细。正社长
在社里站得住是凭借热情,由于这种热请,使他拥有某种关系,
他常常出入这部长那部长家里,回到报社与同事言语间不免流
露出对这部长或那部长的亲密之情,总是抑制不住地象称呼从
小一起长大的老熟人那样称呼部长们的小名。缪一公公的小名
就常挂在正社长嘴边,墨非就听过不下五六次。
墨非深知官人们的利害关系,所以想出一个转圈法——即
由缪一的公公写个短函给正杜长,推荐黛二一颗赤子之心回归
祖国的怀抱,盼正社长给予解决工作问题,正社长与黛二无识
无交,肯定转手推给负责人事的副社长老刘接办受理,以便向
缪一公公交差。这事落在老刘手里便好办了。在上边转了一圈
最后落到老刘手里与这事从一开始提名就落到老刘手里非常不
同。转圈法虽然罗嗦,但老刘批准起来就非常正直无私、秉公
办事,非常理直气壮,不仅没有私情,而且帮了上司的忙,一
举而多得,真乃万全之策。
黛二听完转圈法就无可奈何地笑起来。墨非啊墨非,三个
约翰·琼斯加起来也想不出你这迂回战术,她望着墨非,望着
才年长于自己不过七八岁的却完全是另一代在夹逢里长大,做
人的朋友,心里一阵酸楚和悲哀。
一阵掌声把黛二和墨非的目光引到台上,正好麦三伴着浓
郁醇香的亚热带风光和音乐款款而来,她的眼睛左看右看,顾
盼流连,胯部风骚地摆动。灯光的色彩打到她半裸的身上,金
黄、肉红。她身上线条的流动感以及滚热的质感,压迫着人们
的眼睛。一股健康的生命力呼唤起台下人们情欲般的浓烈掌声。
黛二小姐低下头来,望望自己苍白的肌肤,便奇怪地站起
身离开了饭店,把自己埋没在夜晚的黑暗中。
黛二回到家,向母亲讲述了墨非设计的转圈法。她才讲了
一步棋,黛二母亲就全明白了,不用像墨非讲给黛二时那么一
步一步掰开揉碎、和盘托出。母亲毕竟是受过革命大熔炉久经
洗炼的人,一点即明。于是,黛二与母亲欢喜起来,总算有了
头绪。然后又是一番感慨:这世界有权力的靠权力,有金钱的
靠金钱,有屁股的靠屁股,不想用屁股又无权力、金钱的就得
靠智慧了。黛二小姐进而又想,无论战场还是情场,中国人能
够打败美国佬就全仗这智慧了。
喔,纽约!走回故土旧路才几个月,纽约已恍如隔世,远
在天涯了。
黛二小姐与母亲
黛二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黛二与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的
敏感日子真是过得举步维艰。倒还不在于一般缺乏男人的家庭
里那些最显薄弱的环节。比如;黛二小姐与母亲现在住的这套
房子,从黛教授在世时一起搬进来住,至今已有五年了,煤气
管道从一住进来就完好齐备,但五年来形同虚设,从来没有通
过气,害得黛二家每月把个媒气罐换来换去,好在当时黛教授
有辆公家小汽车。黛教授去世了,人走茶凉,曲尽人散,人去
车空。黛二小姐后来几次试着自己去换媒气罐,可她实在体单
力弱,纤纤的胳臂无论如何提不动那煤气罐,终于没有成功,但
这并不难,黛二小姐给墨非一个电话敲过去,事情就解决了。比
如,黛二家的抽水马桶,三天两头漏水,滴滴嗒嗒哗哗啦啦,水
声潺潺,缠绵不绝,黛二小姐左试右探,便掌握了水箱的构造,
出了问题,黛二三下五弄就解决了;家里的电线也常出故障,黛
二小姐对于电路简直无师自通,不仅任何电路故障难不住她,她
还可以把家里的电路改造修缮一新,弄得那些小彩灯、击电音
响、电动玩具,左闪右亮,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悦然。
黛二小姐与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的生活最为艰难的问题是
她们都拥有异常敏感的神经和情感,稍不小心就会碰伤对方,撞
得一蹋糊涂。她们的日子几乎是在爱与恨的交叉中度过。
黛二母亲在失去伴侣后,全部的注意力和情感都倾投到黛
二身上,这就要求黛二得付出与之相当的注意力和情感才能使
母亲得到平衡。可是这对黛二来讲太难了,她有自己更感兴趣
的世界,有自己的朋友、伴侣和未来。于是,注意力的不公平
使得她们的生活异常紧张,常常闹翻。
在黛二小姐的记忆里,这几年她的每一个生活阶段中,母
亲都会从黛二身边选中一位黛二小姐最为珍视的朋友作为她内
心里最搁不下的人。黛二母亲一感到被冷落或不被注意,就会
抛出这位“假想敌”与黛二小姐论战一番。
黛二小姐回国后与母亲的第一场“战争”是由缪一引起的。
缪一与“谁谁的儿子”同居很长时间以后,忽然有一天缪
一发现自己怀孕了,才急忙去办结婚登记手续的,时下的婚前
体检政策是必须先打胎才允许结婚。黛二小姐那时刚回国不几
天,听缪一说很想要这个孩子,黛二就托了人,冒名顶替代缪
一做了婚前体检。
当时正是隆冬二月。那天早晨六点钟,小闹钟就按指定时
间忠实而悦耳地叫了起来。房间里仍是一片昏暗,黛二小姐打
开床头灯,伸出胳臂拿过小闹钟,把闹针向后调了十分钟,可
闹铃还叫,黛二又把闹针向后调了十分钟,闹铃仍然不依不饶
地叫。到底是日本货,不把人闹起来不罢休。这么一折腾,黛
二小姐睡意已去,便披衣起床。叠被洗漱、梳头化妆、穿上外
衣,一切匆匆忙忙而又井然有序。要求空腹体检,便免去早餐。
缪一已在妇产医院门前等她了。缪一站在冷风里瑟瑟发抖,
神情忧郁,面色憔悴。她们走进了妇产医院,一股热热的暖气
伴着来苏味流进她们的鼻孔,缪一依然苗条,那时还一点看不
出是个孕妇,她的脸上带着歉疚。黛二很想安慰她没关系,可
她什么也没说,只在她不安的肩上轻轻搂了一下。然后她们并
排坐在一张绿色的长椅上,开始填写那份婚前体检表,姓名,年
龄。性别,婚史。月经周期,流量,颜色等等。
然后黛二小姐便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检查。静脉抽血;手
指验血;X光透视,妇科生殖系统检查(直肠检查);验尿……
检查生殖系统的妇科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齐耳,
面庞冷峻,目光威严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塑。她的眼光在黛二小
姐身上打量了一下,然后毫无表情地说:“上床。脱掉裤子,包
括内裤。把腿分开。”黛二小姐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动作缓慢地
开始脱。那女人转过身去,从柜子里取出一副消过毒的橡皮手
套戴上,又在一只手指上涂了些润滑剂,然后猛地转回身来,冷
冷地说:“快着!”黛二小姐噗嗤一声乐出来,那声音好像是一
位已经等得焦急万分、等得不耐烦了的很有权威性的情人发出
的,可是黛二小姐还没乐完,只觉女医生那戴了手套的一只手
指猛地一下就从后边戳进了黛二小姐的子宫。黛二一声尖叫。
“你干嘛?”女医生不紧不慢仍然用刚才那平平的语调说:
“你不是初婚吗?初婚就这样检查。”黛二小姐这才明白了什
么叫直肠检查,她在心里叫苦连天,无声地骂着他妈的。女医
生在黛二小姐的子宫、卵巢等等地方摸够了,就说:“行了起
来吧,没问题。”黛二一边提裤子,一边在心里发着狠:难道
我要你告诉我我没问题吗?”
黛二小姐从妇科出来,皱着眉头,苦痛不堪。见了缪一第
一句话就说,“真不明白男人搞同性恋搞个什么意思!”
黛二从来没有替谁受过这份罪,晚上回到家自然是说起这
事。母亲认为黛二对她关心太少,对别人倒满心热诚,言语间
就透出对黛二的不满。不满就不满吧,可是母亲话锋一转就骂
起那“谁谁的儿子”是什么狗东西,臭流氓!说缪一居然用这
种形式……下边的话就不好听了。黛二站着不动,盯住母亲那
发直的眼神,她觉得母亲大缺少对人的理解,同情,太不宽容,
如此小心眼神经质,毫无往日那种温良优雅的知识女性的教养,
近似一种病态。一股怒火直往黛二小姐的头顶冲,她忽然一字
一顿郑重警告母亲:“我不允许您这样说我的朋友!无论她做了
什么,她现在还是我的朋友。您记住了,我只说这一次!”然后
黛二转身就走了。她一个人在光秃秃的北京冬季的街头毫无目
的地走,她为母亲难过,为她的孤独难过。她懂得母亲。
第一场战争之后,她们又发生过无数次争论,黛二小姐厌
倦已极,每当这时,她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离开这个用爱心来
折磨她的女人。她甚至已经看到了自己和母亲这样单身下去的
生活前景早晚有一天,母亲将把黛二小姐视为世界上第一
号敌人。
每当这时,黛二总是丢一句:“有病!”然后摔上门,躲
进自己的房间。黛二小姐的屋门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她平时
总是把玻璃用窗帘遮挡住,她很不习惯自己在房间里的活动
譬如沉思默想、读书。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