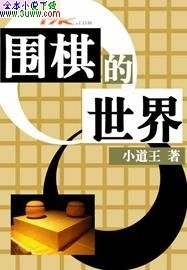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5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成员,并为会议进行勤奋的准备,每周全力投入公司问题的时间也不太可能超过两三个小时。某些人坚持认为,这种局限性正是欧洲所拥有的那种制度的理由之一,那种制度下,董事积极得多,构成了公司管理的第二层面。更积极的董事也许能更轻易地发现问题,尽管长期而言欧洲也有其自己的公司治理问题。不管怎样,欧洲制度也有其真正的缺点,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会管理使公司不那么灵活,适应力不那么强,不那么愿意尝试和接受风险,不那么具有决策效力。
综合来看,我更喜欢我们公司治理制度——有一个更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外部董事的卷入更有限。许多人认为,在我们的制度下,尤其是得到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加强后,信息流向董事会的有效性和欧洲制度的一样强。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管理不善和公司灾难的可能性稍大些,我仍认为,从长期的总体经济业绩的角度来看,我们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成本。
导致纳塞尔最终去职的决定性因素是有大量证据表明福特公司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改善。一年已过去,纳塞尔仍能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但积累起来的负面证据似乎更多些。如果能获得更多的时间,纳塞尔也许能使福特公司情况好转,实现那些非常有必要的变革,但风险在于如果他不做这些的话,时间可能过去得更多。权衡两边的风险后,董事会决定转向,任命比尔为首席执行官。
当比尔说他准备自己接管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以使公司重回正轨时,我告诉他我认为董事会将会完全支持。但我接着问他:“你是否考虑过怎么对媒体概括你所做的一切?”我警告比尔,媒体可能用各种负面的方式来描绘这种变化。“你不会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告诉人们真相,”我说,“你只有一天。”
比尔需要谨慎处理他要传达的信息。一方面,他因为关心公司而介入,这并不是什么夺权。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把注意力全吸引到公司的问题上来,或是使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听起来比实际的大。这是对这一原则的另一个证明,即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来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问题是赤字支出和增税谁是谁非,或是改善福特公司与福特陷入麻烦或董事会政变谁真谁假。
我对比尔的建议是一定要非常小心措辞,并采取使媒体接受自己观点的战略。他必须在新领导下对未来的建设性观点,而不是不恰当地强调问题或过去的可能使福特公司看起来像陷入麻烦的公司的过去冲突。我告诉比尔,在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是要求汤姆·多尼伦帮助我筹划这种沟通战略的,我建议他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这并不是说比尔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而是因为公司的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政治觉悟,尽管这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后来的结果表明,比尔很好地处理了过渡——不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公司内——而贾克建设性和大度的态度对此大有帮助。比尔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显然已经稳固。
在返回纽约一段时间之后,朱迪和我与六个老朋友一起坐着小船在西西里游玩了一个星期。这些老朋友中包括戴安娜和列昂·布里坦,我们在耶鲁法学院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随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了内政大臣。一天,当我们在岸上徒步旅行时,戴安娜评论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政客在下台后无法释然,并试图以各种方式赖着不走,总想重获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
第二部 第47节
我说我对某些美国政治人物有同样的印象。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出色地担任过许多不同的高级外交职位。在相似的心境下,他曾对我说,某些人对自我的认识如此依赖于他们在华盛顿的位置,以至于他们永远都用早先的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而另外一些人,迪克补充道,把他们在政府任期看成是非常特殊的经历,而继续关注他们自己在将来要做的事。
戴安娜和迪克所提出的看法都是我常常注意到的某些东西的延伸。严重依赖工作来确定自我的人就会依附工作,依附那些权力比他们大的人。而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不依赖于工作的人,则有能力离开,从而产生出一种心理独立感。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能记得早年在高盛公司时的岁月。进入政府后,我当然没有曾拥有的金融自由,但仍然有能离开并过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感觉。这使我的观点更为独立和坦率,并能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工作。
在同一次谈话中,戴安娜·布里坦还提到一位拥有高贵的英国头衔的朋友,在生意上也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但从未成功实现一生追求的抱负,即成为下议院议员。他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总是对那个未能获得的荣誉表示极大的遗憾,而不是自豪地回想所有那些他已经获得的成就。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杰出的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故事。尽管他备受尊敬,却总是因自己从未实现过的、想成为首席大法官的抱负而心疲力竭。即使是极其成功的人似乎也总是想得到某些他们无法得到的东西。内心的需要促成外部成就的实现,但外部成就却永远不可能满足内心的需要。这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将会是长期性的。
我在私营部门的时光是好坏参半。但不管怎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总是好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和花旗集团公司达成的协议要比我希望的好得多。我埋头于一系列令人痴迷的实质性和管理问题,我处于一个非常出色的机构的核心,却又不必承担经营责任。在花旗集团公司之外,我也非常有幸能深深卷入我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涉足那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机构如哈佛学会、本地倡议支持组织、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西奈山医疗中心。我并不想念政府的那些活动或津贴收入,尽管我确实想念一起共过事的人,也不赞成我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我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我就是误解了自己。某些人似乎很擅长控制其介入水平,但我从未能那样行事。离开政府后的经验强化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不管走到哪儿,你自己总是跟随着你,因此,你最好要知道自己是谁。在不确定的世界贪婪、恐惧和自满第十二章贪婪、恐惧和自满
1999年7月,我回到纽约,重新投身于市场和金融的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在我离开的6年半里变化有多么大。我儿子杰米当时在投资公司Allen & Co·工作,他告诉我说,即使你觉得自己一直保持对情况的了解,变化实际上还是比你所想的大得多——因特网和技术只是部分原因。在开始更深入关注所发生的事后,我才认识到杰米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任期即将结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请我加入他建立的一个非正式的团队讨论市场结构,我开始更充分地理解这些变化的技术方面的内容。亚瑟和其他人觉得,新技术应当会使更好、更有效率的业务经营方式成为可能,而实际上,某些市场参与者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为保持其传统优势而奋斗,而大公司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来者为自身的利益正倡导变化,这个研究小组为这些提供了某些深入的见解。莱维特小组并不打算得出确定的结论,但这一讨论确实帮助我理解了过去改变并继续改变着金融市场的技术和其他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是新的交易活动规模。据我所知,主要交易所的日交易量增长系数为5倍——比如,从我在高盛的最后一天到我重返纽约的那一周,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已经从2110万股增至11亿股。但如果真要对这种增长的意义有所感觉,你必须与金融业有密切关系。比如,由于市场的增长,私人股本业务和对冲基金迅速发展。1992年,管理着1000万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就算是规模大的。而在1999年,许多基金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有几家管理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基金的数量也翻了一番。
在纽约,繁荣所造就的精神状态带来的社会后果处处可见。人们在市场上赚来大把钞票,其支出也急剧增加。我听说有些新人不在纽约结婚,而是飞到欧洲去举行结婚庆典。人们建起了豪宅——通常是第二或第三居所。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朱迪和我想搬出从70年代初就一直居住的合作公寓,并且找到了一处我们喜爱的公寓。我们的出价比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虚高的报价低得多,但我们的经纪人认为很合理,然而却有人出了比报价还高的价钱。我们放弃了寻找新公寓的努力。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很是怪诞的。
身处股市繁荣几年之后,许多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经济上的极乐之境。1999年末,网络和电信股票价格仍在继续迅速上升。那年夏天我重返纽约,纳斯达克指数略高于2500点——年底之前他就会达到4000点,2000年3月10日会达到5049点的高点。人们那时听到的各种评论会让人想起20年代时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歇尔的遭遇。在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周,费歇尔发表了著名的评论说股票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永久性的高平台”。世界真像市场所想像那样变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如果认为市场有点疯狂可能更靠谱。我记得曾在一份金融杂志上见到过一个图表,他描述的是所有上市交易股票的市值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关系。直到1996年,股票市场总值也从未高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毕竟那是我们在美国境内所生产的所有货物与服务的总值。实际上,1925年以后二者的平均比例关系是略高于50%。1929年在市场最高点时,这一比例是81%。但到2000年3月,已达181%。纳斯达克的价格收益比的增速甚至更快。80年代,平均为18·5。2000年3月,达到了82·3的最高点。那时,信息技术股票的收益占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总收益的大约16%,而其市值却几乎是这一数字的2倍,达大约36%。
某些我非常尊重的人并不认同我对许多被广泛接受的有关股市观点的怀疑。其中一位是斯蒂夫·埃因霍恩,我和他一起在高盛公司共过事,他是我们投资政策和股票选择委员会的主管,此后是全球研究部的主管。斯蒂夫曾在十多里一直名列《机构投资者》评出的最出色股本投资战略家之一,担任了几年纽约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副董事长。我把本章的草稿发给他请他评论,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他到高盛公司的第三周,就和我在有关一次购并的套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与他共事的伙伴提醒他,就他在这家公司开始职业生涯而言,这恐怕不是明智之举。于是他到我的办公室来道歉。他说当时我对他说不必道歉——以后也请他继续与我保持不同意见。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以令人振奋的意见冲突为特点。斯蒂夫认为,长期投资者通常应当以股本方式持有资产,因为历史上他比其他种类的资产表现更好。他并不认为90年代末的市场水平反映出的是集体疯狂。斯蒂夫认为,由于强有力的经济基本面和低利率的环境,90年代末的股票价格尽管按历史标准来衡量已经很高,但除技术部门以外并非明显地不理智——因此只需通常的市场调整。
我的看法是,90年代末的情况是周期性的投资过热插曲的又一例证,市场的整个发展历史中这种事一直在发生。近期发生的几次我记得很清楚:60年代人们对混合大企业极有信心,他们的股票价格比收益高许多倍;70年代初的所谓“漂亮50家” ——诸如宝丽来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有创新性产品或营销方法的公司股票,他们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70年代末的“能源宝贝”;80年代初西南地区的房地产泡沫。90年代初生物技术公司的泡沫已经预示了90年代末的另一次生物技术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思维所导致的过度借贷。
但涉足市场的人们似乎并未从过去的插曲中得到教训。他们总是认为,这一次不同,理由是这些。而这些理由通常是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投资者过度引申了这些发展,导致了市场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可危及经济基本面的活力。你可能认为人们会从人类过去的集体金融经历中得到教训。由于某种理由,他们没有。
第二部 第48节
2000年2月,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