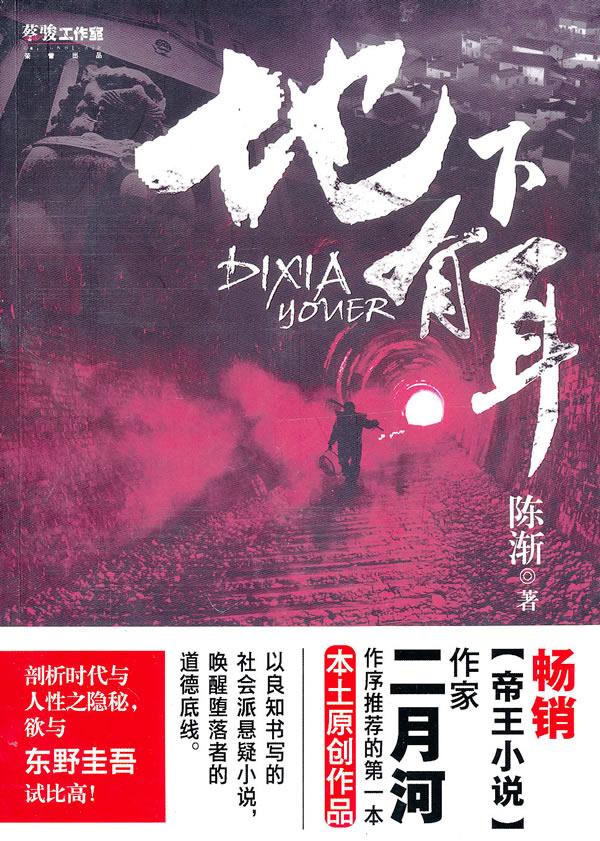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党-第5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柯子炎还有情况要透露,与军事情报无关,比较私人。刚才捕住老三时,他说过彼此想念,其实他知道老三想念柯特派员只是调侃,老三真正想念的是自家老父钱以未。老三一定提审过刘树木,知道行动组追踪金门,所以迫不及待也跟上岛来。如此看来钱以未可能确实就在本岛,大家继续努力,也许钱家父子可以在牢里见上一面。
“只怕不太容易。”三哥说。
“不找到哪里可以。”柯子炎说。
柯子炎把右手掌张开,举到面前,让三哥看他的指头。窗外投进的阳光从他的指缝照过,他的指骨畸形被光线描述得非常明显:食指与中指弯曲变形,骨节膨大。
他这两个手指头本来可以用来刻字,被刑讯打折后再也拿不了刻刀,但是不妨碍开枪,也不妨碍用匕首。这么多年里,他用这两个指头杀过不少人,有日本特务,有共产党,还有无辜人员。他在杀人时从不手软,冷酷无情,同僚以“血手”称之,否则他不可能得到信任,从共党叛徒干到中校特派员。在抓过、杀过那么多人之后,他心里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抓住一个人,把这个人吊起来折磨,打断其手指,伤害其家人,逼其招供、投降,然后枪毙。这个人是谁?就是钱以未。他挖掘“钱以未连线”不遗余力,除了要争功讨赏,也因为心怀恨意。他与钱以未是两代人,彼此从未见过面,只因刻字神交,何来怨恨?因为他本可安安分分做一个普通人,凭一把刻刀吃饭,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不必家破人亡,伤筋断骨,人不人鬼不鬼变成“血手”,活为行尸走肉,死后下油锅万劫不复。追根溯源是共党宣传蛊惑害了他,钱以未罪有一份,当年钱有两枚长方章让他印象至深,直接印入他的脑间,把他“赤化”了。
“说法真怪异。”三哥说。
“我自认是变态。”
如果钱以未落到柯子炎手上,经不起刑讯而投降,柯子炎会感到很满足,因为不仅仅他会投降,他曾经景仰的钱先生也一样,彼此不分高下。钱以未不投降,柯子炎会把他亲手除掉,无声无臭,悄然消失,算是成全钱先生,也是讨个道理,请钱先生为柯子炎曾经有过的遭遇和不幸负责。让钱以未死于己手,以命相偿,让“钱以未连线”在自己手里挖除,而自己还活着,这种感觉很好。行尸走肉也要强于死人死线。
“其实你无能为力。”三哥说。
三哥断言柯子炎找不到钱以未,更挖不掉其连线。这条线的关键不仅在人,还在其维系,是什么东西把这些人维系起来?是共同的理念、信仰和精神。搜捕杀害钱以未并不能伤其精神,毁其维系。这种维系不仅存于地下党内部,更在两岸城乡里巷之间,如果它生于千万百姓心中,融在大家共同的历史血脉里,“钱以未连线”就永远切而不断,无论时日,不管风雨,它总会一再觉醒,断而再起,死而复生。
“你可以了解钱亚清怎么变成钱以未。”三哥说,“秘密其实都在这里。”
柯子炎说:“这个来历我知道。他本是乙未,不是以未。”
三哥说:“说来也不算秘密,其中之要就是信仰与精神。奋斗胜利都靠这个。”
柯子炎嘲讽:“钱家老三自以为是,其实自己是鹧鸪是鸽子都没搞清楚。”
三哥说:“我清楚狗嘴里没有象牙。”
柯子炎称自己嘴里还真是长有象牙,此前含而不露,事到如今,可以一现真容。
老三口口声声父亲长父亲短,心甘情愿当孝子,为自己从未谋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个钱以未,不惜冒死潜上金门,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钱以未的儿子。
三哥说:“少来狗叫。”
“说的是实话,信不信随你。”
柯子炎原本不知三哥别有来历,只知道是钱家老三。去年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厦门渔港小巷外初次交手,柯意外发现老三长得跟钱家人大有不同,真是鹧鸪鸽子不一般。后来了解,原来老三不是钱以未元配所生,钱以未在台湾还有别的女人。柯子炎感觉这是一条线索,特地安排人在台湾追查,却发现钱以未在台湾从未再娶,老三查无出处。为这件事,台湾一组特务掘地三尺,梳理日据时期大量档案,终于从一个已经回日本去的旧监狱官处查到线索。原来老三的生身父亲叫林鹏,是旧日台湾地下反日组织成员,属于钱以未那一系统。老三出生之前,林鹏被日本人捕获,死于刑讯。其妻同时被捕,因怀有身孕,且知情不多被释放。其后几年日本特务一直监视林妻,怀疑她与地下组织还有联络。有一次一个疑为地下联络员的女子偷偷潜到林家,被特务发现,组织突袭,林妻持菜刀抵抗,帮助那个女子逃走,自己被日本特务用刀砍死。此案前因后果日本警察心知肚明,所谓“遇劫身亡”之说实为故意作假。林妻亡故后老三沦为小乞丐,钱以未在狱中得知,设法托人将他送往厦门,声称是自己的儿子。林鹏夫妇原本都是钱的部下,钱以未照料同志的遗孤也在情理之中。钱家人因为老三长了个高颧骨,认定是自家人,其实鹤鸪鸽子都是鸟,闽南台湾一带颧骨高的人多的是,并非只有钱家。
“那两个死的才是你亲生爹娘。好心告诉你,让你到阴间才好相认。”柯子炎道。
三哥冷笑:“鬼话一概不听。”
柯子炎清楚老三早已刀枪不入,他不指望老三知情后翻然悔悟,愿意供出假父钱以未的下落。说到底钱以未和林鹏夫妇同样都是共党,老三怎么说都是叛逆崽子,子承父志,无论认谁作父,落到柯特派员手里都一样。此刻柯特派员想知道老三喜欢哪种死法,老虎凳刑讯,还是零刀碎割?可以自选,他会酌情关照。
三哥说自己从来不信邪,也没怕过死。当年日本人当着他的面打死他的老师,引他走上这条路,从那时起他出入枪林弹雨,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我还要看你下地狱。”三哥说。
柯子炎批评老三不如老四。钱家小妹在厦门被围,举着一颗手榴弹,拉弦还喊卧倒,知道饶人一命,只不过不被领情,终究死于乱枪,说到底怪不得别人,是她自己活该。老三老四不是一个种,却出自同一门,胆大敢死,老四回到厦门,老三来到金门,一个跟一个步入死地,难道相信老天永远跟自己同边?相信自己子弹打不死?既然一切都因信仰,有信仰的人会胜利,那么就胜利吧,有信仰的人不怕死,那么都去死吧。有朝一日有信仰者统统死光,世界上剩下的全是行尸走肉,岂不天下大同。
从柯子炎嘴里听到澳妹死讯,不由三哥咬牙切齿:“等我替澳妹讨你这条命。”
柯子炎道:“来生再说吧。”
不待来生,几小时后,凌晨二时时分,枪炮声响彻金门,天地为之震撼,金门战役打响。数千解放军战士凭借渔船强渡大海,占领滩头阵地,迅速向纵深地带穿插,岛上守军拼命抵抗,到处枪声连片。
特务组所驻村庄离滩头较近,枪炮声排山倒海一般惊心动魄。特务匆促撤退,迅速离开驻地,三哥被反铐双手拖上吉普车。
三哥哈哈大笑:“你们死到临头了。”
柯子炎骂:“走着瞧。”
几辆吉普车离开驻地,沿着乡村土路快速撤退,天黑地暗,道路难行,吉普车亮着灯,开得跌跌撞撞。翻过一个小山头时,前方突然响起密集枪声,一支进攻队伍突破防线,打过山头,向公路猛扑,黑暗中一串串弹光飞过山坡。
柯子炎大喊:“是共军!快冲过去!”
三哥突然在车里跳起来,用劲全身气力拿身体撞击前座司机。吉普车突然失去控制,蹿出道路翻下山坡。山坡下有一片开阔地,早先涂营二连在这里埋设过地雷。
吉普车触雷爆炸,三哥与柯子炎同归于尽。
尾声
来年春天,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漳州一处老房子里找到了母亲钱周氏。母亲已经离开厦门,带着外孙吴亚明回老家定居,小巷木屋的主人从南洋回来,房子还给了人家。政府要给母亲安排住所,母亲坚持回老家生活,因为丈夫钱以未、女儿钱玉凤、亚明的父亲吴春河和大儿媳陈蕾都知道这个地方,他们要是回家,在厦门找不到她,一定会到这里,这里有他们的东西,她要在这里等他们回家。
老房子里有许多旧物与母亲相伴。当年担心特务搜查,母亲偷偷把不少东西搬到此间藏匿,多为父亲钱以未的物品,有他留下的书籍,一抽屉石头,他的篆刻印章——其中有一对让特务柯子炎耿耿于怀、遍搜无着的长方章,它们藏在这里,印文分别是“山河破碎”和“天地更生”。
工作人员劝告母亲节哀,烈士们不可能回家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母亲拒绝安慰。她坚持认为自家小女儿去了台湾,可能是去寻找父亲。待台湾回归,他们自会归来。大女婿吴春河与钱以未一样曾经多次失踪,消失数年,都说已经死了,最终他们又都再次归来。死而复生在这个家不是稀罕事,母亲永远心存希望。
人民政府给母亲发了抚恤金,在母亲所居旧屋墙上钉上一块木匾,匾上题有“满门忠烈”四字。
五年后,有一封信自香港寄到漳州。小学生吴亚明给母亲读信,他一读信头“亲爱的阿姆”,母亲就大叫:“那是谁?是谁!”亚明赶紧看信末署名:“是小姨!”
确实是我,于貌似长眠中“觉醒”。
我没有死于美式手榴弹,也没有死于乱枪,我之存活因为意外,也因为孙力以命相换。我拉了弦的手榴弹竟然是颗哑弹,当特务在我眼前卧倒一地之际,它没有爆炸。当时我整个人蒙了,呆站着看特务们趴在地板侧头翻白眼。孙力突然扑上前连开几枪,林家团被他当场击中,特务们一起回头朝他射击,注意力被忽然引走。我身边意外地“吱呀”一声,一个门扇洞开,我不假思索当即窜进门里,回身把门关上。
这扇门怎么回事?当时我被特务逼到墙角,身后是一面高墙和一扇紧闭的木门,高墙里边围着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园子,园子已经残破,我所据院墙这扇门是后门。偏巧有个女乞丐住在那破园子里,女乞丐年纪很大,耳朵很重,外头枪声砰砰乱响,在她耳朵里可能像是放鞭炮,她打开门察看究竟,适时把我救了。
我逃进园子后立刻向前飞跑,仅仅几分钟,特务撞开被我反关的后门冲进园子,园中女乞丐夺路逃跑,被他们射杀,我攀上另一侧院墙边的一棵树,爬到墙头上。我听到柯子炎大喊“开枪”,耳朵里一片枪响,震耳欲聋。我被乱枪从墙头打下,掉到墙那头,那边是面斜坡,坡下就是海湾,我从坡下一直滚到海里。落海后我挣扎着游开,抱住海浪上漂浮的一块破木板,随即昏迷不醒。恰有一条军用小艇经过那块水域,艇上当兵的发现我血淋淋漂在海上,把我捞起来送到附近一所军医院里。
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复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托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系。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别做声。”他小声道,“回见。”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觉醒”。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历和意思。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