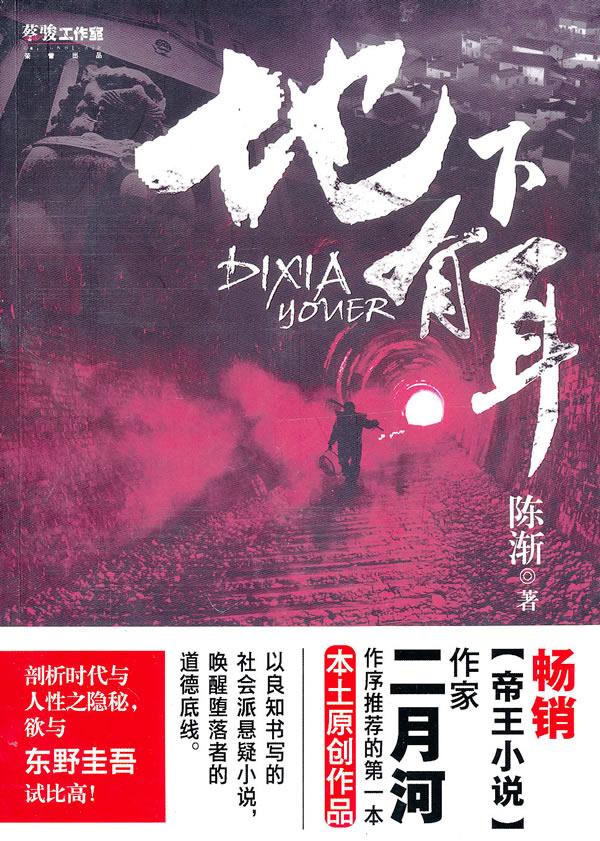地下党-第2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易太太怀疑特务有内应,否则他们从哪里得知吴被关在庄园里?其纵火计划也要内应才能得手。假和尚一问三不知,不清楚哪个是内应,易太太把吴先生提出来审,吴对特务的计划和内应也都一无所知。易太太给他看了假和尚带上山的信,他承认写信的“弟两火”是保密局特派员,也承认特务派假和尚上山联络,确实可能准备纵火劫人。但是即使特务打上山,他能逃出庄园,也不会跟特务走,因为他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是要追捕他,不是要救他。
“你怎么又变成了共产党?”易太太追问。
吴先生称他的自治同盟就属共产党,原来不清楚易太太的底细,所以不能讲明白,现在看来易太太不是国民党,所以可以承认。
“你去游击队干什么?”
“我的任务是接头。”
他称自己从台湾过来,任务是建立联络。这件事情对两边都很要紧,生死攸关,他不能多说。易太太把他交给游击队,情况自会清楚。
“撒谎!”易太太呵斥。
易太太已经在老齐那里核实过,共产党不认这个人。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哪里会费这么大劲救他?此刻他忽然改口自称共产党,又是台湾又是接头,一定是想拖延时间,隐瞒真相。易太太下令用刑,痛打,打到说实话为止,却不料他始终就是那些话。易太太发怒,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还不说实话,那就砍头,让他到阴曹地府去跟阎罗王接头联络。
“易太太不能这样草菅人命!”他抗辩。
“承认特务可以不砍头。”
他死活不承认,咬定自己就是共产党。一怒之下,易太太下令把他和假和尚一起砍头,以此绝了山下特务纵火劫人计划。
三哥大惊:“这就砍了?”
真是砍了。尸首丢在东山坑下。
我们立刻赶到东山坑。那是村子东边一处悬崖,悬崖四边都是山岭,有一条山涧从坑底流过,潜到地下溶洞里,所谓东山坑实际是一块塌陷的溶洞。三哥让我留在坑上,他和一个同伴借着崖岸的树木和绳索攀下,在坑底找到了姐夫。
他居然还有一口气。
奉命砍人的自卫队员不知是因为懒惰,或者出于同情,他砍了假和尚,却没砍姐夫,只把姐夫推下悬崖,交差了事。姐夫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而且被团团捆住,哪怕摔不死,也没有力气爬上悬崖,只能在坑下自己慢慢死去,让野兽啃成骨架,让蚂蚁浑身吃光。直到推他下崖那一刻,那人还想让他供认特务。姐夫说:“别麻烦了,无论打死砍头,我都是共产党。”
大哥说过,难得春河能吞忍。姐夫其实不只能吞忍,他是坚韧不拔。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台岛迷局
姐夫吴春河还在游击队医疗所的山坡上一瘸一拐,即打定主意返回台湾。
这次一瘸一拐与他擅长的伪装易容无关,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黄狮坑村的牢房受尽酷刑,为了撬开他的嘴,易太太的手下丝毫没对他客气。他的两个小脚指头给逐一弄断,有如当年他嘴里的牙齿被一一拔除,不同的是拔牙属自愿,断趾纯粹是被迫。易太太的“自卫队”非国非共,亦民亦匪,打仗不讲究计划,刑讯犯人也乱来,老拳齐下,毫无章法,他们拿姐夫的脚指头下手,用手指头硬掰,上刑的受刑的都很难忍受。姐夫痛入骨髓之际,居然会开导那些刑讯者去找小铁锤,让他们拿那东西砸扁自己的脚指头,这样彼此都会痛快些。被三哥救出后,头几天他的脚根本不能沾地,但是他紧咬牙关,很快又站了起来,拄着拐棍于山坡上一瘸一拐。
几乎没有谁相信他还能活下来,无论是刑讯他的,还是看着他给抬出东山坑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姐夫经历过的酷刑,很少有人经受了如此折磨还能活下来。只有三哥钱世康认定姐夫可以挺住。
“我们家都行。”三哥坚信不疑。
果然如他所料,姐夫吴春河挺过了这一关。
一位地下党负责同志专程从闽西赶来问候姐夫,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姐夫吴春河的接头任务终于完成。以他的状况,此刻应当安心留在医疗所里养伤,直到解放大军到来,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几天后南京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残存时日已经所剩无几,盼望中的胜利和新生即将到来。
吴春河说:“现在台湾越发重要。”
欢欣鼓舞之际,有一件事让他忧心忡忡。
吴春河上山接头那天,交通员小张被捕,酱油铺交通站被特务破坏,事发突然,却非偶然。那几天当局接连出动大批军警,加上宪兵与特务,在各地组织大搜捕,有数个交通站被敌破获,一批地下党人员被逮捕,白区地下工作受到重创。
这是因为出了叛徒,叛徒代号“老徐”,原是地下党一个白区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老徐那一天离开白区,拟上山回机关开会,途中折进一个村庄,他的妻子和孩子隐藏于村中。老徐在家里住了一宿,没料到自己早被便衣特务跟踪,特务一直等到半夜后,待一家人熟睡、警觉放松之际突然冲进屋里,将老徐及家人捕获,老徐没有撑住,叛变招供。三哥潜回厦门时曾告诉我“出大事了”,说的就是出了叛徒。上级非常担心前来接关系的吴春河被捕,导致台湾地下工作受破坏,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找到吴的下落。
所幸吴春河绝处逢生,终于平安生还。但是他的下级谢德灵出了事情。
姐夫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被易太太的自卫队刑讯逼供之初,自称归属于闽南人民自治同盟,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它与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有关。谢德灵等人参加“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当局搜捕,撤往大陆,在闽西南交界地带拉起一支武装队伍。由于他们与本地地下党组织没有隶属关系,联系尚未建立,如果以共产党名义开展活动,担心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经与吴春河商定,暂时打出“人民自治同盟”旗号。这一次吴春河返回大陆,目的之一就是与当地组织接上关系,安排谢德灵这批人的关系转交,却不料事未开始即已生变,由于老徐叛变,谢德灵意外被捕。
谢德灵与本地地下党组织并未建立联系,怎么也受叛徒牵连?原来谢德灵活动区域处于几县边境山地,天高皇帝远,当局统治力量薄弱,历史上多出聚众山林者。谢德灵拉起队伍之前,当地有小股地下党游击队,也有数伙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匪。前些时候保安团进山“清剿”,谢德灵联络一股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以及地下党游击队,三方合作,有守有攻,把保安团的“清剿”破坏了,从此敌人特别注意他。老徐叛变后,敌人得知谢德灵部不属本地“土共”,即设计击破。他们让老徐出面,以地下党负责人希望会商为名,通过与谢部协作过的人员联络,把谢德灵骗出来。谢不知道当地出了叛徒,对方主动联络,谢一时高兴,放松警惕,落入圈套,于下山接头时被密捕。几天后谢部遭遇突袭,队伍损失大半,残余人员撤离原有区域,遁往深山。
吴春河闻讯,非常焦急。
“谢德灵眼下在谁手里?”他了解。
竟是柯子炎,柯特派员。
“谢德灵叛变了吗?”
“血手”柯子炎心狠手辣。捕住谢德灵时,柯问都不问,当着谢的面,把跟随前去的三个战士一起砍头,尸体推下村头粪坑,谢当场昏倒。目前情况还不明朗,敌人突袭谢德灵部,并不意味他已经叛变。柯子炎不遗余力深挖“钱以未连线”,企图切断大陆与台湾的地下联系,吴春河是他一大目标。谢德灵是吴的下级,参与过台湾地下工作,知道不少情况,落网后柯子炎会如获至宝。如果他叛变,必危害极大。
因此吴春河决定尽快返回台湾。
三哥赶到医疗所极力劝阻,姐夫不听,只问:“澳妹怎么样?”
三哥说:“她回厦门了,很安全。你危险。”
三哥劝阻姐夫,不是个人意见,是游击队领导的意思。如果谢德灵出问题,姐夫返回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眼下这个时候,大陆之敌已经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虽然还不时发起“清剿”,力量却已不足,游击区在迅速扩大,这里比白区安全。姐夫刚刚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为此差一点牺牲,身体还需康复。台湾方面的工作眼下有人负责,姐夫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交通线布置应对,不必亲自冒险前去。吴春河不属于本地组织体系,领导不能命令他,却还是郑重跟他谈话,再把三哥派来说服,建议吴春河不要返台,游击队愿意就此向上级作出说明。
姐夫说:“我放心不下。”
他和他的同伴在特殊环境之下,极其不易地在台湾一点一点开辟工作基础,付出无尽心血,忍受百般磨难。所谓“难得春河能吞忍”,其实那边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忍辱负重。现在这些人和工作基础面临危险,姐夫对所属地下组织整体情况最了解,应变经验最丰富,这种时候不能躲在一边。
“柯子炎设圈套等你,回去正中下怀。”
三哥断定谢德灵事件很可能是柯子炎一手制造,目标就在姐夫。吴春河被易太太扣押时,柯子炎不惜纵火劫人,说是营救,实际是想把他抓住。吴春河脱险留在游击队,柯子炎鞭长莫及,转从谢德灵处突破,把吴春河引出安全区域,他才可以下手。
吴春河说:“对付这个特务得走在他前边。”
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托,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