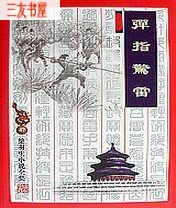大宋金手指-第9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水稻稻种的优选,加之水与土壤的优沃。使得如今流求熟田的产量极高,仅淡水田庄地水田,年产稻谷便有六十二万石。
淡水渔场是随着江南制造局的逐渐搬迁而来的,起步得略晚了些,目前有渔船五十余只。鱼塘一千七百余亩,每日渔船能捕来鲜鱼过五千斤,虽说尚嫌不足。但展得极快。赵与莒也早有指示,淡水的渔场须得抓紧,这不仅可以为流求居民提供充足的动物蛋白,更重要地是可以培养出一批藏于民间的水手。
较为特殊的便是鹿苑,鹿苑虽说起了这样地名字,里面也确实驯养了数百头鹿,可主要养的还是猪、牛、羊、马等大型牲畜以及家禽。因为旱田里种植了大量的苜蓿等饲料,稻谷又累年丰收。故此这些禽畜可以大量圈养。为饲养这些提供肉蛋的禽畜,倒有两千余人得整日忙碌不休。
依着赵与莒的安排,禽畜粪便是要经常清理的,一般都是倒入渔塘之中,充作渔饲料,而过上一年左右,这些鱼塘又会被放干,将沉底的淤泥翻出来,做为肥料埋在旱田或桑树、果树之下。
“四娘子。官人这方法真管用。”负责农场的是郁樟山庄地老家人赵恩,他是个不紧不慢的性子,说起这田地之事,便满脸都是笑。
“办得极好,俺记下了,会和官人说的。”杨妙真也是心情舒畅,从赵恩给她的数据来看。不仅淡水初等学堂的孩童们每日都有肉食。便是普通的人家,每隔三五日也可以吃到一回蛋肉。当初她在山东东路的时候,这可是大多数义军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这一切,都是源自自己的那一趟郁樟山庄之行。
想起赵与莒,杨妙真脸又浮起了红晕,她轻轻皱了一下眉,回忆起自己与赵与莒相识以来地经过,越的觉得自己看不透他。这世上仿佛没有他不知晓的事情,甚至远在江南,他便知道山东东路有个杨妙真。
一切尽在他掌控之中,胡人与金国在北疆的战事,海外流求的气候与物产,几乎事事他都了如指掌。
可此次将自己打来流求,难道说是有什么事情是他无法掌握的么?
想到此处,杨妙真神思恍惚起来。
她正心不在焉之际,一个推着小车的少年大叫着从她身边冲过去,杨妙真这才惊醒,慌忙避开,眉头皱了皱道:“这小子有几分眼熟……不就是那于竹么?”
推小车地正是于竹,他光着膀子,腰间扎了护卫队特有地那种厚皮带。小车里装着的是一车砖,这种独轮小车在淡水极普遍,最强壮地小伙子可以用它推着六百斤的稻谷在田埂上跑得飞快。
“现今正是冬日,护卫队的人帮忙清鱼塘呢,若是只靠着我们,哪里做得完!”赵恩道。
“这小子进了护卫队?他不是被汉藩治得极惨么,怎么还巴巴的凑到护卫队里去?”杨妙真微笑道。
“人便是这般怪,他年满十七,依着咱们这的规矩,年满十七便可选择,是继续在初等学堂就学,还是进入单位分配工作,旁人大多都是继续就学,他偏要干活,而且还非得去护卫队。不过这小子如今改得多了,虽说还是咋咋唬唬的,做起事来却很是肯出力气。”赵恩也笑了:“小人常对汉藩说,这便是第二个他。”
李邺当初的糗事,杨妙真还是自秦大石等人处知晓了一二,心中也颇为感慨,这般顽皮的人物,竟然也被赵与莒生生给治了过来,不仅治过来,还能将于竹这样的也带过来。
于竹专心注著地推着独轮车快跑,推这车也有讲究,若是停下来,或稍有不平衡,车便会侧翻。故此虽然他明明看到了杨妙真,也不曾停下脚步行礼招呼,李邺早就教过他,做事时须得专注,否则不如不做。
“到了!”眼见靠近目的地,他才渐渐放慢脚步,到了地方之后,他将车上砖块每六块一次地搬了下来,哈哈大笑道:“俺今日已经是十二车了,老德,张献宝他多少车了?”
被称为老德的是个三十出头的黑胖汉子,身体肥硕得倒象个地主老财,一手拿着铅笔一手拿着纸,笑眯眯地看了眼纸:“十一车,多乎哉,不多矣。”
“比俺只少一车?”于竹瞪大了眼:“俺不信,老德你莫非数错了?”
“让开让开!”他正说道间,突然后背有人怒喊:“好狗不挡道!”
于竹拉着车子避开,抹了把汗便撒开了腿,身后那人一边下砖一边问老德道:“那厮多少车了?”
“十二车,比你多一车,献宝,你今日要输与他了。”老德笑道。
“老德,格老子的,我岂会输给他个龟儿子!”那人冷笑了声:“瞧我的!”
杨妙真正往这边走来,听得那人一口蜀腔,回过头来问赵喜道:“移民里连蜀人都有?”
“连夏人都有,何况川人?”赵恩笑道:“这厮来时已经十七了,故此不曾进入初等学堂,极是能吃的一条汉子,是个霹雳火的脾气,偏偏于竹喜欢逗弄他,二人无论做何事都要比试一番的。记帐的叫王老德,偏是喝白水也能胖起来的人物,莫看他这般模样,倒有些心机,跟着学堂夜校学得识字算帐,是个精细人呢。”
杨妙真微笑起来,天南地方各种各类的人物,都被赵与莒收容过来,他们在原先地方不过是路死沟埋的货色,可到了流求,总能被觉有用之处。
“俺看好了,这就回去。”她向赵恩招了招手:“看情形你这是极忙的,休要招呼俺,俺自家识得回去之路!”
“那小人便不送了,四娘子路上小心。”赵恩也不客套,在郁樟山庄里呆惯了的,便知道那些礼节客套都是虚的,唯有实诚做事,方能得到赵与莒重视。象方有财,初到郁樟山庄时只靠着嘴皮子,始终不得赵与莒信得,但后来建新庄子时实诚肯干,立刻被提了起来。
杨妙真循着田埂向回走去,嗅着这田野之间青草的芬芳,她心情忽然放松起来。一种6地之上没有的感觉包住了她,她觉着在此处,极是无拘无束。她深深吸了口气翻身骑上自己的马,再向四周看了看,低声自语:“这是俺男人的,俺拼了性命,也要将它看护好!”
想到赵与莒,她有些惆怅地北望,若是赵与莒能与她一起,在这无边的原野上纵马疾驰,那有多好。
“也不知他如今可好?”( )
九十七、惊蛰雷响动九渊
杨妙真所挂念的赵与莒,坐在一顶小轿之中。他掀开轿帘,有些怅然地望着外头的街道、行人,虽然他可以看到外边,但他知道,自打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外边的这一切便不属于他了,他过的将是牢中鸟一般的生活。
这是在庆元府昌国县,也即是沿海制置使驻军之地。上次临安之行,虽然史弥远私心之中已是属意于他,可是因为全保长大张旗鼓的缘故,最终赵与莒兄弟还是被送回了山阴。此事令全保长极是羞惭,四邻也多有讥嘲。赵与莒兄弟回乡过完年之后,余天锡再次到了虹桥里,偷偷将赵与莒带走,有过一次教训,全保长这次自然不敢声张。
余天锡也没有把赵与莒带回临安,而是带回他的家乡庆元府昌国县,由他母亲照看,并且教导赵与莒宫庭礼仪。此地距悬岛并不远,不过赵与莒还是尽可能深居简出,更是尽量避免与悬岛联系。
他知道自己身边定然布满了眼睛,史弥远绝不会将他摆在此处便不再关注了。
路旁熙熙攘攘的人流来来往往,因为悬岛的缘故,这昌国县极为繁华,在悬岛之上赚得钱的沿海制置使军士,还有来此收购刻钟、洋布和玻璃的商贾,让这昌国县远胜一般县城。
赵与莒正要放下轿帘,突然听得路旁有人“咦”了声,他侧过头去,却看到胡福郎吃惊地盯着他。
赵与莒苦笑了一下,没想到自家出来晃一晃,还是会被熟人遇上,不过遇上胡福郎倒是无妨,他原本便是全家远亲。史弥远便是查也查不出什么破绽来。故此他踩了一下轿底,抬轿子的两人放下轿子。他自轿中出来,向胡福郎行了一礼:“九哥原来也在此处!”
胡福郎神情惊讶,自己常驻于昌国,正是赵与莒的安排。他前些时日让杨妙真带来的信,说是将会有段时日不再来,为何又突然乘轿出现在此?
“与莒,你如何……”他是个极机灵的。只道是赵与莒被人挟持,故此看了那两个轿夫一眼。两个轿夫虽说面露不耐之色。目光倒不凶狠,这让他有些放心,看了看周围,一个义学少年也没有,这又让他不解。
“九哥,我如今在此求学。”赵与莒悄然挤了一下眼,让胡福郎不要多说话,胡福郎会意。拱手道:“与莒在此求学。何不让人告诉愚兄一声,也好有个照应。”
“不敢麻烦九哥。九哥店铺依旧在原处?”赵与莒道。
“正是,与莒若是有暇,不妨到我这来。”
赵与莒不敢多做耽搁,两人拱手话别,望着赵与莒消失在轿子中,胡福郎皱紧眉,心中突的一紧。
跟在赵与莒身边地,分明不是郁樟山庄的人,虽说山庄三期之后地义学少年他都叫不出名字,但赵与莒身边的却不然,大多他都认识。这些年来,托着赵与莒的福,他专售继昌隆的生丝与绸缎、江南制造局地刻钟,已经为自己置办了大量家当,虽说赵子曰、孟希声先后分去了他不少权柄,不过他对自家的境地已经极是满意。可他也明白,自家有今天,皆是赵与莒之力,离了赵与莒的支持,凭着这几年的积蓄,他还是可以当个足谷翁,却未必能更进一步了。
他地利益,与赵与莒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在义学少年长成之后,赵与莒对他地倚重不如以往,可在胡福郎心中,却如同当初开“保兴”时一般。
他正思忖当如何是好时,旁边有人拉着他道:“胡掌柜,你为何还在此处愣,快上楼吧,今日愚兄做东,你无论如何也得给小弟这个面子。”
胡福郎拱手道:“小弟临时有事,须得回去一趟,陈兄还请见谅。”
那人原本请他吃酒,是想借着他地关系多收些刻钟,闻得此言不免失望,还待再劝之时,胡福郎已经匆匆离开了。
他走时匆忙,却未觉有人跟在身后,回到自家店铺之后,他写了封信,刚唤来仆人,想让他送去悬岛,忽然又觉如此不妥,便起身想要自己送出去。
出门不久,他终于觉有个人跟在自己身后。那人自与赵与莒偶遇起便一直跟着他,他偏偏是个极好的记性,对人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觉那人跟着后他心中再次一凛,确信赵与莒真的遇着了麻烦。
他是个极小心的人,当下便改了主意,借着自己熟悉周围情形,甩脱了跟着之人,乘船离了定海,连夜兼程赶回山阴。当他赶到郁樟山庄后,他才自赵与芮口中得知一切,这才恍然大悟。
“据说朝庭有意为沂王择嗣,莫非与莒能入嗣沂王府?”知道赵与莒并无妨碍之后,胡福郎心中暗想,他来山阴时匆忙,回昌国时却没有那般紧张了。
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回昌国的途中,有关赵与莒与他见面之事便被呈到了史弥远桌前。
“是与莒舅家远亲?”看到那份陈条,史弥远皱了皱眉。
赵与莒极合他的心意,不仅因为他觉得这少年性子迟缓,便于他操纵,更是因为余天锡与他说起过的种种异端。他极信天意的,故此才会笃拜佛释,觉得若是赵与莒在手,他之大计定然能成。因此之故,他才对赵与莒格外关注。
条陈上写地极详细,包括早年胡福郎曾经替郁樟山庄开“保兴”之事都写得分明,就连最后“保兴”为人所迫,不得不关张也有记载。史弥远算了算时间,当时赵与莒才值七八岁,这磨坊或许是他玩出来地,但开“保兴”定然是与他无关,想来应是他母亲为了维持家业所为。若赵与莒真是天纵之才,又怎么会被区区行所迫。不得不关了能为自家生财的粮铺?
心中虽如此想,史弥远还是觉得。让赵与莒继续呆在昌国已经不妥了,他唤来余天锡,没有与他提起胡福郎之事,而是问道:“纯父。那少年在你家有多久了?”
“回禀相公,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余天锡笑着拱手:“相公便是不问,学生要也说地,家母有信来。说是他已学得差不多了,便是一手字。也大有长进。”
“看来倒真是静心苦学了。”史弥远微微一笑:“纯父。明日辛苦你回去一趟,将他接回临安吧。”
听得此言,余天锡心中大喜。他久居相府,自然也习得一些史弥远权术本领,知道此事若成,那便是拥立之功,史弥远固然将因此而权势永固,便是他论功行赏起来。也少不得分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