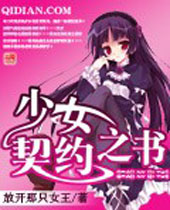失败之书-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前,她被发现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惟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作为一个例外被安的亲戚们接受。起初,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勾引女孩的大学教授。约翰默默不语,用双手证明他还有别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时间,把森林深处的破败农舍翻修成像样的家。
约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不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惟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地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流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象。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
约翰和安(2)
…
安和约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无意听到。安想要养个孩子,或至少养条狗。我当然能理解她内心的软弱。她在暗夜里嘤嘤哭泣。但转过脸来,她又笑了,跟我们讲起他人的悲惨故事。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
美国房东
…
如果我凭记忆给拉瑞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九三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300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开冰箱想找点儿饮料,忽然感到背后的目光,转过头去。“嗨,”拉瑞坐在沙发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镜后面审视我。我有点儿尴尬,像贼被抓住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西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普斯兰梯(Yi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西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纳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瑞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接着她开始盘问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饭后我看两人继续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夜里我被他们做爱的声响吵醒了。看来事情进展顺利,我为拉瑞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而高兴。
第二天我问拉瑞是否关系已定。他含糊其词,暗示那位女客不会再来了。没两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门,戏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给他们做饭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拉瑞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参加了一个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把诸如人种、年龄、身高、体重、爱好等个人资料及电话号码发给每个成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自由结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拉瑞每天回家直奔电话录音机。拉瑞坦白说,他根本不想再结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拉瑞很吝啬,一般吝啬的人总是抱怨没钱。他下了班常常不归,找一些杂活干。比如帮别人粉刷房间、安装电器、布置花园。后来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穷,他另有一处房子租给了学生们。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瑞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
…
帕斯(1)
…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Paz)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