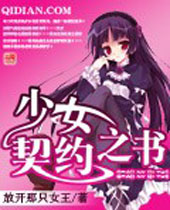失败之书-第3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午夜之门(2)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 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罗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莫托瑞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 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午夜之门(3)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份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