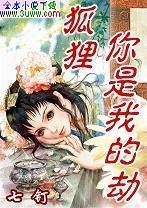�ҵ���������-��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껻�ڶ��ų�Ƭʱ�����߾Ϳ�������Ϣ������ˡ���������
���������ҵķ����ǰѴ�һ�������������·ֿ����������������飬��ʱҲ�Ƚϲ�ָͬ��¼�ƵIJ�ͬ�汾��ѧ��ѧ�����ƺ���ִ���ڰ汾������ŷ��ִ��в��죺�������ڵ�һ��������22��22�룻�˴��³����ĵڶ��汾��Ϊ23��17�롣�������������һ���Ŀ��ױ��գ�O��Klemperer����ֻ��19����2�룻����ͷû�����յ��Ӳ�³ŵ�������أ�BrunoWaiter���İ汾�������ٶ�Ҳ����������һ��ָ�Ӽ��У�˹���ؽ�L��Slatkin���й��оصİ汾����21��25������������£������˲���˹̹�ͳ��ˣ�����1987��ָ��ŦԼ���ֵİ汾����������24��53�룬��ν���¼�����������������գ�SimonRattle����23��52�롣��Ȼ�������������ԭ����ʱ������25��9�룩��������û�����롶�ڶ���������֮ǰ�ġ�ԭʼ�桱��������úܣ�һ���dzɣ�ȴ�����ء���������
����������ΪʲôҪ��ʱ��ԭ��ܼ��ٶ��ϵ�������Ч�������أ��Ǹ��������ƺ�Ҳ��ׯ�ϡ�Ȼ��ԭ����ע�����ٶ�ȴ�ǡ�ׯ�ϵĿ�塱�����Կ����������ϣ�ֻ�в���˹̹��������ħ����ʲô��������������Ȼ����������������ҡ������ǣ�������š������Ƿ�Ϻ����ߵ����ݣ���λӢ��һ���ļ�ֵ��ʲô������Ӣ�����Ż��ǹ���Բ��֮����������ޣ���������
������������д����һ�����²�27�꣬����֮������������£��ѵ���������ʱ�����뵽�Լ�������������ٴ�֤�����ּҡ�����Ī���غ��沮�ء��������ˣ�����Ҳ��������ʱ����̫�����У������ĵļ尾��ʹ��Ҳ̫�����ҡ�Ȼ�����պ��������ּҲ�ͬ��������ҵ�Ϻܳɹ�����ʮ���������άҲ�ɸ��Ժ���ܲã�����������������ĥ�Ѷ�˵ġ����ڶ�������������ʱ���������ȿ��������ջ�Ҫ�������������������ѽ�ծ����Ʊ�뵱�أ����֣�����ѧԺ��ѧ���������ѹ����ܾ����Լ���;��ⶡ�����
�ڶ����������������������ߣ��ϣ����յġ������2��
������������������
�������������ڸ�һλ�����ҵ�һ���������д������������
���������ڶ�������һ���������ڶ�������һ�ֻ��䣡��Ӣ�����ĵ�һ�����⣬�峺���ơ���һ��������һ�����˵ľ��飬Ҳ�����㣨�����Ļس��У�һ�����������������������ȵ�����ʱ���ͻȻ�����������Ŀ�У��·������������ꡪ������������������֮�¡����㼸�������˸ղŷ��������飬����ǵڶ����¡�������Ǹ���ܰ���������������������»ص������������������Ȼ�����⼤�����ݵ������������⣬����ͻȻ�е�ֵ���������һ���ƹ�ͨ������������Щ���粨����������ߣ���������ĺڰ��г����濴��������̫Զ���㼸�����������֣�����Ҳ��ú������壬��һ���ֵ��Ļþ����������в�������һ�����ĺ��С�����ǵڶ����£������ľ��ڲ����С���������
����������λ����Կ�������ġ���������ѡ����������¼�Ƶĵ�һ���汾�����С��Ҵ���Щ���п���һ���������������ң�Ϊ��������Ʒ�����������⣬����ʱ�Ĵ�������ȴ������֮�Աǣ�������ɥ֮��������Щ�����У�������˵�����־�����������ȫ��������������Ʒ���Ǵ�������������ģ�Ȼ�����ġ������������ǻ���ѧ�����ڸ��顣��ͬһ��������˵��������Ҫ�����֡����ý����ֵ���ʽ�������ֳ�������������һ�����ʵĸ�����棬��һ�ȿ�������һ���������ǰ�����Ǹ������ʱ������û���κ����ѡ����Ǹ����磬�Ž̵��˿�������Ȼ�������á���������
��������Ȼ�������������У���������֮·Ҳ���ػ����۵ġ��ڵ��������У���������Ů��������һ�μ�Ϊ������ʫ�裺��������õ�壡������ʹ��֮�У�����Ը�����á����Ҵ��ϵ۶�����Ҫ�ع��ϵۣ��ϵ۸����ҹ�ԣ��������������õ��������������ˣ�·�����߲��ꡣ��˵����д��������µ�ʱ���ָ��Ѳ����������μ�����һ��ָ�Ӽҵ������������ó�ʫ��ĺϳ�����ŵõ������������������мӽ������ڽ���ζ�ĺϳ���Ȼ������ʹ�����������յ㣬Ҳ���ܾ��尾�ģ��ֶ��ڴ˱�����ó����뻯���ر����Ƕβ��������Ĺ�����������������ʹ���ٻ�����������һ����Խ�������Ʋ�ֱ�������������Ǻϳ����渶���������Ů������Ů�����������Ӣ�������ҵ����ȵ������ã����������������ڴ˼������õ���������������1988��汾�����Ȱ�Ү³��ѧ���õ�����ɷ�н��µ�¼�������ٽ�֮¼����β������������
�����������յ�����Ƿ��ɴ˵õ����ꣿ��������Ҫ�ٻ�ʮ���꣬��������ģ�Ӵ�Ľ�������ֱ������ھš�������һ��̽�������������������Ʒ�����뿪�����������51�ꡣ����������һ�꣨1911�꣩ǡ���й�������������������
���������ġ�������
����������ƫ���������ֶ��꣬���������ݵ���³���ɣ��������������λ���ּҵĽ����ֺ���һ������һ���dzɣ�һ�������������δ���Թ���ֻ�ǵ�����ѧ����ʱ������һ�����������յĽ�������ͷ����һ������β���ھţ�����ӡ����֮�衷��δ��ɵġ���ʮ���������ĵ�һ���¡����õ��Dz�ָͬ��¼�Ƶij�Ƭ�����ڳ�Ƭ¼�Ƶ������ͬ����Ҳ�����ܵ�һʱ�İ��á�����ͳ�Ƭ��־���۵�Ӱ�죬������ʱ�õ���������Ҳ��ʹ�Ҹ��ܲ�ͬ����������
�����������ԡ������������Ϊ�����ҳ���ʱ�����մ�����߶��صİ汾���о���ɫ�������������������֥�Ӹ罻�����Ź��Ƶ������汾���־�ǿ�����൫��Ȳ��㣬��������Ч���ϼѵ�˹���ؽ��վ�����˵Ļ��Dz���˹̹��1987������ŦԼ��������ij�Ƭ�����ҵ������豸�в���ʱЧ���ؼѣ������������յ�Ӣ���汾������������µ�����������ͷ��һ�����ֲ����ҵĿ�ζ����ͷ����ָ�Ӽҿ��ױ���ָ�ӵİ汾�����ŷ��ֿ�����������������°汾֮�ž�����Ȼ����һ�κ��ؽ�������¼�Ƶij�ƬЧ��ƽƽ������Ů�θ�������˹�أ�MaureenForrester�����dz��úܸ��ˡ����������ɫ�����꼸������Ī�����п�ƥ�е��ƺ�ֻ��·��άϣ��ChristaLudwig�������ݡ����ˣ�JanetBaker��������Ҳ���ݳ����ո������������λŮ���֡�������������е�Ů������ɫ������Ҫ��������Ҳ�����Ƹ���Ը��μ��ݳ���ʩ�ߴĿ��շ��ױ��հ棩�Ϳ�ɪ�ա����У�KathleenBattle��˹���ؽ�棩���Ƕ������ǵ�С�������������˽�����ŵ����JesseNorman��������û����������������
������������ڰ������ֽ�������۵�����������֮���ڣ��������ҽ�����������ҵ���ʿ����ɭ��Lucerne�����ֽ����˼������ֻᣬ����ѹ��Ϸ�ǰ��Ͷ�ָ�ӵ����մ������������Ϊ��̾����Ϊ������������ѵ�ڹ�͡�����˵��������˹̹���̫�����ˣ����Ͷ���Ǵ�ʦ������ʱ���Ͷ�մӰ��ְ����������������˰�֢��������ʿ������Ҳ�������������ձ�����֮�꣬�����ʼ��ͬ�аɣ�����������������ı����ֽ�ָ�Ӵ���ʱ��¶ͷ�ǵġ���������
���������ڸ�д����֮�ʣ����ر��1977�갢�Ͷ�ָ��֥�Ӹ����ŵ��ϳ�Ƭ�ó����������ֵ�һ���½���ʱ20��47�룬�����������Ҳ������顣Ҳ������������汾�������Ͷ�Ϳ�����������������������������ʱ
�ڶ����������������������ߣ��ϣ����յ�����ʢ��
�����������յ�����ʢ�硡������
������������۹������������ա�������
����������۹������ŵ������ܼ�ϻ��ؾ�ְ�ݳ��ĵ�һ�����ֻᣬ�����յġ���һ��������Ϊѹ��Ϸ������ŵ����ֽ���21���ͣ����յ����겻ɢ����������ͣ��������������ź�ָ�Ӽ�ͷ���ζ���ǰ�������ɡ����ս��ư��ְ��ֽ�������ʱ�������յ����ͷ�ڣ�ʮ����ǰ���Ͷ���θ���ָ��ʱ��Ҳ�����յ�һѹ���Ͷ�������ԭ��Ӱ��ְ������ݺ�ȥ������ʿ����ɭ���ֽڡ���ɽ�����������յĵڶ��������������ͷ��������
������������10��23�գ����ϻ�������۾���ָ�Ӱ��������յ�һ֮ʱ��ǡ�Dz�ʿ������ָ�����ģ�JamesLevine���쵼�����������յڰˡ����ųơ�ǧ�˽�������������Ϊ��ְ��������ԭ��ָ��С��������ְʱ���������յھ���Ϊ�ݱ����������������ÿ�������������������Ȼ�������ã������������ϻ���ָ����۹������ŵ����ࡣ��������
���������ҹ���ѡ�����ֻ�ĵڶ����������ɱܿ�����������������ʱ�������ֵ�ϰ�ף�����ר��������Ȼ�����ϰ볡����һ�����ݡ������ľ��ġ�Զ�Ρ�����������ס�ˣ�������鼤�������Է�й����ǿ�����г���Ϣ�������°볡�������������������飬��ϧ�ڵ�һ���¿�ʼ���ã���֧����ͭ�ŵ�������е���������������ζ�������ϻ��ص�ڹ�ͺ�����Ϥ�IJ���˹̹ǡ���෴���൱��������������˵������µĸ߳����ֶӵ������ƺ���Ȼ����������ǿ�ţ����Ҿ���Ӧ����fff�����ǵö���ǰ�ڲ�ʿ��������˹ָ̹�Ӵ������������߳���ʱ����ͭ�ܺ�ľ���ֵĶ�Ա��վ�������������Ҿ����ӣ�ȫ����δ�������������кã���������
�����������յ�����ʢ�硡������
���������������������������ߡ�������
�����������ֹ������ŵ����෨���ƺ��������ָ�ӽԲ���Ϊ֮�����Ͷ�Ͱ��ְ���Ԥ�ݴ���ʱ���ҿ����Ǽ�¼Ƭ�����ֶӶ�Ա���Ƿ�Ӧ��վ��������Ц˵�����ˣ�����������¼�Ƶ����ų�Ƭ����Ȼ����������ʽ�ġ�Ȼ�������յ�ԭ���е�ȷ��ָʾҪ������Ավ�����࣬�Ҳ¿�����Ϊ�˴ﵽһ���ر������Ч����������֧С����ȫ����ʼʱ�����ں�̨����һ������ɫ�����������������۹������ŵ���֧С���ִ˴�����Ҳ���ղ���������Ȼ����λָ�Ӽ��в�ͬ�Ŀ������ϻ��ص�ڹ��Ӧ���ܵ����ء��������ܹ��裨Ҳ�������ң�˵���������Ͷ���ǰ�ϻ���ָ�������մ��������¼�Ƶij�Ƭ���෨���һ�ޣ��ɼ��������ǵϻ��ض�������˼���Ǻ�ijɹ�����������
����������Ϊһ�����ԣ���ȴ���������������������������ʱ�ڵ���ƷӦ����ÿ���һ�㣬������һ���ºš��������ˡ������̵ĵ�Ȼ��һ���������������������ң������������Լ�����֪������������Ͽ�����ʱ���θ��룿
�ڶ����������������������ߣ��ϣ�����ѹ���ԡ����֡�
������������ѹ���ԡ����֡���������
����������۹��������ּ������һ�����ֻ������յġ����彻��������Ϊѹ��Ϸ���ܼ�ϻ��ؽ�����۹������ŵĵ�һ�����ֻᣬ�������յġ��ڶ�����������Ϊ����������ν��ʼ���ա�Ȼ��������ּ�ȴ�������κ�������Ʒ����֪Ϊ�Σ��ѵ��ϻ���ҲҪѧ���ɡ�����ǰ����ư��ְ���ʱһ���������յ���Ϊ�������ڵڶ��ּ�ȴ�������κ����յ���Ʒ������Ψһ��һ�����������յ��������ֻ��ø�ǰ��ָ�Ӱ��Ͷࣨ���Ͷ�ij�Ƭ�ճ��������ԡ����춯�ء����������ݣ�����������
�����������յĽ�������Ŀǰ���н������ŵ��Խ�ʯ����۹�������֮ǰ��������յ�һ��ǿ���⣬�˴�����ĵ�������н����������пɸĽ�֮�����ڴ�Ը�����Ժ������Ե�������ש�����Գ¼�������������
������������Ҫ����ǵϻ��ض����յ�ڹ�ͷ�ʽ����ָ�ӵ����յ�һ����ָ�������մサ��������¼�����ij�Ƭ�е�ڹ�����ƣ��й��оأ��������ţ������߷������ò���Ϸ���ԡ��˴��ݳ��ĵ��壬���Ҳ������ij�Ƭ���Ƚϣ���ƾ�������ֵľ�����ۣ�����������൱����ȣ����Ұ����������Ľṹ���ֵ�ʮ�������������ͷϷ�ڵ������¡�г��������Scherzo�������ѵ�һ�������ġ���������Ϊ�ԱȺ����죬�����۹�������������ؼ��Ե�������Ҳ������ر��������ر�����ϯС����Լ�ú��������ˣ�JonathanClarke���ı����ر��ɫ������֧С�ź���֧Բ�ŵ������˴�һ���µġ��������������ڵڶ�������Ҳ�����ˡ��������͡�����������ã�ֵ�û��ڡ���������
��������Ȼ���ڵ�һ���£�С���������������ʼ������������ֶ�ȴδ�ܡ������������ֲ��ֵ���������Ҳ�������ҵ�¥����λ������Ч�����⣬�Ļ����ĵ�����ʵ�ڸ������ˣ�����ľ���ֲ���ú�Ͷ�룬����ȫ��С�ź��ֵ�ǿ��������֧�䣬��������������������ġ����ᡱ����Ҳ������׳�������е����壬��Ҳ������ϻ��ص�ڹ���йء���������ָ�Ӱ��ְ��ֵİ汾�Ƚ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