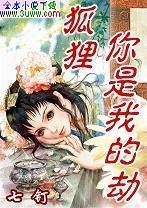我的音乐往事-第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ⅰ妒ジ杞幌烨贰ⅰ禖调交响曲》、《奥菲欧斯》、《帕西风尼》和《浪子历程》等名作,如今这些作品已经成了20世纪音乐史上的“经典”了。
斯氏虽然标榜古典主义,但他仅是利用古典的题材(如《俄狄浦斯王》)和古典的作曲形式(如对位、赋格)而已,这些题材和形式,似乎给予他一种架构的限制,在这种自我约束的架构中不断创新,就是斯氏心目中的自由,这种看法,显然也是属于古典主义的,但斯氏的古典主义,却为自己添增一种新的风格——简洁、峻峭、严谨,更充实了节奏感,也为乐坛树立了一个新的旗帜,作曲家风起云涌,几位美国名家如库普兰(AaronCopeland)和塞逊(RogerSessions)等纷纷群起效尤。
斯氏于二次大战初避难到美国,定居好莱坞,埋首写作他的“新古典主义”的乐曲,岂不知十里以外就住着他的死对头——勋伯格,这两位20世纪的大师,却只在一位朋友的丧礼上见过一面,真可谓是“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当1951年勋伯格去世后,斯特拉文斯基却突然于古稀之年开始用十二音律写作,最初是战战兢兢,几年后就得心应手,到了1957年的芭蕾组曲《阿冈》,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当斯氏掌握十二音律的时候,年轻一代的作曲家如约翰·凯吉(JohnCage)和斯托克豪森(KarlheinzStockhausen)等人却完全打破“音律”的范畴,使用噪音、天然音和录音机,目前最流行的是一种“电子综合机”拨弄出来的“音乐”,对于这些新的东西,斯氏一概嗤之以鼻。也许,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位音乐老人已经开始落伍了,也许他一直是作曲家中的“贵族”,坚持音乐本身的神圣,而否定一切不属于音乐或不够音乐水准的东西。
斯特拉文斯基非但是音乐家中的“贵族”,也是人生中的“贵族”。终其一生,他不愁衣食,幼年时代在圣彼得堡,娇生惯养,青年时期在瑞士和巴黎展开音乐活动,受到名振欧陆的名舞蹈家迪亚基列夫(Diaghilev)的重用,他早期的三部芭蕾舞曲,都是这位名师的“俄国芭蕾团”(BalletsRusses)重金礼聘而写的。斯氏成名后,更是嗜财如命,又因为他喜欢水城威尼斯,所以有人称他为“威尼斯商人”,斯氏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说:“作曲赚钱的妙诀是,先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然后再使写成的东西作为别人的重金委托。”他甚至把自己英文姓名的第一个字母“S”也设计成钞票的缩写“”!在未死之前,他已经在拍卖他的曲谱,当《纽约书评》的编者问他为什么不把曲谱送给博物馆或图书馆时,他不禁大发牢骚道:“因为没有指挥音乐会和灌新的唱片,我的收入已经大减。然而我比较受人欢迎的作品,在美国偏偏是不收版税的免费品,如果用我近来不受人欢迎的作品的所得,来偿付我的医疗费的话,照目前的写作进度来看,恐怕要到我102岁的生日才能付清我的医药债。”
斯氏发这句牢骚的时候,大约是在1971年初,他刚从美国西部迁居到东部的纽约,为的是医疗方便,却想不到竟骤然长逝,如果他仍留在阳光充足的西部,他的作品也许就不止一百多首乐曲、11本书和无以计数的文章,照他最近几年的作风来看,似乎是人越老话越多,他曾与徒弟克拉夫特(RobertCraft)合写了六部《谈话记录》,又接受《纽约书评》杂志编者数次访问,这位老音乐家态度高傲、牢骚满腹,用字遣词极尽艰涩冷僻之能事。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战乱和流亡是20世纪思想和文化史的“主旋律”,然而迄今为止,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并不太多,和中国有关的研究则更少。20世纪末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界大谈所谓“离散社群”(Diaspora),却往往把它设在一个“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讨论,甚至和“全球化”拉在一起,毫无历史意识可言。
其实“Diaspora”(离散社群)这个词源自犹太人的历史,指的也是犹太人离散到他方,如今被广泛引用之后,反而把这个犹太根源给忘了。也许,重谈20世纪犹太人流亡的故事早已成了老调,而且在目前的气候中也不合时宜,所以最近这类书在中国似乎未受重视。承蒙《读书》编辑汪晖先生的推荐,我得以读到这本译著——《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读后不胜欣慰,也连带想起犹太人流亡的问题。
斯特恩(原名HellmutStern)是犹太人,1928年生在柏林。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当权并大肆排犹的时候,斯特恩举家逃难。他们到处申请签证碰壁,英美各国对犹太人的入境管制更严,最后竟然流亡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原来斯特恩的母亲获得一份捏造的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去工作,于是全家于1938年离开德国,乘船辗转来到中国,经上海、大连到哈尔滨,一住就是11年,和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关于哈尔滨的章节。
《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灵魂在乐谱上行走(1)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自1931年起,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为日本人统治,属于伪“满洲国”——一般史家对于这一个时期的研究往往嗤之以鼻。然而,日本殖民者在东北留下大量的研究资料,“满铁”收藏的经济资料更丰,为美国知名学者如马若孟(RamonMyers)、黄宗智和杜赞奇(PresanjitDuara)等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资料宝库,但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斯特恩的这本书,恰好为我们打开一个研究哈尔滨文化的窗户。我读了此书才理解哈尔滨当年竟然如此“国际化”(cosmopolitan)。哈尔滨虽在日军统治之下,但作为纳粹同盟的日本非但不排犹,而且大开方便之门,所以除了上海之外,哈尔滨也成了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自1917年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更多,包括白俄和俄裔的犹太人。这些外国人很快就在这个东北边远的城市酝酿出一种以宗教和音乐为主的国际文化。书中如此写道:
这样一来,20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就变成了一个带有国际色彩的都市——而且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那些流亡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待在中国……可是,他们都先在这里扎了下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很便宜,至少在这里的生存前景短期内是令人乐观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准备出发的气氛。“黄金的20年代”在这里开始了。哈尔滨很快成为“远东的巴黎”。
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哈尔滨开设了领事馆。连美国也设立了代表处。那时候不必缴税……于是,百货大楼、夜总会、旅馆,一切都以欧洲的风格出现了。此外,也出现了许多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音乐厅,等等。
以上的叙述,很容易使人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中国竟有两个“远东的巴黎”,也是我在为拙著《上海摩登》准备资料时始料未及的。我心目中的“双城记”指的是上海和香港,是以英国殖民文化的背景为坐标,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和犹太文化。从本书作者的立场而言,犹太人流亡故事的“双城记”却是上海和哈尔滨。斯特恩全家抵达上海时,曾遇到一位久居上海的犹太富翁Toueg,其财富与沙逊和卡都里两大犹太家族齐名。这位富豪有意收养十岁的斯特恩,但为其父所拒绝。“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斯特恩在书中回忆说。于是全家终于定居在哈尔滨,一住就是11年。
从一个音乐和文化的观点来看,斯特恩的音乐天分完全是在哈尔滨培养成熟的。他的老师特拉赫藤贝格(书中未附原文,无从考证)原来是圣彼得堡玛里金斯基剧院(译者没有注明原文,可能就是当今最有名的Marinsky歌剧院,它的乐队叫Kirov交响乐团,也有一个同名的芭蕾舞团;现在的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杰基耶夫)的首席小提琴家。这位小提琴家是俄罗斯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奥尔(LeopoldAuer)的学生,所以应该和奥尔的另一位高徒海菲兹是同辈甚至同学。而特拉赫藤贝格在哈尔滨教出来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也是斯特恩的同学——杨慕云,后来成了中央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40年后,斯特恩随柏林爱乐访问北京时,两人终于重逢。
作为一个乐迷,我对于斯特恩这段叙述中的音乐掌故特感兴趣。他说连大名鼎鼎的海菲兹都曾在哈尔滨客居过,还有那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FyodorChaliapin,书中译为菲尧多·沙雅斌)。斯特恩参加他老师组织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这个乐团可能和当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相似,成员都是洋人。斯特恩说:“乐团的音乐家之中不仅有俄罗斯人,而且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在日本占领期间也有几个日本人。”他的老师担任首席小提琴,指挥是施威考夫斯基。该团定期举行音乐会,也邀请独奏家和客座指挥,内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指挥朝比奈隆(TakashiAsahina,书中照音译为高市朝雏),最受乐团的欧洲人钦佩。这位大阪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曾两次受邀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虽没有小泽征尔(另一位与中国东北有渊源的音乐家,他生于沈阳)名气大,但他对布鲁克纳交响乐的诠释至今独执牛耳。妙的是我最近在北京购得一套价廉物美的“雅典艺术”版布鲁克纳交响乐全集光盘唱片,指挥就是此公(也没有注明日文原名)。据闻他最近已经过世。
斯特恩于1942年14岁时举行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弦裂》一书中把曲目列了出来(第55页),大多是难度甚高的小品——巴赫的《g小调帕蒂塔、柔板和赋格》(可能有误,应该是《g小调奏鸣曲》中的一段)、康努斯(Conus)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冷门作曲家的协奏曲极为好听,当年可能是热门,也是海菲兹的拿手好戏)、克莱斯勒的若干名曲(可能是《爱之喜》、《爱之悲》、《中国花鼓》等小曲),最后是帕格尼尼的《女巫之舞》(难度当然更高)。14岁就有此造诣,实属难得。
斯特恩全家在哈尔滨的生活很苦,他为了援济家用,也曾自组四人小乐队为中国人的婚礼奏乐助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来了,他们的生活更不安定,甚至还要到内蒙一个小城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去找工作。几经折磨之后,终于在1949年离开中国,乘船到以色列。先在咖啡厅伴奏,混一碗饭吃,最后终于在1951年进入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作为一个犹太人回归故土,斯特恩对早年以色列建国后的文化问题却着墨不多,对自己的落叶归根心情也无交代,不免令人失望。也许,他和许多德裔犹太人一样,心目中其实有两个祖国——以色列和德国,前者是他的心灵故乡,后者是他的文化故乡,而文化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心灵上的感受。因此斯特恩在本书有关以色列的章节中,谈的几乎全都是指挥家和演奏家,尤以描写海菲兹和钢琴家鲁宾斯坦最为传神,对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记述则不多,甚至关于他和卡拉扬之间的恩怨也只是一笔带过。倒是谈切利比达克这位传奇性的指挥家的篇幅较多,说他当年还是一个调情高手,深受女士们欢迎。
斯特恩本来可以长住以色列,在此飞黄腾达,然而他的父亲却又移民美国,他几经考虑后也决定于1956年到美国谋生,以便照顾年岁已高的父亲。然而他在美国并不走运,因为没法加入工会,所以失去了一个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机会,只能在二流乐团工作,甚至还卖过皮鞋和保险。最后终于在1961年重返柏林,并顺利考取柏林爱乐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据我所知,该团有四位首席小提琴手,斯特恩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日本人,他脸上有一个大黑斑)。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魂在乐谱上行走(2)
斯特恩在描写他重返柏林的章节中却充满了激情,甚至特辟专章讨论“为什么回到德国”,为什么还要回到当年备受迫害的地方?他说有些犹太人想到德国的时候,“感到有无法克服的仇恨,表示将永远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而像他这样选择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并不多。他自称“在全部流亡岁月里,我都非常思念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