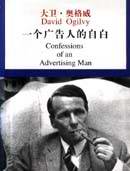黑皮自白-第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春督察处下设秘书室、督察室、侦审室、第一科(情报科)、第二科(总务科)。
督察室为督察处的核心科室,外勤活动的指挥部门。督察处的大量活动均由该室执行,如搜集情报、侦察跟踪、检查搜捕以及行刑等。该室编制上校督察长一人,中校督察主任一人,督察员数人,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巡查队,哨卡,检查所及警卫分队。上校陈毓 、李冷、关梦龄、陈牧先后充任督察长。
该书涉及督察处的人物,除督察长关梦龄外,有安震东(少将,第二任督察处长,后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处决),张国卿(少将,第三任督察处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陈牧(上校,先任督察处侦审主任,后任督察长,解放后处决),陈寿岚(中校督察主任,解放后处决),印匡时(上校秘书主任,解放后处决),郭子襄(少校督察员)、翟丕翕(中校侦审主任)、杨绍林(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中校情报科长)均被处决;陈哲(中校总务科长,捕后释放)。
② 保密局长春站:建于1946年3月,原称军统北满站,戴笠死后,改称保密局长春站。长春站是军统在“北满”的特务核心,军统在“北满”的各特务组织以长春站为轴进行特务活动,督察处亦在其中。长春站对督察处的领导是全面的,同时又是原则的,督察处既在长春站领导之下,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特务组织在蒋管区大肆镇压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在解放区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派遣特务,设置潜伏小组,搜集情报,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第二章 该杀当死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4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门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9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来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7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面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分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