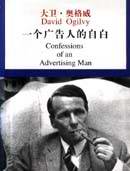黑皮自白-第3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150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农场主任介绍说:“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建造了厂房,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成立了三个生产队,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去年收成很好,给国家收了30多万斤粮食。今后还要扩大,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
接着参观拖拉机,苏联的履带拖拉机“热特”、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斯大林80号”拖拉机。“热特”机正在切豆饼。天很冷,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主任在汽车上说:“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方圆百里,都要开垦成良田。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农场主任高大身材,黑红的脸,有30几岁,学机械的。人很稳重,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充满着乐观精神。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那就好了。
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10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一九四九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着想着,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开饭,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台湾解放后,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但也没人反驳,何必叫大家扫兴呢。
每天我看不少书,写不少笔记,不间断写日记,认为马上就要出去,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一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子,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80%。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哎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送我们到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九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五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三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