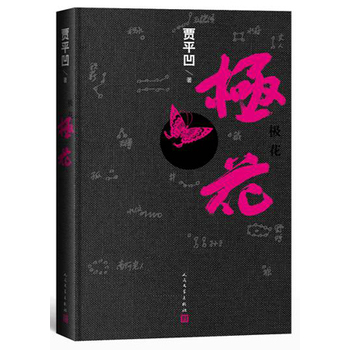极花-第2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扒拉着水前行的,现在没有水了,走路胳膊腿在扒拉着空气,空气也就是水。我知道了月亮和星星是属于夜的,梦是属于夜的,有些动物和植物也是属于夜的,我睡在哪儿瞌睡了都在夜里。知道了乌鸦乐意着乌鸦,它们在白皮松上有说不完的话,而何首乌的枝条和何首乌的枝条交接了也开花生香。知道了修房子,房子的人把砖瓦抛上去让房上的人接,接的人越是抗拒,砖瓦越会打伤手,只有迎合着,就能顺势转化冲力,接起来轻而易举。知道了你用石头凿狮子用纸剪老虎,凿成了剪成了你也会恐惧它。知道了心理有多健康身体就有多健康,心境能改变环境也能改变容颜。
那一夜里有了雨。
黎明时分,疯狂的雨落在硷畔上,尤其在磨盘和井台上,听了一个响声就折身离去。狗在窑门口窝成了一团。乌鸦回到了巢里。而何首乌藤蔓下的那几块小石头还在,它自己生不来根系长不来翅膀,浑身沾了泥水,怨谁呢?一只狐狸出现在老老爷的葫芦架下,似哭似笑,似笑而哭,很快从硷畔上跳下去就不见了。
兔子开始在炕上哭,我去哄他,原来是尿布湿了,给他换上了干尿布。哐啷一声,是猪又跳出了猪圈,噘着黄瓜嘴在硷畔入口那儿拱土,猪是肚子饥了。我穿好了布鞋,再在布鞋上套着了一双黑亮的草鞋走出去,这一天就又忙忙碌碌了。
* *
如今,我学会了侍弄鸡。黑家原来是一只公鸡三只母鸡,黑亮爹为了留住我,留住我就先要留住胃,他杀掉一只母鸡给我吃了。另外两只母鸡和一只公鸡见了我就啄,正面啄不着,常常一转身,便啄我的脚后跟。当又杀了一只母鸡,剩下的那只母鸡和公鸡见我就跑,跑不及了张开翅膀飞,它们是能飞到葫芦架上,鸡毛都散落一地。我知道我是鸡的罪人,对鸡说:不是我杀的,不是我要杀你们。坚决不让黑亮爹再杀了,还新养了六只母鸡两只公鸡,黑家就有了十只鸡。鸡和狗不和,狗老撵鸡,鸡还是在硷畔上随吃随屙,到处是鸡屎,但它们热闹着,我也不寂寞,我和鸡们相处得很好。三只公鸡的冠越来越大,肉乎乎的全垂下来,而且颜色红得像染血了。老老爷说过,人头上都有黄光,黄光大身体好也长寿,如果黄光小了,不是在生病就是快死呀。可老老爷还说半语子头上的光是红的,红光的人火气大,半语子就是火气大。公鸡的冠应该也是红光变的吧,三只公鸡的火气也大,动不动围着狗啄,啄得狗不敢再撵母鸡,然后它们要扯嗓子叫,叫声从杂货店那里都能听到。七只母鸡安静得多,个个都是在头顶上隆起一堆绒毛,像是插着什么花似的。每天早晨吃饭,我的舌头能发出咕咕的声响,母鸡们就跑拢了来,盯着我的筷子,我把碗里的饭夹一疙瘩扔在地上,它们就地啄,我会就势抓住一个,指头塞在屁股里,我也能知道里边有没有个软蛋,是马上就下呀还是午饭后才能下。对着狗说:顿顿给你喂那么多,鸡吃的啥,吃虫子吃菜叶吃草也吃沙子,鸡下蛋哩你不下!黑亮在旁边说:鸡不下蛋鸡憋得难受么。我去收拾鸡窝,在那个筐子里铺上了干草,再铺上苞谷胡子,让它下蛋时有个舒适的地方。等着蛋下来了,把热乎乎的蛋放在眼睛上,眼睛在这一天里都是明亮的。我也会再把鸡蛋拿起来对着太阳照,瞧见里边隐隐地有一小块阴影子,知道那是被公鸡踏过所生的蛋,这样的蛋就放在另一个罐子里,将来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那一只遍身都是黑羽毛的母鸡,我已经试过了它当天没有蛋,它总是早饭后就卧在鸡窝里,到了正晌午还在卧着,我就把它赶出去,说:你给我遭什么怪呀!它占了窝,别的母鸡就把蛋下到别的地方了,我就得抱着兔子去硷畔下的草丛里或厕所后的柴禾堆里去寻找。
如今我学会了做搅团。搅团做好了就是搅团,做得不好就成了糨糊。搅团是用苞谷面来做,尤其是秋后的新苞谷磨出的面,做出来清香,又筋道又软滑。但搅团是一年四季都吃的,不可能总是新收的苞谷磨出的面,用旧苞谷磨出的面也可以,必须是旧苞谷磨出七天之内的面,如果过了七天,做出的搅团就不好吃了。做搅团首先是会和面,舀一瓢苞谷面在冷水里先搅成糊状,不能稠,也不能稀,筷子一蘸要吊出线来。当锅里添够水,水在第一滚将面糊糊倒进去,倒进去后就立即用擀面杖搅,不断地搅,一边搅一边再直接抓面粉往锅里撒,撒匀,不能有面粉疙瘩,一旦有了面粉疙瘩,那做成的搅团就不好看也不好吃。搅要一个方向搅,不能左搅一下右搅一下,乱搅做的搅团没筋道。搅是力气活,要搅八百下或一千三百下,锅里的面糊糊先是翻滚,再是起泡,最后是彼此的气泡噗噗响,泡破着溅开。这时的火不能用硬柴,最好是禾秆或荞麦草。一直搅到你把擀面杖插在锅里,它能立起来一秒钟。灶火退去,盖上锅盖,捂那么一个时辰。捂的期间,就在另一个锅里用油炒好葱花,蒜苗,辣面,盛出来,再烧开半锅水,放上盐、醋、酱、花椒、胡椒、大茴小茴,水滚开了,再放进蒜片和姜末,再放进炒好的葱花蒜苗辣面,汤就做好了。搅团如果没有好汤,那就是糨糊。吃搅团时在碗里盛小半碗搅团,浇上汤,这叫水围城,筷子沿碗边来动,刨着吃一口,喝一口汤,不能慢也不能快,慢了吃不进嘴里就从嘴边掉下来,快了便烫嘴,尤其在喉咙烫喉咙,咽下去了烧心。搅团香是香,不耐饥,这里人称它是“哄上坡”,说是吃得再饱,从坡下走到坡上肚子就饥了。所以农忙时不吃搅团,吃搅团是下雨天没事,嘴又馋,才做搅团。
如今我学会了做荞面饸饹。荞面筋性差,难以擀成面条,只能做饸饹吃。做饸饹叫压饸饹,得有饸饹床子。这村里人家的家具都不完备,平日需要时你借我家的,我借你家的,但饸饹床子家家都有。饸饹床子其实很简单,用榆木做成一个镲草的镲子一样的形状,只是没有镲刀,在上的那根木杠要长,安着一个木槌,在下的另一根木杠中刻一个圆坑,坑里透着几十个眼儿,荞面和成面团后,就烧锅水,等水滚开,把饸饹床子架在锅上,然后抓一块荞面面团握成坨形,放在那个圆坑里,抬起上面那木杠,木杠上的木槌正好顶住有面团的圆坑,使劲往下压,面团就从圆坑的窟窿眼儿吊出饸饹来,煮在锅里。压上边的长杠那得使劲,整个身子都要伏在上边,有时就跃身坐上去。饸饹可以凉调了吃,那必须配以辣子蒜泥醋和芥末,芥末最重要。也可以再炒了吃。也可以浇汤吃。家里有亲戚来了,一般都吃凉调饸饹,能当菜吃,更是主食。村里谁家过红白事,客多,那就吃汤饸饹,汤饸饹一碗就盛那么一筷子饸饹,只捞着饸饹吃,不喝汤,把汤再倒回锅里,重新盛饸饹,浇汤,一直吃十几碗二三十碗了,最后才把碗里的汤喝掉。村里人把这种饸饹叫“涎水饸饹”。我觉得不卫生,村里过事时我是不去吃的。而我在家做饸饹了,给黑亮和他爹他叔都用大碗,饸饹和汤一块吃喝,每人两大碗就吃喝饱了。
如今我学会了做土豆。土豆可以蒸,可以煮,可以切成片和块了炒或炖,可以切成丝热炒和凉调。切丝时讲究切得又薄又细。开头我切时,黑亮说我切的是板凳腿,后来我能切细了,又为了快,刀就伤了我几次指头。现在我一边和人说话一边切,甚至晚上不点灯摸黑切,切出来真的是一窝丝。如果热炒,切出的土豆片和土豆丝不过水,如果要凉调,切出来的土豆片和土豆丝就一定要过水,否则就粘成一疙瘩,既不好看也吃着不爽口。炒土豆片可以放酱油,凉调土豆丝却只放醋,还要白醋。过水的土豆片和土豆丝,水里就有淀粉,沉淀了,再摊成饼,炒这种饼,那就是粘粘,老人和孩子最爱吃。粘粘和肉片辣椒丝再一起炒,那是饭桌上的一道硬菜。把土豆片用绳子串起来,一条一条挂在墙上晾干,干土豆片和豆角南瓜一块焖炖,又是另一种味道。还有几种吃法:用土豆丝包荞面窝头,用土豆丝煎苞谷面饼,用土豆丝拌面粉炸丸子,用土豆丝包饺子。还有一种叫擦擦,就是把土豆丝用荞面,或豆面拌搅了上笼去蒸,蒸熟了浇上辣子蒜泥水吃。还有一种吃法叫糍粑。糍粑是把蒸熟的土豆放在石臼里用木槌捶打,打成糊状,还打,糊状成了胶状,拿出来浇上油泼的辣子,蒜泥水,醋和酱,滴两点芝麻油更香。糍粑在捶打时十分费劲,而且十斤土豆只砸出五斤糍粑,只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才做这样的饭。最方便的就是蒸土豆和稀饭里煮土豆,不要切,就那么囫囵着。这种吃法几乎村里的人家一天至少有一顿,吃时嘴张得很大,眼睛也睁圆。但村子里有好多人眼睛都不大,使我想不通。
如今我学会了骑毛驴,毛驴背上不垫任何东西,骑上去也不牵缰绳,从硷畔上走下去村里的漫坡,经过那些错综复杂的巷道,甚至塄塄坎坎,我让毛驴往左它就往左,我让毛驴朝右它就朝右。如果双腿一夹,它跑得噔噔噔,我在毛驴背上还抱着兔子。如今我学会了采茵陈,它嫩的时候和臭蒿分不清,只能看叶背,叶背发白,掐下了有一种呛呛的气味。茵陈当然是一味药材,能清肝明目,去毒败火,但茵陈在长到三片四片叶时采回煮熟那是一道好菜。而它一老就不能吃了,只能割来晒干当柴禾。如今我学会了认地椒草。这种草的籽在煮肉时放进去,能除腥味。学会了编草鞋,虽然人人都穿布鞋胶鞋了,下雨天村里人还是要穿草鞋。学会了缝制腰带,村里年岁上了五十后都喜欢系腰带,黑亮爹是大热天光了膀子也系腰带,他说不系腰带,身子好像直不起,是两截。学会了用糜子做糕做酒。学会了用蒿子做笤帚,用黄麦菅根做洗锅的刷子。
如今我学会的东西很多很多了,圪梁村的村人会的东西我都会,没有啥事让他们再能骗我,哄我。黑亮说:你最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做圪梁村的媳妇了。这话我又不爱听,每每在清晨我拿了笤帚扫硷畔,听到金锁又在东坡梁上哭坟,我就停下来,回窑换上了高跟鞋,然后再扫。
* *
黑亮的肚子已经大得站直了眼睛看不见脚尖,裤子也提不上,裆吊着,显得腰长腿短。他一天三顿一口都不少吃,晚上还要再吃些什么,吃完了就鼓腹而歌。我让他减减肥,但老老爷却在说男人要腰粗的,四十岁左右肚子还没起来,那一生就不会发达了。
黑亮要发达,他不满足经营那个杂货店,与村长闹过别扭后,同张耙子三朵商量了,还是同意和村长一块搞血葱生产基地,条件是村长可以当头,但起步钱三人平摊,日后赚了钱也三人平分。新的血葱生产基地经过反复选址,最后是定在村子坡梁后的野猫沟。但野猫沟的地也是一片一片分给了各家各户,要集中出四十亩地种血葱,就得把他们三家别的地拿出来和那十多家的地置换。那十多家听说是村长、张耙子、三朵和黑亮要种血葱,也想入过来,他们不愿意,人家就不置换,或者置换,要以野猫沟的一亩地置换别的地方的二亩地。矛盾一起来,这就靠村长去硬吃硬压,村长也趁机给黑亮和张耙子三朵提出:将来血葱赚钱了,他分四成,其余人分六成。黑亮和张耙子三朵咬咬牙,说行,就让村长去解决,而黑亮也给村长说地动时他家的窑裂了缝,想在现在的窑的左边二三百米处再箍几孔窑,要求村长批个条子,他到镇政府申请去。
吃饭的时候,黑亮把这事在饭桌上说了,黑亮爹说:才合作呀,就心怀鬼胎,那以后赚开钱了,村长他就吃独份了。黑亮说:只要真的赚钱了,说不定我们就先把他踢腾出去了,要不,我咋让他批庄基条子哩。黑亮爹说:你有钱箍新窑?黑亮说:先把条子拿到手么,卖血葱了就有钱的。黑亮爹看了黑亮一眼,低头把碗里饭吃完,起身又去厨房里盛饭,半天再没出来。黑亮就给我说:男人么,好男人一生最起码要干三件事,一是娶媳妇生孩子,二是给老人送终,三就是箍几孔窑。箍窑这念头是在你来了后就产生的,尤其有了兔子,愿望更强烈了。人常说别人的媳妇自家的孩子,咋看咋好,而我是看着兔子好看着你胡蝶好,我就要给你们娘儿俩住上全村最好的窑!他越说越兴奋,饭也不吃了,要拉我去他选中的新窑址。黑亮爹从窑里又出来了,说:你好好吃饭!别狂,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黑亮说:爹,这咋算狂?黑亮爹说:你是不是以为有了媳妇有了孩子,这世上啥事都能干啦?!黑亮说:胡蝶和兔子就是给了我自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