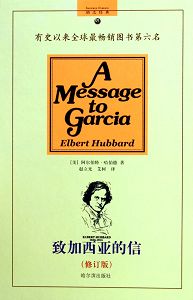伊利西亚-第2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嘘!”埃尔丁叫了一声。他竭力在大喘气的同时挤出一丝笑容,“这不就是我那令人尊重的老伙计库拉托尔馆长!”
库拉托尔馆长的眼睛,起初闪着冷冷的蓝光,随后立即变成了深红色,几乎同一时刻何罗从后部对金属人发起了攻击,抓住了他作为脑袋的那个蠢笨的凸出物,这一行动无疑是救了埃尔丁一命,由于何罗猛拉库拉托尔馆长的头部,从他眼中发出的两道红色射线,错过了埃尔丁这个目标而击中了埃尔丁后面的拱道,烧得拱道上的石头焦黑了一大块。
“库拉托尔馆长,”库兰斯喊道,“库拉托尔馆长,你犯了个致命的大错误。”
知道他并没有犯错的埃尔丁,已经飞快地跑进博物馆中,消失了。库拉托尔馆长的攻击目标转向了何罗。除了博物馆及馆内摆设之外,他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
德·玛里尼大喊:“莫利恩,时钟飞船,”同时奔向时间机器;如果他能把时钟飞船置于库拉托尔馆长和搜索者之间,那双方都将有喘息之机。另一方面,那个女孩——对无论多么奇异和丑陋的生物都从不害怕——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跑去;库拉托尔馆长正在堤道上抓着何罗的后背,高高举起,说时迟,那时快,库拉托尔馆长把何罗的身体旋转两圈,向墙外扔去;何罗的腿碰着了墙,立即用脚钩住不放——实际上当库拉托尔馆长抛开他的时候钩住了一线生机。
莫利恩已经接近这个金属人了,但库拉托尔馆长并没有看见她,他弯膝跪在墙顶上,头朝前俯着,水晶眼紧盯着何罗的腿,然后伸出一只金属手,抓住何罗的一个脚踝,迫使他把腿伸直,另外一只手则伸向何罗的另一个脚踝。
莫利恩赶到了,毫不迟疑地冲到库拉托尔馆长和何罗之间,伸出手抓住库拉托尔馆长另一支正往下探的胳膊,同时半转身,对着库拉托尔馆长喊:“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能为了你那愚蠢的博物馆而杀人?立刻把何罗拉上来!”
库兰斯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俯身墙外,抓住何罗的一只手,开始把他往上拉,他和莫利恩最终把脸色苍白的搜索者拉回了安全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安全。库拉托尔馆长并没有完全放过他,也没有忘记埃尔丁。
看到何罗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中,漫游者又从博物馆冲了出来,握紧了拳头,摆出传统的拳击架势;库拉托尔馆长看见了他,放弃了何罗(尽管不情愿),威胁性地大步逼近了埃尔丁,就在此时,德·玛里尼驾着时钟飞船及时赶到,停在了两人之间。
库拉托尔馆长看着时钟飞船,红色的眼睛渐渐褪成依旧具有危险性的橘红色,其中燃烧着一种黄色的火焰,片刻之后转为蓝色,就像冰屑一样闪着寒光。他朝时钟飞船缓缓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
在时钟飞船里的德·玛里尼意识到他该怎么做了。阿塔尔曾告诉他库拉托尔馆长能通过模仿四只手的动作与有色的金属立方体“交谈”,即通过机器人之间的语言进行交谈。现在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用时钟飞船和库拉托尔馆长进行交谈,但是怎么用呢?时钟飞船在它复杂的构造中隐藏着许多秘密,这就是其一。泰特斯·克娄曾多次暗示,这个机器是半自动的,有知觉的,那就意味时钟飞船有它自己的机械语言能力……为什么不可能呢?在清醒世界中,计算机之间不也相互“交谈?”时钟飞船之间为什么不能?甚至连克娄也不知道那些大幅摇晃的四只手的重要性:难道是时钟飞船在计算、思考或自言自语?
德·玛里尼知道怎样使用时钟飞船的扫描仪、传感器。
扩音器以及武器系统,他能驾驶它往来于不同的两个世界。
“按钮”、“开关”和“扳机”全记在他的头脑中和在时钟飞船的头脑中——在他们的头脑中:他的和时钟飞船的。他们的头脑合二为一时,他闭上眼睛去感觉那些熟悉的工具和控制器,找到了它们:“我必须和库拉托尔馆长交谈,让他告诉你再传给我,请你帮助我与库拉托尔馆长交谈。”
在清醒世界这也许不能奏效,但在梦境中事情总是会简单得多。德·玛里尼感觉到头脑中像是打开了一扇门,或者说在他的头脑和时钟飞船的头脑之间打开了一扇门。他知道自己已经找着这个时空机器的“通话器”,现在已经可以与库拉托尔馆长交谈了。
在堤道上,库拉托尔馆长走得更近了,他水晶石的眼睛中充满了怀疑和质询,他期待地望着时钟飞船转盘上的手,德·玛里尼知道不能再让他等了。
金属人发生变化对库兰斯、莫利恩和何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时钟飞船也发生了变化,它的手无规律地运动着,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迹,狂乱地挥舞着,完全缺乏协调性,总而言之,这是过去完全不曾有过的,起码在德·玛里尼的经验之中是这样。
“看!”库兰斯低低地说,“库拉托尔馆长和时钟飞船一样挥手,看!它们在交流!”
库拉托尔馆长的四条细长胳膊转到了他筒状身体的前部,移到了一个定点上,伸伸缩缩地调整好它们的长度,开始有节奏地不停旋转、颤动、疾挥——没错,他正在与德。
玛里尼交谈。
“我是探索者,”德·玛里尼说,“我想你应该听说过我。”
“事实上,我听说过许多事情,有关于你和莫利恩。关于你正通过其与我交谈的时钟飞船的,还有你想要寻找的埃尔丁。我听说在太古时期有一块原始土地以及一个叫埃克西奥尔的白色巫士,我听说在熔岩湖沸腾着的里特,阿达斯·埃尔坐在他的飞房子里测量一个垂死太阳的脉搏——太阳将会再生;我也在很多地方听说邪恶的势力正在上升,其中之一甚至威胁到整个多维世界本身的结构。”
“那么你肯定能帮助我,”德·玛里尼说,“我们能在别的地方进行秘密而舒适的交谈吗?”
“我在哪儿都很舒服,”库拉托尔馆长回答,“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躲在塞兰尼恩下面,擎住悬空的石头,梦谷的景色尽收眼底。然而我想,你是不会这样做的;你在时钟飞船里不舒服吗?”
“是的,但——”
“但你是人,需要熟悉的环境,适应的氛围以及个人隐私。好吧,我理解你,我自己也是一个隐居者,进博物馆谈,好吧?但首先我得处理完麻烦事——他们两个,一个甚至现在还躲在你的飞船后面……”
德·玛里尼打断了他的话:“库拉托尔馆长,你不许伤害搜索者!”
“不许?”库拉托尔馆长看上去很惊讶,“伤害?我知道这些词的意义,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用在这儿?你不明白:我只是在保护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人类最奇特、最伟大、最惊人的梦幻痕迹,这儿有许多不为人知、或被做梦者清醒后所遗忘的梦;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噩梦,把它们传送出去能使人发疯,这儿是梦的王国,梦的丰富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所有想象,除了——”
“什么?”
“我知道最后这个词的含义,我能肯定你也必须知道,但这儿有两个人是不会明白的,他们也想象不到骚扰我所保护的这个博物馆——并由此保护梦谷的土地——会招致的后果,但你说不许我伤害他们?也许我不会——他们确实是毫不知情!所以站到一边去,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打发他们。首先是躲在你后面的那一个!”
库拉托尔馆长的话表明他无意伤害搜索者。德·玛里尼把时钟飞船升到空中,使埃尔丁重新暴露出来了。他重新举起了拳头,喊道:“来吧,库拉托尔馆长。你和我单挑。用别的方式也行。”
库拉托尔馆长的眼睛又变红了,两束光柱喷射出来,比预想的速度还要快,不是射向他的拳头,而是割着了他周身的衣服,但却没有烧焦他的一根汗毛。光柱不停地移动着,把埃尔丁的衣服割得只剩下碎布条,埃尔丁的手匆忙移动,想护住他身上的布片。他衣服的口袋被割开了,一把闪光的珠宝掉落到堤道的圆石上——随之而来的是库拉托尔馆长更猛烈的报复性攻击!
一时间埃尔丁几乎变成赤裸了,紧紧抓着碎布片以遮住自己,或者说是掩盖他的窘相。当漫游者恐吓的气焰被彻底打倒之后,库拉托尔馆长把注意力转向了何罗。
库兰斯和莫利恩立即站到了一边:埃尔丁也许除了自负之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此何罗也应该是安全的。
阿达斯。埃尔何罗的感觉是:当金属人最初攻击埃尔丁的时候,他完全被吓坏了,但是漫游者所受的惩罚似乎罪有应得,因此何罗咧嘴微笑,继而大笑起来,但现在:库拉托尔馆长的眼睛变成了银色,射出的光束也是银色的,何罗感到那些光束在用力拖他,他举起双手想避开库拉托尔馆长,“停止开火,你这镀锡的机器,”他喊道,“我做了什么事,值得你这样?”
但银色的光束更快地射向何罗,把何罗快速地抬到塞兰尼恩上空,金属人的头继续后仰,直至他完全垂直向上看——此时光束迅速延伸,把何罗推到头顶上的云层中,消失于视线之外。忽然光束断了,金属人收回了视线,所有目击这一动作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直到何罗穿透云层重新跌落回视线之内。光束重新射出,准确无误地接住了他,把他缓缓放到码头边上。当库拉托尔馆长放开他时,何罗只觉得气短胸闷,头晕目眩,然后摇晃着仰卧在地上。
紧接着,这个博物馆的看管员又回过头来,以同样的方式把埃尔丁从堤道上举起,抛落在他的朋友身旁。金色的光束从库拉托尔馆长突然变成黄色的眼睛中射出来——那是一阵明亮的黄色,就像许多黄蜂被捆在一起形成的,而且这种光束也像那些令人讨厌的昆虫那样能蜇人。当光束击中埃尔丁和何罗的时候,他们嚎叫着,跳着,咆哮着——埃尔丁更是经受着双倍折磨,他渴望用碎布遮盖住自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奔向塞兰尼恩迷宫似的巷道,很快不见了踪影。
“伤害他们?”库拉托尔馆长又开口了,他大步走向那堆掉落在圆石路上、差点被窃的珠宝,动手把它们拾起来,“也许有一小点。我只要确信我的行为能镇住他们就足够了,但无论那两个人在哪儿出现……”他闭上了嘴,留下余地,等把珠宝全部拾起来后,走进了博物馆。
在时钟飞船里的德·玛里尼跟了进去,在他后面进去的是莫利恩,至于库兰斯,他跟在搜索者后面离开了;他要送给他们一艘小型太空船作无言的道别。既然他们不久就要在塞兰尼思被传为笑柄(由此也将会导致很多争斗),那么最好尽快把他们从太空岛上“驱逐”出去,即使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也行。
在博物馆内,莫利恩进入了时钟飞船,德·玛里尼告诉她他的新发现——时钟飞船的“通话器”,现在她也能听到库拉托尔馆长的话了。
“你在寻找伊利西亚,”金属人说,“我知道我是在那儿造出来的。我在伊利西亚时有了外壳,到这儿才有了生命。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怎样去那儿,因为我对伊利西亚一无所知,只知道通向那儿的路漫长而艰辛,然而,你到这儿来在我的预料之中,在你之前有个人——有个东西——也来过梦谷找库拉托尔馆长。“
“那个灰色的金属立方体,”德·玛里尼说,“属于某种时钟飞船,它告诉你来自伊利西亚的关于我的情况。”
“继续说下去,”库拉托尔馆长有些惊讶,“也许梦幻时钟飞船对你并没有什么用,也许你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信息。”
“梦幻时钟飞船?”
“是的,那个灰色的金属立方体是艘梦幻时钟飞船——一个在思维的潜意识层工作的控制器。自从我来这儿以后,梦谷中从不需要这样的装置,但这次那个立方体是作为一个信使而来的。”
德·玛里尼皱了皱眉头,说:“泰特斯·克娄告诉我去我自己的梦中寻找,到过去里去寻找——或者说到我自己的过去里去寻找;他提到了一个巫士,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巫士一样:埃克西奥尔·克穆尔。有知觉的气状物嘶嘶嘶嘶嘶告诉我差不多同样的事,我已经在这里的梦谷中找遍了所有可能的路径,如今看来,最终的答案肯定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在塞姆何佳的埃克西奥尔·克穆尔那儿。”
“说得对!”库拉托尔馆长说。
“但是已经过了40亿年了!”德·玛里尼说,“我能在过去的哪里——什么时候找着塞姆何佳?又到塞姆何佳的哪个地方去找埃克西奥尔·克穆尔?”
“噢!”库拉托尔馆长说,“这些问题你必须去问梦幻时钟飞船,只有它才有来自伊利西亚的答案。”
库拉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