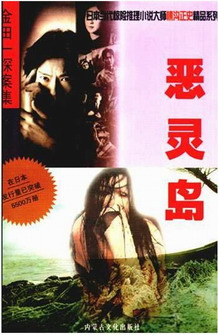古拉格群岛-第8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工作”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下一页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上一页
回目录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